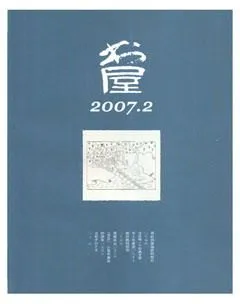《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譯序
馬克斯·韋伯的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二十年前有彭強、黃曉京翻譯的簡本和于曉、陳維剛等人翻譯的全本,2006年陜西師大出版社又出版了后者的所謂“修訂版”。這些年來,“韋伯熱”在中國持續升溫,這兩個版本可謂功不可沒。
馬克斯·韋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艱澀難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轉譯,翻譯起來自然比一般學術著作困難。上述兩個版本的翻譯并不盡如人意,專用名詞錯訛較多,因為“硬譯”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處也多,馬克斯·韋伯作為社會學大師的睿智與博學,對人情事理的洞察與明達,語言的機敏與靈秀,就這樣被轉譯文字的粗疏與荒蕪,掩蓋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閃光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們在這次重新翻譯過程中,也頗能體會前輩當年勞心勞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來翻譯基礎上稍有進步,庶幾不辜負近半年來的“苦行”。
司馬遷《報任安書》有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治學的最高境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有足以當之者。本書處理的主題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說”(天),后者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變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轉變(人)。天人之際,最為幽邈難測,探究其間關系,舍馬克斯·韋伯這等天才其誰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間,特別是1520年之后,“傳統基督教整個結構中的幾乎每個部分,都受到了批評性的審查”。原來的信仰、實踐機制,或者遭到徹底破壞,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現了基督新教,一種新的信仰、實踐機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問題是“我蒙恩得救了嗎”,信教摧毀了原來的常規遵奉結構——含有神秘法術的儀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懺悔”也被告知毫無用處……在這一片廢墟之上,加爾文宗的“預定論”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預定論”告訴了信徒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但對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問題,又什么答案也沒有提供,“它是把信仰問題的全部責任,都轉壓在個體肩膀上了”,信徒必須自己找尋得救的證據與答案,“自己創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贖的確證”。這就給人的世俗生活帶來了兩大變革。
一是“神圣”與“世俗”之間的轉換。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東西,如神秘主義、隱修制度、獨身主義等等,都變得不那么偉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棄,與此同時,原來很多“世俗化”的東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價值上得到了承認,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這是一種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轉換,也是神圣價值向世俗價值的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職業(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圣徒就是履行其職責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業中也能榮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證明,例如1684年英國一位牧師宣稱,“商人以其職業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發展這一事業”。所有誠實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職責,甚至“清掃房間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須忠于職守,干好工作”。這樣經過加爾文教義的置換,俗世中的職業變成了榮耀上帝的手段,發財致富也不再是一種罪惡。但散發著神圣氣息的“Calling”,始終是一種救贖的“召喚”,賺錢不是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榮耀上帝。為了證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寵,這些苦行的信徒,就會把剩余資本投入再生產領域,而自己的行為還是要時刻檢點,以期符合圣徒的標準。這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制度、資產準備上,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則是開啟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過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渾渾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隨機成分居多。現在加爾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證明來,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須每時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覺。加爾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懺悔辦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則是日記。英國神學家比德爾1656年在監獄中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把我們在一天中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記下來,也把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事情記下來。”這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加爾文教徒的共同心聲。與比德爾幾乎同時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萬頁的祈禱、謝恩記錄。巴喀斯特牧師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記里面,對自己年輕時所犯下的錯誤痛悔不已:“偷水果、讀愛情小說” 等等。蒙田和盧梭的《懺悔錄》風靡一時,也是有此種社會風氣背景的。為了獲得救贖蒙恩的證明,新教教徒就通過這種不斷的反省、砥礪,將自己的日常生活歸整為一個系統化、理性化的模式,這是一種“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與否的選民觀念,也改變了傳統的人際關系,由共同選民組成的團體逐漸具有了對事不對人的特性,這是現代社會組織或是企業組織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這兩種轉向,西方文化發展出一種以“合理性”為基礎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現在工商業上,便是如何能夠有效率地去賺取利潤。這便是韋伯闡述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再往后發展,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理性至上”的口號甚囂塵上,科學與民主的觀念逐漸成為新的“天命”,終于造就現代文明的輝煌,追根溯源,還是從這兩大轉向處發軔的。
但歷史的發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發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詭”。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漸走上了“祛神圣”之不歸路,在一個神圣缺席的時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儼然譖越成為一個個頭頂光環的“神圣目的”,同時也使得物質財富“這件外套”,變成了一間像鋼鐵一般堅硬的牢籠,而原本用來履踐“榮耀上帝”精神的“職業”,從“Calling”變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著其內在神圣性的喪失,而逐漸變質為單純謀生的手段,“完成職業責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價值有什么聯系”,職業中的枯燥、無聊、壓抑,竟成為新時代的文化病癥之一。“理性化”以對日常生活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歸整始,卻日漸陷入瘋狂與虛無的泥潭中無所適從。韋伯認為,在現代社會,流行的是“以一種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為美麗畫皮的機械性僵化現象”。這是一個預言,也是一種嘲諷。
翻譯過程中,我們時時感覺到馬克斯·韋伯對這種文化危機的焦慮與擔憂,這應該是他著作此書的原初動機,即他的目的不僅僅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還是希望能對他那個時代文化上的種種弊端提供救療的啟示,起碼是像魯迅說的那樣,要喚起治療的注意來。
翻譯完畢,有兩個感想不期然涌上心頭。第一,現代化問題終究是起源于西方的問題。從韋伯這本書可以看出,這是歐美文化已經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極其復雜的數學題,而現在我們是被迫將這道數學題搬進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現代文明的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決了諸多人類之前未能解決的問題,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環境等危機也在所難免。在這道五百年的數學題中,西方自有其調節、化解這些弊端和危機的方法,韋伯的這本書便是一個證明。但對于跟著人家演算的我們來說,卻很難找到、也很難使用這些調節、化解的方法。例如韋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從中汲取對現代有啟示意義的智慧,我們就不可以,不說別的,光那些教派名稱就讓人腦袋大。但當我們也試圖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尋可以醫療現代文明病的啟示時,卻發現在這道數學題中,很難兼容下我們先人的智慧。這是我們現在進退無據的尷尬。
所以,如何找準自己的問題,而不是亦步亦趨地跟在人家屁股后頭演算,可能成為我們現在文化發展的關鍵。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發展的道路與軌跡,它可以吸收外來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環境變革的嚴峻挑戰,但如果它不能堅持自己的文化立場,而喪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質,迷失了前進的方向,那么即使埋頭“算”得再好,也不過成為一種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內部迷惘、混亂日劇,其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
第二,韋伯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文化模式,新教信徒的“入世苦行”便是。一方面有著高遠而超越的理想,一方面積極入世而履踐苦行,這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文化發展,都是一種最佳態勢,是取得成就的基礎模式。兩者互為依托,如果沒有超越性的理想而僅僅入世苦行,那么在取得一定成績之后必然會裹足不前,人的本能沖動,因為沒有超越性理想的升華與克制,必然會升騰為享樂的欲望,物質財富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聚散之間,消耗殆盡,更無法為進一步的發展提供基礎與動力;而如果僅有某種高遠的理想,卻缺少踏踏實實的入世苦行精神,則難免蹈虛陷溺之弊。任何偏頗都會帶來危害與弊端,觀諸中西方文化發展歷史可知大半矣。
最后還要對一個關鍵詞的翻譯做一點簡要說明。
本書第二部分有一個詞非常關鍵,即“Asceticism”。以前的翻譯大都譯成“禁欲主義”,我們這次改譯為“苦行主義”,是基于以下兩種考慮:一、從詞源上看,“苦行”比“禁欲”更為準確;。據《新天主教百科全書》(2003年版)云,“Asceticism”一詞來自希臘語“Askesis”,意為鍛煉、身體訓練,特別是指奧林匹克運動員在參加比賽之前戒除享樂而進行刻苦訓練。早期基督徒借用該詞,指為獲得美德而進行的靈性訓練。刻苦訓練包括“禁欲”,但還有訓練的意思,迥非“禁欲”所能包括。
二、比較兩個詞的語體色彩,“苦行”帶有褒義,“禁欲”帶有容易引人誤解的貶義,這應該是二十年前特定時代思想的反映。而且翻譯成“禁欲主義”,詞的外延較為狹窄,似乎只是“禁止欲望”,甚至更褊狹地理解為“禁止性欲”,然后又按照現代人的眼光判定為不人道。其實該詞在本書中不僅僅有遮止意義上的“禁欲”之意,更有積極作為以求得拯救之確證的含義,例如積極做工、謙卑、服從、齋戒、恒切禱告等等,絕非“禁欲”所能涵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便是直接將“Asceticism”譯成“苦行主義”,并有較長的解釋,如云:“宗教上為了實行精神上的理想或目的而克制自己肉體或心理上的欲望的一種實踐。幾乎沒有任何宗教不具有苦行主義的痕跡和某些特征。”又云:“苦行主義源于人們企圖達到種種最后目的或理想。……基督教中有多種類型的苦行主義。早期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是主張苦行的,敘利亞的基督徒是極端的苦行主義者。天主教注重隱修院生活,耶穌會注重乞食為生,都是苦行主義的表現。盡管宗教改革的領袖們不接受苦行主義,但在加爾文宗、清教派、虔信派中,還有某些形式的苦行主義。”在本書中另有一個詞語專門用來表達“禁欲”的,即“Mortification”。所以我們認為,將“Asceticism”譯為“苦行主義”,比“禁欲主義”更符合本文的語境。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英文版),李修建、張云江譯,九州出版社2007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