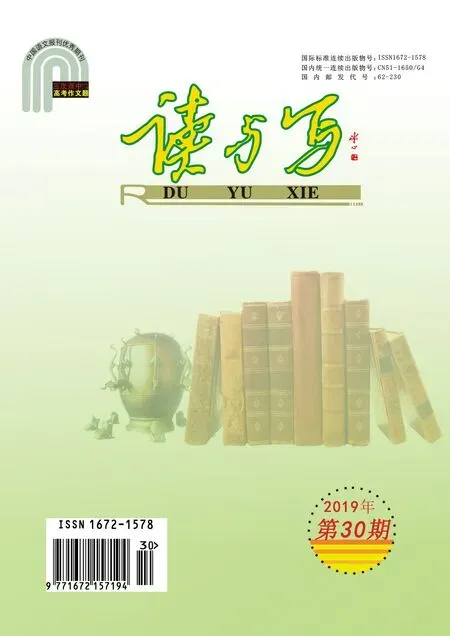基于核心素養(yǎng)的小學數(shù)學良好習慣的培養(yǎng)策略
羅金華
(四川省綿陽市新皂小學 四川 綿陽 621000)
小學數(shù)學學科的核心素養(yǎng)包括學生的數(shù)學基礎知識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與學習方式與方法等多方面的內容因素,據(jù)此,在課程開展過程中,教師需圍繞這些層面注重對學生思維的啟發(fā),引導其養(yǎng)成良好的數(shù)學探究方式,深化其數(shù)學問題意識,助力其良好習慣的養(yǎng)成。踐行核心素養(yǎng)的教學理念有助于培養(yǎng)學生對數(shù)學知識與問題的分析、思考與探究的能力,促使其數(shù)學綜合實力水平的顯著提升。
1.與學生生活實際相結合,全面深化其數(shù)學意識
教師從核心素養(yǎng)角度出發(fā)對學生的數(shù)學良好習慣進行培養(yǎng),需要首先結合學生生活實際來深化其數(shù)學意識,讓其體會到在生活各處蘊含到的數(shù)學知識與現(xiàn)象,以此方式不僅能夠加強學生對數(shù)學知識點的深入認知,還能激發(fā)其數(shù)學探究的興趣與欲望,使其深刻領悟學科思想,助力其核心素養(yǎng)能力的發(fā)展。具體過程中,將數(shù)學課程與學生生活實際進行結合,教師需以信息技術手段作為輔助用具展開教學探究,以此給予學生更為全新的學習體驗,拓寬其視野。比如在學習六年級位置與方向這一模塊內容時,教師便可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進行備課,在教學課件中突出教學重點來為學生進行多媒體投影展現(xiàn)。
本課內容要求學生能夠了解各項建筑物之間方向與距離等因素信息,使其能夠準確描述出兩相物體之間的位置關系。因此,為了能夠與學生的實際生活掛鉤,教師可向學生展示有關本市區(qū)的建筑地圖,讓其了解所在市區(qū)各項大型建筑之間的方位關系與其中的距離問題。例如,教師可以學校為中心點在多媒體展示板上向學生展示學校周邊的大型建筑,包括圖書館、超級市場、火車站或其他較為明顯的建筑,并繪制成坐標圖示讓學生進行瀏覽。之后,教師可引導學生依次描述各個坐標與學校之間的位置關系,以此加強其對于本課知識點的實踐應用,滿足核心素養(yǎng)的要求,扎實其數(shù)學知識基礎。此外,學生通過與自身生活實際具有一切聯(lián)系的圖示瀏覽能夠了解到生活中所蘊涵的數(shù)學知識,這能使其認知數(shù)學學習的重要性,培養(yǎng)其數(shù)學情感與興趣;同時促使學生在之后的學習中能專注于自主探究,自行解決一些疑難問題,打造個人良好的數(shù)學行為與習慣。
2.加強對學生教育指導,深入鍛煉其邏輯思維能力
邏輯思維能力是小學數(shù)學學科核心素養(yǎng)的重點要求之一,也是學生展開有效數(shù)學學習的必要條件之一,對其學習的最終成效而言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在小學數(shù)學教學中,教師應當加強對學生循序漸進的教育引導,幫助其深入分析數(shù)學知識與問題來鍛煉其邏輯思維能力,并以此優(yōu)化學生的數(shù)學探究方式與技巧,保障其充分學習收獲。具體實施思路下,教師應當重視教學過程來為學生營造思維拓展的教學氛圍,不管是在課程學習的哪一階段中都要加強對其思維的啟發(fā),需結合教學內容對學生進行有意識的思維培養(yǎng)。以兩位數(shù)乘以兩位數(shù)這項教學內容為例,在本模塊內容的課程開展后期,也就是復習時期,教師可為學生布置部分習題讓其展開具體的運算,進而分析與探究得出最終結果。
緊接著,教師檢驗學生運算結果的正誤,對于出現(xiàn)錯誤較多的學生要求其敘述自己的解題思路與運算步驟。與此同時,對于步驟較為完整且運算答案正確的學生,教師也需要求其敘述自己的運算思路與解題經(jīng)驗技巧。以這樣的對比方式能夠讓班級整體學生都意識到兩種極與極之間的探究成果分別是由怎樣的思路而展開的,并由錯誤的解題思路給予學生警醒,而由正確的思路給予學生啟發(fā),以此引導其他同學對自身的學習步驟與問題構思方式展開反思,全力強化對其邏輯思維能力鍛煉,培養(yǎng)其良好的學習探究思維與習慣。
3.適當創(chuàng)設教學情境,強化學生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教師依照核心素養(yǎng)的目標要求對學生的基礎知識掌握能力與數(shù)學邏輯思維能力進行了深入鍛煉后,便可適當為其創(chuàng)設教學情境使其展開對數(shù)學知識的深入應用與實踐,以此大力培養(yǎng)學生問題分析、反思與解決的能力,并保障其充分的課程學習效果,促使其良好數(shù)學學習方式與習慣的養(yǎng)成。以小數(shù)的加減法這一模塊教學為例,具體課程開展過程中,教師將班級學生分成不同小組展開分組的情境探究。每個小組需要根據(jù)教師的教育指導展開主題情境的演練,比如,其中一個小組可以構建到超市買東西的生活情境,并根據(jù)對所買物品之間的小數(shù)價格加減法加強對數(shù)學知識的具體應用。小組內部可由一個同學扮演顧客,其余幾個同學扮演出納員,而情境場景內部的操作工具可由學生的學習用具:鉛筆、橡皮和文具盒等物品代替;標價與金錢之類的物品則可由卡片代替。以這樣的方式展開情境探究,由出納員和顧客一同核算具有不同小數(shù)標價的物品,加強整組學生對數(shù)學知識的實踐應用。此項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夠強化對數(shù)學知識的掌握效率,還能體驗到利用所學知識解決一些生活化問題的喜悅,這有助于培養(yǎng)其良好的學科情感,使其在之后的學習和生活中也能運用數(shù)學知識解決問題,助力學生養(yǎng)成良好的數(shù)學行為習慣,提升他們的素養(yǎng)能力水平。
4.總結
總的來說,基于核心素養(yǎng)背景下的小學數(shù)學教學中,教師想要培養(yǎng)學生的良好習慣需重點從其基礎知識的扎實、數(shù)學邏輯與思維能力的引導以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的探究等層面展開路徑探索,積極更新教學方式與手段,以此在加強其學習效果的同時推動其素養(yǎng)能力的有效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