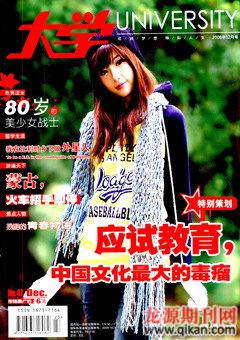多“好玩兒”的語言
宋 柯
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
二戰后,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于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后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他的夫人是個醫生,會說好多種地方方言。他們定了個日程表,今天說普通話,明天說上海話,后天說湖南話,一天換說一種話,來研究語言。有一回,趙元任同客人共桌就餐,他們恰好來自八個地方,趙元任居然共餐兩次,就能用同桌上的八種方言交談了。
趙元任曾表演過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陜西,出潼關,由河南八兩湖、四川、云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后八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話,介紹名勝古跡和土貨特產。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玨兒”。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后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趙元任和同學在閑時玩語言游戲。用同一個音的字不拘平仄寫出講得通的句子,趙元任于是整出了《施氏食獅史》,通篇只有“shi”一個音,寫出來,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說,那就任何人也聽不懂了:“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尸。食時,始識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回講演,趙元任當翻譯。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后去往北京,一路上熱鬧非常。羅素在杭州演講時,趙元任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在去住長沙的途中,趙元任跟同船一位湖南人學了幾天湖南方言,到了長沙后,羅素演講,趙元任竟能以當地方言來做翻譯了。那天翻譯完之后,一位聽講者上前問道:“趙先生,你是哪縣的人?”竟以為他是地道的湖南人了。其實,他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這些無形的鼓勵,使得趙元任在語言研究方面的興趣越來越濃。
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33種漢語方言,并精通多國語言。研究者稱,趙先生掌握語言的能力非常驚人,因為他能迅速地明白一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總結出一種方言乃至一種外語的規律。
但奇才從沒有放棄吸收新的語言素材。
1927年春天,趙元任在清華大學研究所擔任指導老師時,曾到江、浙兩省專門調查吳語。經常是一天跑兩三個地方,邊調查邊記錄,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農民家里。每到一處,他就到學生、教員、商店職員中去物色調查對象。確定對象后,即著手調查,快的花兩個鐘頭,詳細一點的,得花三四天。當時,他只能用耳聽手記的笨辦法。有時,他借助一點簡單的工具,記錄單字聲調音值。3個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在出版此書時,語音符號采用國際音標,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
他在88歲高齡時,還是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口袋上插著幾支不同顏色的筆,隨時把聽到的話記錄下來。在《中國話的文法》一書中所舉的實例,差不多都是他平時當場記下的別人說的話。
人們說他具有“錄音機的耳朵”。他是中國方言研究工作的開拓者和最有成就的工作者,是中國國語運動的元勛,他對漢語共同音標的確定、漢語拉丁字母的制作作出了杰出貢獻。1945年。他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被美國語言學界大家公認“在語言上趙元任沒有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