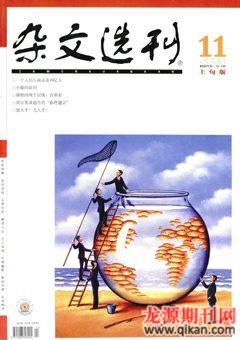陳澤群先生
劉洪波
雜文家陳澤群先生走了,我應該有一篇文字給他。
陳澤群先生1927年生于廣西陸川,1952年來到武漢,2008年9月2日逝于武漢。他一生的坎坷悲歡與武漢聯系在一起。我與先生極少見面,關于他的種種經歷,只是得自于閱讀。讀他寫的文章,這是我與先生交往的方式。
世界變化很快,今天在我們這座城市,哪怕以報紙為業、以筆為生的人,知道陳澤群先生的也不是太多了,而陳澤群先生卻是為報紙和筆而活的人。十三歲時他已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三十歲時因為在《長江日報》發表雜文《倚墻為生的人》而被派“右”,因這篇文章而引起的討論曾被編成小冊子《保護積極分子》正式出版,因這場討論而受牽連的有數百人。五十二歲以后獲得“改正”后,陳澤群先生發表了七百多篇雜文,絕對的幽默、犀利和雅致。
陳澤群先生已屬于歷史,無論他所經歷的時代,還是他作為一個雜文家,但沒有走進歷史的是他的雜文。互聯網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他是“網前時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不能從網上讀到,所以能夠讀到他的雜文的人也將是越來越少。
我不會去敘說陳澤群先生的生平,那些故事讀來令人傷感。盡管我知道今日也多有不如意的人,但如果讀過他的經歷,相信有很多人會體味出這個時代是多么幸福。老一代的故事,大概都有“憶苦思甜”的作用,何況陳澤群先生的經歷又非一般的生活困苦,而是一個思考與表達者所遭逢的困境。
讀到的訪談說,2006年夏天,陳澤群先生患上了“一過性失憶癥”。但早前十年,我已聽他說“很快要變成傻瓜”。1996年夏天,在《武漢晚報》的一次座談會上,我第一次見到陳澤群先生。座談會上還有老作家曾卓,剛退休的雜文家周聲華以及退休之后開始寫雜文的華中理工大學建筑學教授張承甫。
那次座談會上,談了雜文的話題,但現在記得更清楚的是打趣陳張兩位老先生。那時,陳先生和張先生都是剛剛再結連理,我們這些小輩分的就要他們分別介紹各自的戀愛經驗和婚后生活。言談和神色之間,兩位老先生都洋溢著幸福。那天陳先生說:“我正在變成一個傻瓜,醫生說按照我現在的情況,發展下去就是里根那樣。”陳先生風霜吹皺的臉上滿是笑意,孩子般的透明和頑皮,帶著我們沒大沒小。
那是一個溫馨的上午,座談的主題是張先生的雜文集《細辛草》。現在,張先生、曾卓先生、陳先生已經先后離開,老先生中還有周聲華先生在,幾年以前他開始當“抗癌明星”。
還記得到陳先生的家里去,那時他在趙家條的江漢大學住宅區里。陳先生帶著我們幾個人回家,家中卻是有人的,他說,我這里都不用鎖門了,隨時都有學生在這里。后來,江漢大學搬到了沌口,陳先生也移居到了田園小區,想必不再有學生容易登門拜訪,我想這一定不是陳先生想要的一種狀態。
城市是很多人構成的總體,但對于生活在他處的人,一座城市是存在的,可能僅僅是因為這座城市里有某個人。對一些人來說,武漢是存在的,會是因為陳澤群生活在這里;陳先生走了,武漢與他們就沒有什么關系了。容易也好,艱難也好,人都會有自己的一生。陳先生在我們這座城市經歷時代加給他的一切,也把自己變成人們建構武漢印象的一部分。
陳澤群先生的逝訊,我是5日深夜才從鄢烈山先生那里得知,6日早上就是他的告別式。此后,還會有多少人記得陳先生,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的文字還在,而我也沒有與他告別,他的離去并沒有成為我經歷的一部分,所以我會當他一直在。
【原載2008年9月10日《長江日報》】
題圖 / 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