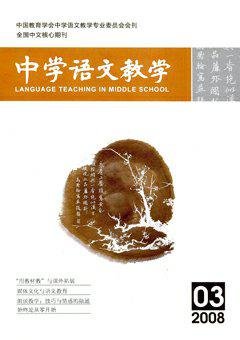始終是從零開始
洪宗禮
從學語文到教語文再到研究語文,我走過近半個世紀的“語文”之路。在這條坎坷崎嶇的道路上跋涉,我歷經曲折。然而,作為一個摯愛母語又愿終身為母語課程獻身的虔誠的教育者,我矢志不渝地求語文教學之真,解語文教學之謎,進而鑄造語文教學之“鏈”,終于到達我心向神往的彼岸。
我在一所學校從事語文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近五十年,盡管其間有多次從政與調至高校的機會,都毅然謝拒,堅守在我鐘愛的中學語文教學崗位上,始于斯,終于斯。年逾古稀,容易懷舊,便寫下一些往事及感悟。
上世紀50年代末初為人師,帶著1958年“大躍進”的狂熱,我躊躇滿志地來到江蘇省泰州中學,興致勃勃地走上了工作崗位,教的是初中語文。我在大學門門課程5分(時為五級計分制),又是學生干部,還擅長演戲。同學們夸我有“三個一”:一口普通話,一手好文章,一肚子詩詞散文。自視憑這些條件,教初中語文“綽綽有余”。然而任憑我天天忙到深夜也應付不了語文教學的“兩座大山”:改作文和備課文。上世紀60年代初正是中國語文教育抓“雙基”最扎實的階段。看著老教師毫不費力地頻頻收獲,自己則犯愁何日才能“多收三五斗”。
最使人煩心的是改作文。當時是每周一作一評(間周一大作一小作),把作文改得滿紙紅,卻吃力不討好。有位同學寫作水平一般,卻一次寫滿一本交來,錯別字、病句又多,可謂“荊棘叢生”,一篇作文改到深夜也改不完,一怒之下,手中蘸水筆的尖銳筆尖猛戳到作文本上,扎出一個洞。望著被墨水濡濕的殷紅一片,我才漸漸冷靜下來。次日,我把學生請到辦公室,帶著內疚而又埋怨的語氣說:“弄污作文本本該向你檢討,可你把作文寫得這樣長,錯字病句又那么多,能體會老師的苦衷嗎?”那同學沉默不語,淚水漸漸出眶,口中囁嚅道:“我想將來當個作家。”學生的輕輕一語,我的心頭一震:透過學生的作業可以看出這位同學的學習心態。學生有很高的寫作熱情,自己卻發火抱怨,足見我在大學里學的教育學、心理學還停留在書本上,不能致用。
此后,我對這位同學熱情鼓勵,引導他把幾百字的短文寫好,再逐步學寫長文。后來,這位學生畢業參軍入伍,不久便當上了通訊員,過了幾年,成了一位將軍的秘書。經多年奮斗,他成了一位軍級文職干部。
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影響深遠。它使我悟出一個重要道理: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可以“登堂”,只有在實踐中不斷學習提高,才能“入室”。自己必須牢固樹立教書育人的觀念,不斷錘煉教學的各項基本功。于是,我以零為起點,開始了新的跋涉。我在床頭柜上寫下“情操高、教風實、教藝高、基本功好”十三字箴言,結合工作實際重新學習教育學、心理學以及中外大家論教育的著作,寫下幾百篇教育教學札記,制作了幾千張卡片。三篇談教育體會的文章陸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經十余年努力,算是成了一名比較稱職的語文教師,初步奠定了日后發展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我成了學校語文教研組長,很快投入到“搶救”語文的千軍萬馬之列,用火山爆發那樣的熱情去奪回因“文革”給語文教學造成的損失。其時,我40歲,因超負荷地在各年級上課,喊裂了聲帶,原來在中學、大學曾是“著名的男高音”,擁有“漂亮的音色”,此時喉嚨卻像只破了的砂鍋。
開展教學研究,撰寫教科研論文的熱情,也像久壅頓開的泉水,汩汩流瀉。我邊教學、邊總結、邊研究。初中、高中,畢業班、非畢業班,都有我的“試驗田”。三尺講臺成為我錘煉教育思想和教學藝術的練功臺,教學實踐成為我提煉經驗和提升理論的基石。《試論語文的工具性》《想,是一個總開關》《寫作與辯證思維》等一篇篇論文發表,一本本專著出版。我所研究的著力點主要在語文教法的改革上。
其時,我的引讀論已經初步形成,引寫論亦在醞釀之中。為了嘗試應用“雙引法”教學,我開了一節寫作公開課,聽課者是來自全省的800多名教師。課從“引讀”開始,先讓學生集中“反芻”幾篇課文中有關寫人物的知識,理解作者是如何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精當簡練的筆法,準確生動地勾勒出人物形象的;然后當堂訓練:要求每個同學都為本班的一位同學畫像。由于同學們既是寫作者,又可能是被寫的對象,所以寫作熱情十分高漲。課進行到習作交流階段,一位同學的習作描寫了他的同桌“缺顆門牙”的生理特征,這一細節在文中幾次出現,可惹怒了被寫者,他當即起身抗議,繼而兩人竟推推搡搡,幾乎要扭打起來。風波驟起,滿堂愕然!我也震驚了,40多名學生和800多位聽課者的視線都投向了我:洪老師,你怎么辦?這時我意識到最需要的是冷靜和教育機智,略作思考后我先讓兩位同學坐下,然后把話題意外一轉:“課本中寫魯迅先生的一雙手,十根手指像‘竹枝似的,這一細節美不美?作者為什么這樣寫?”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了:魯迅先生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加上大病初愈,特別瘦,“竹枝似的手指”看起來不美,但這一細節刻畫出一位堅韌頑強的戰斗者的形象,給人美感。討論至此,同學們思竇大開,把“缺顆門牙”和“竹枝似的手指”聯系起來,有的認為“缺顆門牙”正是表現了一個少年的稚氣美,有的認為抓住這一特征寫,會讓人物更具獨特的神采,更顯得可愛……此時的課堂像水燒開了的鍋。最后,寫者和被寫者都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并當場“握手言歡”,課堂內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以后的若干年,我常常回味這堂課,感到雖說勉強完成了教學任務,但只是“險勝”!自己的教學藝術還遠遠未達到成熟的境地,教育機智還遠遠不足以應對千變萬化的課堂。從此,我邊教學邊總結,繼續提升教學理念,提高教育機智,又邁出一大步。
這段時期,盡管由于我在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上取得了成績,被評為江蘇省首批中學語文特級教師和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但我“三省吾身”“教而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決心繼續從零開始,進一步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修煉教學藝術,使自己成為具有高超教學藝術的真正成熟的優秀教師,能夠進入語文教學的“自由王國”。
隨著教改的深入,我結合教學實踐對語文教學作了全方位、多領域的研究,形成了“五說”(工具說、導學說、學思同步說、滲透說、端點說)教育觀,作了構建語文教育“鏈”的嘗試。但當時,語文教學效率不高的問題,仍嚴峻地凸現著;如何實現語文教學科學化與藝術化的結合,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等課題,尚待深入研究。我再次進行反思,用心尋找問題的癥結,尋找新的零點。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揚州大學,拜訪全國著名的語文教育史家顧黃初教授, 請他為我即將出版的一部38萬字的專著寫序,并告訴他,下一步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深化語文教學方法研究;二是編實驗教材。交談中,還流露出我和我的同事對當前統編教材教學低效的不滿意。顧先生似乎未經思考就脫口而出:“編教材!”這句話使我眼前陡然一亮,于是我和顧先生在他家開起了“研討會”。我回顧了自己七八年中對語文教法的改革,感到雖說觸及了各個領域,但總是深入不下去,關鍵是教材不適合教學。教材不科學,再好的教法也不能奏效。我們討論了很久,最后形成共識:用教材來制約教法,用先進的教材理念改變落后的教學理念。編教材,這確實是一著好“棋”!說干就干,1983年我草擬了教材編寫方案,次年編出教材初稿,并作為實驗課題上報,先列為揚州市科研項目,后又列為江蘇省教科所科研項目。教材編成,親自執教;一輪教完,不是小有成效,而是大有成效。初戰告捷,這一成果像火柴頭點燃了我從事母語教材編寫的熊熊大火,我的人生事業又第三次從零開始。
20年來,我主編了三套經國家審定的初中語文教材,累計發行7千余萬冊。三套教材,與時俱進,呈現出第三套對第二套,第二套對第一套否定之否定的態勢,不斷提升水平,日臻完善,終使第三套教材推行到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教材之一。這期間,我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進入花甲之年,本應“解甲歸田”,頤養天年,但回顧近40年的歷程,我覺得自己的語文教改之路尚未走完。我時年60歲,身體尚可;又擺脫了學校行政事務,獲得了更多的屬于個人的時間與空間;課改正在深入,我自悟到每一個有使命感的改革者不應卻步;更重要的是,自己具有近40年語文教學與教材編寫的積累和感悟,應當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研究。我想到應該從講臺上下來后,再走到書架旁,把“立言為徑”作為進入60歲以后的新追求。面臨著第四次從零開始,我毅然承擔起“九五”“十五”兩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參與該課題研究的人員有中外學者專家近200人,組成一個龐大的學術研究的“非常集體”,而我總是說,我是“小馬拉大車”。“小馬拉大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克己為人的精神,靠的是敬人、信人、融人的準則和藝術,靠的是火焰一般的熱情,靠的是維系人心的人格魅力,更靠的是不斷從零開始自我超越的精神、魅力和勇氣!
而今,由于這個“非常集體”的齊心合力,逐步完成了16卷883萬字關于母語教材研究的皇皇大著。令我欣慰的是,在我六旬以后的10年歲月,出乎意外地獲取了一生最高的成就。
回眸自己50年走過的語文教學、語文教材編寫與學術研究之路,深深感到,如果把人生比作“圓”的話,那么“圓”上的每一點,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每一個終點又都是我的事業的新起點。我時時牢牢記住:只有不斷樹立起“始終是從零開始”的觀念,才能跨越一個個巍巍峰巔。
(江蘇省母語課程教材研究所 22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