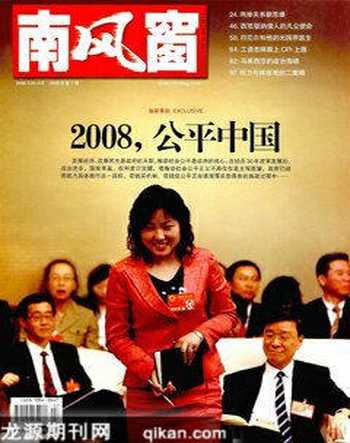傳統在那,文化在哪?
劉 陽
今年兩會上的文化提案,熱點集中在呼吁加強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具體手段則不一。反應較為熱烈的,例如:在小學開設繁體字教育、把京劇曲目加入中小學音樂課、將書法納入義務教育范疇等,代表們不約而同把宏揚傳統文化的重擔壓在了18歲以下的肩膀上。看似著眼于未來,卻過于輕易地放棄了現在。
任何一種傳統文化的死亡,與其說是因為孩子們背誦不出經典,不如說是因為成年從業者失去了以傳統為養料進行創造的能力。也有代表提議,把傳統文化的主要著作和內容“列入各級黨校、各類培訓學校的必修基礎課”,“特別是文化部門的領導,應該盡量去熟悉傳統文化,熟悉了才會有熱情,有熱情才會有動力”。
與成年人有關的還包括:出錢——設立“中國文化產業海外發展專項資金”,用于支持中國文化產品的出口;立法——制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保護、繼承、弘揚法”;以及蓋樓——在山東濟寧建一座中華文化標志城,有代表認為它是“傳承中華文明的千秋偉業”。
另一個更加“成人”的話題是全國政協委員馮小剛拋出來的:“扣子解到第幾粒算色情?”作為商業片導演,馮導并不是在要求創作自由,甚至也不是在要求提高管理的智力含量,而只是要求影片審查制度的規則清晰:你說是第幾粒就第幾粒,但你必須清楚地告訴我,第幾粒?資本在任何市場上都要求制度具有可預見性,以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色,戒》女主角湯唯的廣告片遭封殺,在政協會上,有關負責人并未說明原因,只聲明“對事不對人”。以往的王小帥等導演、以及近5年不得拍片的婁燁,是否屬于“對人不對事”的例子,公眾不得而知。馮小剛認為,中國大片正逐步市場化,但制度層面卻還停留在“計劃時代”,這是中國電影難以同好萊塢競爭的根本原因。
這同樣是發揚傳統文化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環境。民族性的東西是很難靠外人發揚的,而對于海外華人利用其他地區的制度優勢自由發揮創造力的成果,比如李安獲奧斯卡獎、余英時獲克魯格獎等,國內反響含糊。只有李安曾遭表揚,直至湯唯事件為止。
日前,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對媒體表示,“社會主義與宗教問題這個難題被出色地破解了”。他系統梳理了執政黨在宗教問題上面臨的挑戰和政策,并談到,“我們要抵御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宗教領域的西化,就需要……保持和發展民族文化特性”,“要充分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融攝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有益成分”。
曾經對傳統文化的踐踏,客觀上起到了為西方文化及宗教清場的作用。傳統要延續,必然需要新的闡釋與再創造。以老子為例,葉小文說,“對《道德經》的重新審視,是中華傳統文化向現代化、全球化轉化與重塑的一次努力”,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和的理念,和諧的人類健康思想,和諧的治國安邦思想……用東方之祥瑞和氣緩和世界‘文明的沖突”。
如果老子仍然戴著“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為統治階級講解‘南面術”的帽子,只能證明子孫的不入流,自甘墮落。文化原典中的精華,足以滋養當代。
這里有中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反戰宣言——“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不可動輒言戰。即使打贏了也不要得意,為戰勝而高興就相當于喜歡殺人。)
最尖銳的針砭時弊——“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馀;是為盜夸。非道也哉!”(在豪華的辦公樓里衣著光鮮、威風八面,吃到厭食癥,賺到手發軟,另一邊卻農田拋荒,沒錢沒糧,豈有此理,簡直是強盜啊!)
被后世為政者遺忘最徹底的勸誡——“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少點禁忌,政府要有包容力、公信力,才能可持續發展。)
以及最動人的宗教情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無論人們是否良善、誠實,我都以誠善相待。這樣才能擁有善良與誠信。)“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每個人、每件物都有值得珍愛的價值,沒有誰是應該被犧牲的。)“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越助人,越受益;越給予,越富有。)
這些不正是對普世價值最古老的闡述嗎?
正由于傳統不輕易附和“潮流”,所以它才能慰藉人心。在任何一個時代,傳統文化進入當下最迅速而活潑的通道不是贊美,而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