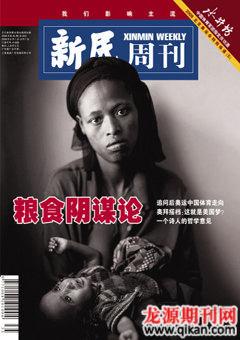誰發動了糧食戰爭
張 靜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這句無意中泄漏天機的大實話幾十年來都未引起世人應有的警覺。
今年以來,世界范圍內至少已經召開了9次以解決全球糧食危機為主要議題的高端會議。
聯合國糧農組織一名官員曾說:“如果領導人一邊高談闊論全球饑餓問題,一邊享用奢華的美味珍饈,看上去可不怎么合適。”
2002年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峰會,就因鵝肝、龍蝦、佳釀,令與會各方事后尷尬不已。但7月初在北海道舉行的八國峰會并未吸取教訓。
這真是一份令最頂級的餐廳和最挑剔的食客都會醉心的晚宴菜單:
開胃前菜:魚子醬玉米卷、煙熏鮭魚夾海膽、洋蔥穌、冬百合配夏薄荷。
第二道菜:竹葉裝飾的扇型盤子上擺著八樣美食,包括用褐藻調味的京都牛肉鍋、配芝麻醬拌蘆筍;鱷梨金槍魚丁;土豆、紫蘇、白煮蛤蜊湯;莼菜鰻魚;醬汁對蝦;烤鰻牛蒡卷;甘薯、香煎刺鰭魚。
接著上桌的是絨螯蟹湯、焗雪斑,主菜是以牛乳喂養的小羊制成的羊排配黑松露。
最后的“夢幻甜點”是咖啡和蜜汁蔬果。
如果再加上午宴的6道菜,每位首腦與夫人一天就享用了24種高級食材,動用了60位廚師。以至于英國《獨立報》不無諷刺道:“討論糧食危機真是一項體力活。”
據世界銀行統計,過去3年來全球糧食價格累計上漲了83%,人類正面臨著30年來最嚴重的“靜默海嘯”:至少有1億人退回到挨餓困境,33個國家面臨糧荒和社會政治動蕩的危險。海地貧民連一盤米也買不起,一日三餐只能以“泥餅干”充饑,糧價高企毫無爭議地成為峰會的熱點議題,但在峰會的餐桌上卻絲毫嗅不出危機的氣息。“富國俱樂部”饕餮盛宴這一極具象征意味的“行為藝術”,多少暴露了他們解決糧食問題的“真情實意”。或者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所言,這本來就是一場“人為的危機”。
“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關于本次糧食危機的起源,氣候變化、油價攀升、生物能源、資本投機早已成為標準答案,“中印需求威脅論”也老調重彈:美國總統布什拋出“印度的中產階層日益富裕”,西方媒體則熱衷指責“中國人開始吃肉了”。
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發展學院周立教授告訴《新民周刊》,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糧食繼能源之后,正成為一種新的賺錢機器和重新劃分世界的地緣政治武器。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品巨頭關心的經濟利益一拍即合,催生出一個龐大的“食物帝國”,糧食危機不過是其擴張的必然結果。
周立曾用了一年時間,跑到美國對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田野調查”。他在一份題為《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的總結報告中指出,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又是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曾任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則言,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這句無意中泄漏天機的大實話幾十年來都未引起世人應有的警覺,而某些國家的確長期將此奉為圭臬。
周立指出,早在1945年,南斯拉夫在鐵托總統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當“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后,美國對智利的糧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連德領導下的大眾聯合政府,卻是致力于農業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連德下臺后,美國的糧食援助很快又恢復了。糧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對阿連德所采取的秘密戰略的組成部分。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 80年代末蘇聯沿著美國指引的方向進行改革時,一位西方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立即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提供多少糧食。
1994年以來,朝鮮連續幾年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對朝鮮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朝鮮必須放棄核計劃,并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
廉價傾銷
美國糧食戰略的推行,在周立看來更多由食品巨頭在前面沖鋒陷陣,首先摧毀的目標是美國原有的糧食體系。
2007年9月,周立在美國中北部做農場調查時,有一晚住在衣阿華州的農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畝土地的小型農場,深有感觸地從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麥片告訴周立:“這盒燕麥片在超市中至少賣3.5美元,我們農民只能分到1.43%,僅折合5美分。”
根據美國農業部和部分研究機構提供的資料,農民在1910年還能獲得近40%的食物價值,2006年下降到5%左右。這導致從1930年以來,小農家庭農場破產了60%。
“如果我們認真看一下恰亞諾夫、斯科特和黃宗智基于蘇聯、東南亞和中國的實證資料研究,并親自到田間地頭去問問農民,就會體會到并不是他們的競爭力不如產業化農場,而是政府只對產業化農場實施高額補貼。”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曾建立過 “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使得糧食價格曲線平滑化,也為政府帶來了巨額的財政盈余,曾得到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但在少數糧食寡頭多年的動員和游說下,1996年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倍受懷疑的糧食儲備制度,為控制了上、下游的食物集團大開方便之門。
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商品化農產品的補貼自1998年以后,規模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左右,其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公司,基本被糧食寡頭盡收囊中。而大量的農業補貼,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從而使得少數幾個食物集團贏得了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競爭力——廉價糧食基礎上的廉價食物體系,通過“無縫的縱向聯合,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鏈”,營造了一個由他們所掌握的“食物帝國”。
“這個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周立舉例說,像美國農業部居然會幫助開發種子絕育技術,而這種生物工藝,只會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
資本化的食物集團,當然不滿足于只控制了本國的食物版圖,它還要進一步擴張疆界。 “近些年糧食的對外援助和自由貿易,就是它擴展疆界的很重要的表現。”
蘇珊·喬治的《糧食政治入門》一書,詳細描述了美國如何成功地用糧食援助,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非洲、拉美等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淪為附屬于美國消費需求的經濟作物園。
“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直接與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家食品集團——Cargill的執行總裁有關。他代表公司利益,卻出任美國的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美國農業首席談判代表,極力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使得農產品自由貿易于上個世紀90年代成功地納入世界貿易組織體系。”周立說,糧商還與政府攜手影響國際組織。當初海地允許美國米進入,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發放貸款的硬性條件。
仗著巨額農業補貼的底氣,“食物帝國”繼續以屢試不爽的“低價傾銷”策略攻城拔寨。
“不僅美國,世界10個提供農產品生產支持的主要經濟體,政府用包括補貼在內的各種方式,對農場提供生產支持,支持總額達到了2795億美元,總補貼份額占農場收入的比重達30%。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生產、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強國提供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
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好像是各國農民在跟美國的農民競爭。可是美國的產業化農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貼。正如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發表文章所稱:“我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
菲律賓自然條件優越,境內還設有著名的國際水稻研究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是稻米出口國。但自上世紀70年代起即轉向發展高價的外銷型經濟作物,逐漸放任本國的糧食生產,道路建設、農機、水利、作物改良、研發、推廣等方面嚴重落后,生產力僅以每年1%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到2000年間的增長幅度甚至低于1%。隨后又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開放市場,進一步打擊了農業部門的生產力。
面對是否有陰謀論之嫌的質疑,周立反問道:“如果沒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業利益,以及美國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個人前途考慮,一個國家為何要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強制機制,硬把自己的廉價貨品‘補貼給全世界?” 這也可以回答歐美國家都倡導自由貿易,為什么烏拉圭回合都變成多哈回合了,在削減農業補貼問題上始終不肯妥協?
美版“戰國策”
既然“食物帝國”的擴張建立在低價傾銷的基礎上,去年以來糧價為什么會突然暴漲?
周立表示:“食物帝國的主導者,在全球糧食貿易體系中,漲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經做到了贏家通吃。”
2005年,布什總統簽署了《能源政策法案》,提出到2012年美國可再生能源要達到75億加侖,拉開了玉米行情暴漲的序幕。2007年底,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案》,該法案要求減少石油進口,推動美國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達到360億加侖,連鎖性地推動了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
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研究員曾左韜博士認為,“乙醇戰略”完全是管仲治魯梁之謀的美國版。
當年“春秋第一相”為拿下魯梁二國,先令齊國老百姓全都穿上了絲制衣服(服綈),齊國絲價大漲。管仲還特意對魯梁商人說:“你們給我販來綈一千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金;販來萬匹,給金三千斤。”吸引得兩國國君都要求他們的百姓織綈以賺取高利潤,從而放棄了農業生產。一年后,管仲又不讓百姓再穿綈,并不準賣糧食給他國。十個月后,魯梁糧價高漲,人民餓餒相及,即使兩國國君急令百姓返農,也為時已晚。齊國不費一兵一卒即令兩國歸順。
曾左韜說:“兩千年后斗轉星移。玩這種糧食策略的變成了美國人。”
第一步:先大量購入低端工業產品,誘使亞洲忙于生產衣服、鞋子、電視,為美國“織綈”。同時廉價出口糧食把亞洲農業擠垮。由于工業化占地導致耕地的消失, 日本谷物的生產水平從頂峰下降了33%, 韓國下降了31%, 臺灣地區下降了19%。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更重視工業,同時削減了對農業的支持,農業總的生產率和產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狀態。近兩年大米主要出口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農業占GDP總量下降到很低水平,農業發展不受重視而長期停滯不前。” 周立表示。
等激烈競爭使得工業品越來越便宜后,美國開始減少農作物出口,導致農產品價格暴漲,從而打擊其他國家的經濟,實行“管仲戰國策”的第二步。但是生產出來的糧食不能浪費,于是“能源自足”成為最好的借口。以增強能源安全的名義推行生物能源計劃。
美國聲稱要通過生產乙醇來實現能源獨立,但分析表明,生物能源計劃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目前利用糧食提煉乙醇僅能滿足3%的汽車動力需要,即使把美國出產的全部糧食都用來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僅能滿足美國18%的需要。”
盡管乙醇生產既賠本又無法滿足能源自足,美國政府仍然全力推動。有資料表明美國計劃最晚在2022年,將其1/4的玉米作物用做生產乙醇。
2006年,美國投入4200萬噸玉米生產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費水平計算,足可以滿足1.35億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國若以玉米生產150億加侖乙醇,需耗用1.8億噸玉米,足夠5.8億人口吃一年。
幾年前美國剛開始推廣生物能源戰略的時候,北大光華的MBA課堂上曾發生過一場爭論。有學生對來自耶魯的美國教授說:“就在饑餓導致許多非洲窮人失去生命的時候,美國耗費大量的糧食生產汽油,難道不是對全人類的犯罪和不道德?”這位能夠影響美國政府決策的著名教授答道:“美國是一個石油美元國家,從來都是利益至上。”
周立分析,制造全球糧食緊張有利于歐美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發展生物能源對美國能源貢獻微小,但通過人為地在世界范圍內制造糧食短缺,對拉動糧價收效巨大。美國通過玉米提煉出乙醇從而節省的汽油不到當年存儲量的1%,卻讓全球糧價上漲了近四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目前糧食價格飆升,源于糧食需求劇增,而接近一半的需求增加源自發達國家對生物能源的追求。
乙醇戰略對美國實為一石三鳥之計。 “美國缺燃料但多糧食,把多余的糧食轉化為燃料有利于減少美國能源對中東石油的依賴,該戰略符合美國的利益。提高農產品價格可以降低美國的農業補貼,從而降低美國政府的高額赤字。”另有觀察人士告訴記者,糧食漲價對糧食進口國傷害最大,可以通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遏制他國崛起的速度。糧價危機也有利于美國趁機推廣轉基因作物。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生產國。綠色和平組織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八國峰會召開前,以美國為首的轉基因利益集團就緊鑼密鼓地準備鼓吹“轉基因技術增加糧食產量”,并希望各國政府放寬對轉基因技術的監管。
十幾年前,全球“ABCD”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已經開始了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在“食物帝國”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時候,如何逃脫被控制的命運?周立說:“中國已經選擇了在農產品貿易上加入了WTO,又無力和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國進行巨額補貼的競爭,中國在涉農以及食品體系的領域,可以作為的空間已經很小。由于中國大約65%的糧食生產是農民不計成本為自給自足而生產,使得中國總體上的糧食自給率還比較高。為確保糧食安全,中國應該對糧食自由貿易謹慎對待,堅持自給自足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