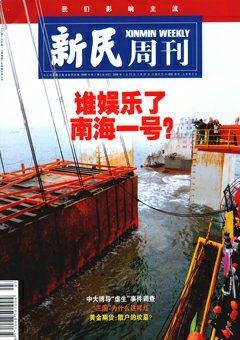“讓”和“使”的天淵之別
孫 滌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精粹是“讓”一字。
鄧公高瞻遠矚,向來言辭簡賅而意味深邃。他開創中國新格局的語錄中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尤其令人琢磨。
“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貧”除了與“富”相對稱,則有其絕對的含義。一個行將溺水的人會感到氧氣的絕對“貧乏”,一個瀕臨凍餒的人會體驗衣食的絕對“貧乏”,然而整個社會的居民卻不可能產生同樣“富”的感覺,即使從生存需求的角度他們已是“足”的。人們所謂的“富”,必是看到他人,特別是鄰人,能夠支配顯著多于自己的物質(往往以錢財來衡量),從而產生的既羨且妒的情緒。被羨被妒的對象,即所謂“富足”者,始終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無論社會進展到什么程度,情況都將如此。因而,使全體人民同等富足的意愿,即使好意可嘉,并沒有持久的可操作性。這類意愿到頭來不但會斫傷人們的進取心和創造精神,也會令整個社會彌漫著普遍貧困的感受。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精粹是“讓”一字。不少持批評姿態的人之所以沒能看穿問題的癥結,是把“讓”(allow)混淆成了“使”(make)。“讓”糾正了前此的“不讓”,是要為扭曲的禁錮松綁。“讓”和“使”的一字之差,乃有天淵之別。我們在討論社會公義或物質分配等大問題時,不可不明察之。
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固然能帶來較多的稅收,增加就業機會,提供新的效用,但更積極作用在于他們能帶動競賽,造成良性互動,形成社會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看到旁人相對的富足而生的羨妒之情,說到底,是市場競賽的根本動力。“羨”和“妒”,在語意上雖有其固定的褒貶,實際上卻難以界定。也許我們能說“妒”的程度較為強烈,容易導致破壞性吧。先賢的原典,例如《圣經》或《論語》,對“妒”都大加貶斥,視為最難祛除的罪惡(sin)。不過適度的“妒”,在推動人類社會奮發向上起著很大的作用。
在此僅想提示這個問題的兩層意思。其一,財富在一部分人手中的集聚是有限度的,物質資料如果不能擴散出去,大部分不富裕的社會成員就無法有效地消費生產的成果,經營活動就不能存續,更難擴展。貧困若以擴大的規模在另一端積累,必將導致社會的崩解,應驗馬克思的經典論斷;其二,財富效應的社會擴散如果不夠迅速的話,那么社會很大的群體將感到屈辱,“人的尊嚴”將備受打擊。諾貝爾獎獲得者印度裔經濟學家森所定義的“免除貧困而能體面地生活的自由”,正是這兩層意思的結合。
由此可知,已經付諸實施的新版《勞動合同法》將接受雙重的檢驗。一方面,它應該繼續“讓”一部分人更有干勁、更有雄心、更不計較風險、更富創造潛力以及更幸運的人能夠先行一步。30年來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卓有成效,端賴于斯。另一方面,它應該有助于迅速推動社會財富的擴散效應,“使”越來越多的人體面而尊嚴地生活和工作。檢驗的標準,簡而言之,應該是: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是否能因之而變得更強還是遭到削弱。勞動力高度自由的流動不但促進良性的競賽,而且讓人們有更豐富的選擇,既幫助“把餅做大”,也促進“餅的分享”。反之,它會制造各種扭曲的博弈,增加經濟運作的摩擦,甚至會造成漠視輕慢法規的尊嚴的結果。這種損失是整個社會所承受不起的。
再來看前一陣的“華為風波”。出乎決策者的預計,“華為自選去留”的方案招致員工的強烈抵制,員工們對“集體辭職”的要求既不認同,對按工齡年均3萬元的“充分補償”也不領情。許多企業對于將給經營帶來實質影響的新法漠然處之,恐怕根本上就沒有嚴格遵守它的打算。不難預計,嚴格新法的執行會增加形形色色的摩擦,成本,尤其是尊重法規的成本,不容低估。
新版《勞動合同法》作為一項經濟的基本法規,將深刻影響企業、勞工、就業、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其意義將遠較眼下的一些問題,諸如匯率改革之類的,要深遠得多。華為一案,有其積極意義,它將引起對政策的機會成本的嚴肅的思索和檢討。以情緒用事作道義譴責,是過于簡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