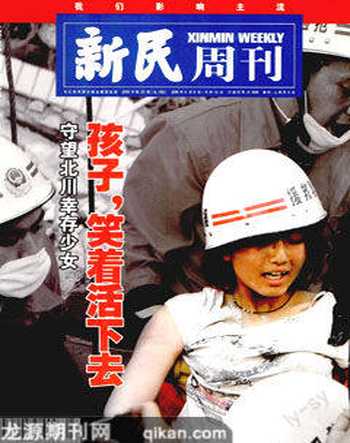“還不夠清貧嗎?”
何映宇
阿城專訪
他編劇的《吳清源》和《貞觀之治》在放映、播出后影響似乎也沒有想象中的大,小說集仍然在市場上看得到,但是關于阿城的新聞卻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這樣隱居于都市之中。
自從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中露過一回臉,阿城就幾乎沒有再在公眾場合出現過。他編劇的《吳清源》和《貞觀之治》放映、播出后影響似乎也沒有想象中的大,小說集仍然在市場上看得到,但是關于阿城的新聞卻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這樣隱居于都市之中。
這些年來,少見他寫作小說,甚至連一度風靡坊間的隨筆也停了,專心加入編劇的洪流,從謝晉的《芙蓉鎮》開始,在田壯壯、侯孝賢、嚴浩等人的影片中擔任編劇。事實上,他本人如果去做演員一定也會很成功,寧瀛有回和查建英議論阿城:“應該有人扛一臺攝像機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
對于阿城不寫小說寫劇本的事,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很不以為然,說到激動處不免言辭激烈,他對記者說,他不能同意阿城關于作家是乞丐的論調,“一個作家應該忠實于他的事業,不應該把錢看得那么重。為什么不在寫劇本的同時也寫小說呢?我不能理解,這些中國作家都是怎么了?”對此,阿城反駁說:“還不夠清貧嗎?我抽的煙都是大前門,太貴的我抽不起。”
阿城也許屬于歪打正著變成作家的那一類幸運兒之一。他最初的身份是個業余畫家,在“星星畫會”的回憶文章中能看到阿城的名字,并不顯眼,但總少不了他這一號。“星星畫會”的嚴力對《新民周刊》記者回憶說,“阿城,時任某文化機構小職員,因其父鐘惦棐牽連,童年、少年頗為不順,那時,他用極美的線描為《今天》作插圖。”他說阿城在星星第二屆展覽上展出的是線描,很干凈的線條,形象把握很準確。
星星畫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這種成功似乎并不屬于阿城,或者說對他的影響是有限的。那些畫油畫、搞雕塑的因為材質的關系,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還有天生的演說家馬德升,和他們相比,他依舊寂寞。
寂寞中,沒有什么比文學更為強大。他1969年在內蒙古阿榮旗插隊,插在一個叫“東新發”的小屯子里,第一次讀到食指的《酒》,就開始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且喜歡上了它。這應該說是那時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他也一樣,反反復復地看,感動。他特別推崇的另一位詩人是根子,那首傳誦一時的《三月與末日》是他全部寫下的九首詩中的一首,他愿意跟隨詩人一遍遍詰問:“春天,溫暖的三月——這意味著什么﹖”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寫小說,寫《遍地風流》。
1986年,正當阿城發表《棋王》后在國內大紅大紫的時候,他卻毅然選擇了出國。
在美國,他白天打工、刷墻,晚上在家寫作,問他累不累,他的回答很簡單:“不累,工具那么多。有刷子,長的短的都有。”問他即使是刷墻為什么不找個能發揮一技之長的,至少也畫個圖案,搞個涂鴉,不要光顧著刷白墻,多單調啊,他回答說:“別費腦子了,就是不想動腦子。”
在海外,他和陳丹青兩個人成了死黨。陳丹青曾對記者說:“我從很早開始不太看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我只看少數幾個人的東西,阿城、王安憶都是朋友,他們寫完了會把他們的作品寄給我看。阿城剛開始寫作,他寄來的都是原稿,大概十來天就到了,然后就給他回信。他比我大四歲,當時我31,他35。”那是1986年的事,“阿城在我寓所住了斷斷續續有半年吧,我們睡在可以攤開的沙發上,天亮醒來看見阿城就在旁邊,簡直不能相信。”
我不會下棋
記者:你是電影《吳清源》的編劇,你喜歡圍棋嗎?《棋王》寫的是象棋,也喜歡下象棋?
阿城:圍棋和象棋我都不會。小時候父母不讓下棋。
記者:那吳清源先生怎么會讓你來寫《吳清源》的呢?
阿城:誤會吧,他誤以為我很懂棋。
記者:你不懂棋的話,寫劇本的時候是否也有困難?
阿城:如果一部電影完全在描寫下棋的情景,誰來看呢?觀眾和我們一樣,大多數都不會棋。
記者:怎么會開始當編劇的?我記得有一篇文章寫香港的前衛戲劇導演榮念曾將您介紹給侯孝賢,是這樣的嗎?
阿城:他將侯孝賢的片子介紹給我看。他也曾經把侯孝賢的片子推薦給陳凱歌,陳凱歌不以為然,我就覺得《童年往事》非常好。就這么個關系。80年代初的時候,誰買得起錄像機和錄像帶?只能是這些香港人,他們有錢,所以能讓我們接觸到一些港臺的電影。
記者:你當時就覺得很不錯?
阿城:是挺好的。我突然發現中國也有像歐洲新現實主義電影這樣的作品。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有許多在50年代國內都放過,比如《偷自行車的人》、《羅馬十一點鐘》,可惜就是中國沒有跟上去。那時影評對這批電影也都是正面的報道。
記者:那時候您還小吧?
阿城:那時能看懂電影了。雖然中國和意大利的關系很好,但是中國人不愛看意大利的這類電影。中國觀眾是好萊塢訓練出來的,最成熟的觀眾是上海觀眾,電影院門口賣手絹,知道你們愛哭。
記者:您父親也研究電影,對您的童年影響大嗎?
阿城:他是管電影的,算是領導,但實際也管不了什么。劃成右派之后他就勞改去了,他跟我們說不上話。等我長大了,我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電影觀念對我并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有一點,我父親對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也是很喜歡的,你看他50年代寫的影評就知道了,對他們的評價都很高。
我做很多事情
記者:你現在既寫電視劇,又做策劃。
阿城:我做很多事情。這些只是你們看到名字了,不怎么掙錢,維持基本的生活,還有很多你們看不到名字的事情。
記者:那么寫電視劇、電影劇本是不是完成就好,就當交差?
阿城:你們不太了解編劇這行當。特別麻煩。經常導演說這里要加兩句廢話,要磨很久。要磨很久是什么意思?好比說原來你一年可以掙到十萬,現在可能要磨五年。
記者:自己編劇的電影會去看看嗎?
阿城:一個電影編好劇,可能七八年才拍出來,人家早把你給忘了。
記者:近期寫了一部電視劇《貞觀之治》,怎么會去寫歷史題材的?
阿城:因為大家對歷史都不感興趣。之前的歷史戲那是歷史戲嗎?都是戲說。我說的是正史。
記者:對現在的文學期刊、小說有了解嗎?
阿城:基本上不看了,也不太關注。
記者:你說對當代文壇完全不了解,但如果有朋友新出了一本書,送您一本,您總會去讀讀吧?
阿城:我一般都謝絕此類贈書。我要買,不要送。朋友的話我們應該幫助他,而不應該占他便宜。他的樣書可以送給企業家,企業家對他幫助更大。
記者:你說作家是乞丐。據我所知,進入體制內也可以糊口,你是特別看重這種體制外的生活方式?
阿城:我認為在體制內糊不了口……
記者:那我們試著過一種清貧一些的生活呢?
阿城:還不夠清貧嗎?電影我都不看,那樣的票價我承受不了。
不需要做多余動作
記者:在洛杉磯的生活是怎么樣的?
阿城:就是因為不認識人,所以在洛杉磯的生活比較好過。在中國是你必須認識人你才能過,關系是一種資源,而在美國不是,不需要做多余動作。
記者:你還是有偏愛的文學作品,比如木心的作品,你個人就比較喜愛。
阿城:木心的作品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知識構成的一部分。反過來,現在的文章,其實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儲備也能看。面對木心的困境,其實是一個新中國的讀者所面臨的困境。
木心、陳丹青的作品會有新鮮感,那是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我們的不同,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相似的,是同構的,看到第一句話就知道他下面要說什么,就是這么個情況。
記者:但是一個美國人,他的知識結構和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肯定是不同的,這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他的文字一定是優秀的。
阿城:先不要說他是優秀還是糟糕的,不要挑挑揀揀,先拿進來,沒多少菜了,還挑什么?挑的結果肯定是營養不良。
記者:說到知識結構,同樣是亞洲人,你覺得日本的電影如何?
阿城:日本電影大師太多了,不要老說黑澤明北野武,他們是拍給西方人看的。在日本,只有沒水平的導演才把獲獎當一回事。文學也一樣,日本的劍俠小說一出來,金庸那些小說就不用討論了,也沒什么好討論的,沒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