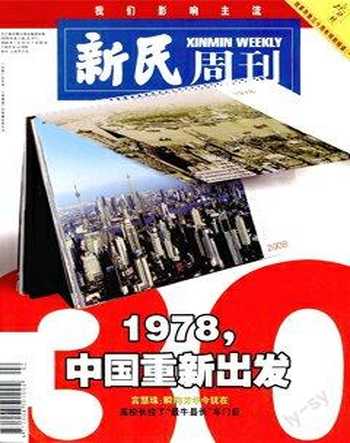大眾住房模式亦可借鑒“共有”
李澤旭 楊 江

共有產權模式可以向年輕創業者在內的階段性購房能力不足的群體延伸,不必將他們推向單一的貸款購房途徑。
作為經濟適用房共有產權模式雛形的提出者,南京市建委研究室主任陸玉龍認為,江蘇試行“經濟適用住房共有產權制度”改革目前局限在拆遷戶范圍。“共有模式可以有多種形式的轉換、延伸,針對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共有模式,惠及更廣意義上的夾心層。”
“我們一般把位于廉租住房標準線之上,但又無力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低收入人群定義為夾心層。但這是不完整的。”陸玉龍認為,根據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將人群劃分為兩個極端:一是社會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少部分人,擁有社會大部分財富,他們的住房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解決;另一個極端是少部分收入極低的人群,他們的住房需要通過政府公共財政服務以廉租房的形式解決,對他們而言,房價高低沒有現實意義,因為根本就買不起。
剩余的中間人群占人口多數,與兩個極端構成紡錘形社會結構。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福利社會沒有形成前,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是希望能夠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產權房的。但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無法在短時間內積累到可以全額購買住房或承受還貸壓力的水平。
陸玉龍認為,這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夾心層”,既包括目前享受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的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不享受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的中等收入人群。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提出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
陸玉龍認為,這里的經濟適用住房也應該是面向兩個極端之外的所有中間階層。而經濟適用房共有產權模式最終也應該向大眾住房模式轉變,讓更多人在共有模式的幫助下,在房屋產權上實現從“我們的”到“我的”。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成功實現階層化,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與必需,而中國的中間階層眼下正處于向中產階層轉化的塑性階段,分布在社會各個行業中,是社會財富積累的具體執行者。
理論界認為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中產穩,社會穩,現在中產不穩主要就是住房不穩,工資收入上漲與房價上漲速度不成比例,高房價使許多中間階層買不起房或淪為房奴。陸玉龍認為,共有產權模式解決“夾心層”住房問題,增加了個體穩定性與社會穩定性,增加了人們的幸福感,且有激勵作用,有利于擴大中產階層。
他闡述,共有產權模式可以避免財政資金投入住房保障“有去無回”,由于政府因投入而擁有產權,使得“共有產權房”在資金和實物上具有多次循環利用功能。“共有產權房”與商品房價格趨向一致,不僅避免了投機行為,且客觀上避免了“貧民區”的出現。
現有經濟適用住房實際操作中,由于政府財力緊張,往往首先從土地上降低成本,因而基本上遠離主城區選址集中建設,交通落后,學校、醫院、商業等配套設施不完備,周圍區域產業欠發達,就業機會少。造成中低收入家庭入住經濟適用房小區,普遍面臨就業難、就學難、就醫難等問題,大部分家庭需要長距離往返市區,不僅不方便,而且居住成本提高。
在他看來,“共有產權”“變送為扶”式的救助,價格與商品房相當并不會加大購房者難度,政府完全可以根據購房者家庭可支配收入和購房者的愿望劃定雙方占有產權比例。
“沒有或減少了住房貸款,也減少了購房者因房貸產生的壓力。購房者可據自己經濟實力,分期購回政府擁有的那部分產權。”陸玉龍認為,隨著新的住房保障體系的建立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適用房積累效應和循環利用機制形成,我國住房保障制度將向更積極、更高級的形態轉變,這一轉變的基本標志是,社會住房保障對象除了目前的弱勢群體外,還將惠及年輕創業者和來自農村的城市新移民。
“共有產權模式可以向年輕創業者在內的階段性購房能力不足的群體延伸,不必將他們推向單一的貸款購房途徑。”至于共有形式,他認為還可以是政府與供房者共有、企業與購房者共有、慈善機構與購房者共有,甚至是加上第三方銀行的三者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