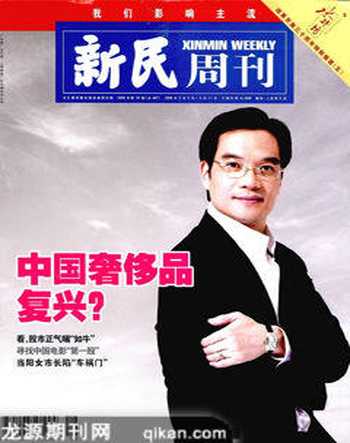韓國財閥為何一再犯案
詹小洪
韓國財閥們不端違規行為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證將企業經營權順利交到后代手上。
4月28日,隨著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正式向集團經營理事會提交辭職書,這個韓國企業巨頭及其錯綜復雜的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引起公眾極大的興趣。
據韓國銀行資料,韓國最大的30個家族企業集團(也稱財閥)幾乎控制了40%的韓國經濟。近年一再爆出的經濟大案、要案既震驚了世界,更為他們充滿東方色彩的獨特企業治理結構做了個最好注腳。

“韓國折扣”稱號的由來
2004年底,隸屬于韓國總統府的機構國家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了一個“財閥集團股份族譜”,將截止到當年4月1日資產達到2萬億韓元(約合20億美元)的36家企業集團作為對象,列出了集團總裁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和旁親在集團占有的股份。通過此圖譜,人們能夠對這些大企業集團中,總裁及親屬的股權明細和他們對旗下子公司通過交叉持股的公司治理結構狀況一覽無余。
此圖譜揭示,這些韓國大企業集團總裁持股率平均不滿2%(1.96%),若加上他們親屬的2.66%股份共4.62%的股份,卻能牢牢控制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權。如決定企業發展方向、制定企業戰略、市場開發營銷、子公司總裁任免、公司利潤分配等等。在韓國企業集團中,總裁絕對是一言九鼎的。值得注意的是,越大的企業集團總裁持股率越低。如三星總裁李健熙0.44%、LG總裁具本茂0.83%、現代汽車總裁鄭夢九2.85%、SK總裁崔泰源0.73%、韓進總裁趙亮鎬2.92%。
每個大企業集團旗下都有很多子公司,有的是上市公司,有的是非上市公司。這36家企業集團旗下共有781家子公司,集團總裁在其中469家子公司(占總數的60%)完全不持有股份。公平委員會表示,盡管總裁在整個集團占有股份極低,卻能利用很少的持股率,通過“杠桿持股”行使著近50%的穩定的企業支配權。
本來,在現代公司制度下,股東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發言權及決策權取決于本人的持股率。但是上述韓國大企業集團總裁卻能利用極低的持股率掌握企業經營權,這證明韓國的企業的治理結構存在問題。
這種“韓國式企業治理結構”,常被外界(多為歐美國家經濟界)稱為“前現代式”、“不透明的”、“獨裁式的”、“違反道德的”。
韓國式企業治理結構的最大問題,是經營不透明,信息披露制度缺失。根據韓國《證券交易法》,上市公司的持股情況必須公開,這樣總裁及其企業管理層還比較難做手腳。但非上市公司持股情況大部分是不公開的。總裁完全可以通過非上市子公司之間的相互持股、互相擔保債務等企業內部交易,來達到以非上市公司控制上市公司,進而達到以低持股率掌控企業經營權的目的。
舉例來說,通過“A公司擁有B公司股份,B公司擁有C公司股份,C公司又擁有A公司股份”這樣子公司之間令人眼花繚亂的循環出資方式,來保障總裁對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權。甚至有韓國官員稱,引發1997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企業財團總裁以低股份率控制了子公司的方式,盲目擴張事業所致”。
這種“前現代式”的韓國式企業治理結構往往與政商勾結(如賄賂政要,為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特定候選人籌集秘密資金等)、做假賬、逃稅、秘密繼承遺產、私下授予經營權、暗箱操作、內部交易等負面新聞聯系在一起。據韓國經濟學家分析,財閥們不端違規行為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證將企業經營權順利交到后代手上。
盡管在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漢江經濟奇跡中,韓國大企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些企業如三星、現代、LG早已進入世界500強。但由于有了上述污名,投資者對購買這些企業集團的股票感到擔心(順便提一下,目前三星集團的股份有64%被外國小股東控制),導致韓國公司的股票價值被大大低估。據韓國媒體報道,大概被低估20%。199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際經濟界流行一個詞匯“Korea Discount”(韓國折扣),意思是韓國企業的股價與外國同類企業相比,價值偏低,并將其歸咎于韓國企業脆弱的治理結構。
企業病屢治屢犯
這種病態的企業治理結構歷來為韓國公眾所詬病。在1998——2007年,金大中、盧武鉉兩屆左翼政府期間,都曾推出一系列強硬的財閥(主要是針對資產2萬億韓元以上的大企業)改革計劃。
其一,實行大企業出資總額限制。即大企業集團對旗下子公司的投資不能超過該子公司的25%的股份,以防止大企業的經濟集中程度,保護小股民權益。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出現資產泡沫化。其二,解散位高權重的大企業集團的指揮中樞——企業結構調整本部(后來叫做戰略企劃室)。其三,禁止子公司之間相互持股和相互債務擔保,以防止大企業用低股份率控制企業經營權。其四,提高大企業總裁及其親屬持有公司股份的透明度。其五,實行證券集體訴訟制,實行交易賬戶調查權。其六,在大企業內,實行金融與產業的分離。在以首爾為中心的首都經濟圈內限制投資設廠,這主要是為了保護耕地和保護環境。等等。
這些措施的主旨是:防止經濟集中在少數財閥手中,提高經濟透明度,打擊腐敗,保護中小股民利益,特別是嚴防財閥的第二代、第三代通過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繼承企業經營權。
總的來說,在韓國社會、公眾對財閥的印象并不好。據一次問卷調查,“你對富豪是否尊敬”,竟有40%的被訪者作了否定回答,肯定的只有33%。2005年,高麗大學要授予三星總裁李健熙榮譽博士學位,居然因遭到該校學生的強烈抵制而差點流產。理由是抗議三星公司禁止工會活動,以及通過買賣旗下非上市子公司愛寶樂園股票的手法而讓其子非法繼承三星公司經營權。
面對公眾的批評、政府的限制,財閥以及韓國右翼媒體則認為,這是韓國社會出現的“反企業”、“反市場”情緒。他們尤其對企業出資總額限制條款指責有加,抱怨這個限制會導致外國投資者對韓國企業的敵意收購。
事實上,韓國財閥們從未停止違規經營,近年來曝光的黑幕屢屢震驚世界。
比如,韓國第二大企業集團現代汽車公司。汽車工業是韓國的主導產業,其產值占韓國GDP的十分之一,就業人員有154萬,占全國就業總數的11%。而現代汽車公司產量占韓國汽車總量的80%。
2007年,現代汽車集團總裁鄭夢九涉嫌貪污900億韓元資產,并給旗下子公司造成2100億韓元的損失,因犯了《特定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中的貪污、瀆職罪而被起訴,被判處3年徒刑,緩刑5年。
判決書說:“鄭夢九長期秘密籌集賬外資金并非法擅自使用的行為嚴重妨礙了企業經營的透明性和健康性”。但是法庭又說,“為了保障企業防御權(指防止外國投資者對現代汽車公司股權的惡意收購——筆者注),將經濟波動影響降到最小化,我們不會取消之前允許的保釋決定”,即網開一面,給予鄭夢九緩刑5年。
三星集團一年的銷售額1500多億美元,占韓國經濟總量的15%。其出口占韓國全部出口額的22%,上交的稅收占到全國稅收的8%。三星市值占韓國股市市價總額的23%、上市企業銷售額的15%和利潤的25%。三星公司旗下有60家子公司,其中15家為上市公司。
今年4月22日,三星總裁李健熙因一系列罪狀而宣布集團領導層辭職,并解散戰略企劃室。
李健熙等人曾利用高層干部職員名義的1199個匿名賬戶管理價值4.5萬億韓元的股票和現金,而沒有繳納股票交易中所產生的1128億韓元資產增值稅,觸犯了《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中的逃稅罪。此外,李健熙還被控未向證券監督當局報告匿名股票的變動情況,觸犯了《證券交易法》。
另外,李健熙等人廉價發行愛寶樂園可轉換債券(CB)后轉給李健熙之子李在镕專務,給愛寶樂園方面造成了至少達969億韓元的損失,犯下《特定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中的瀆職罪。這種轉讓令李在镕成為愛寶樂園的最大股東,愛寶樂園是三星集團循環出資結構的核心,這實際上也確保了李在镕的集團經營權。
發行可轉換債券是戰略企劃室得到李健熙批準后主導執行的。李健熙等還被控介入廉價發行三星SDS附認證股權債券,給公司造成1539億韓元損失,讓自己的兒子李在镕得到相應利潤。

案件發生后的各方反應
韓國財閥們貪瀆罪責一旦東窗事發,往往都會采取一系列補救措施。
其一,捐款回報社會,所謂“花錢消災”。如捐出自己等值于涉嫌貪污或逃稅的款項,用于建立社會救助基金、建立學校,或者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如鄭夢九捐出1萬億韓元(相當于10億美元)。李健熙更將4.5萬億韓元悉數捐出。
其二,總裁或當事企業首腦辭職,通過電視向全國國民謝罪。在現代汽車集團和三星集團兩次事件中,通過電視,我們都看到以鄭夢九為首的數十名現代集團領導、以李健熙為首的十數名三星集團領導們,分別神情嚴肅、整齊劃一地向電視觀眾低頭謝罪的鏡頭。其意義和影響絕不亞于一個政府總理的辭職。三星總裁李健熙從此退至幕后,其子李在镕也辭去三星集團中處于旗艦地位的子公司三星電子公司客戶服務總管一職,“白衣從軍”,去開辟海外市場,為今后登上集團總裁寶座積累一些歷練。
其三,許諾為振興國家經濟作出貢獻。如擴大投資、增加招收新員工名額等。
其四,落實政府屢屢要求實行而企業一直當作耳邊風的政策。如解散曾經策劃過違規行為而被社會公眾深惡痛絕的企業中樞——戰略企劃室。實行金融與產業分離。
那么,韓國各界對財閥們紛紛“落馬”的反映又是怎樣的呢?
首先,提起公訴的檢方和法院往往都是重查輕判。接到財閥們涉嫌犯罪的舉報后,大法院都會成立獨立的特檢組,在偵查過程中一絲不茍,嚴格收集罪證。但最后的判決書往往都有肯定現代汽車和三星集團在發展韓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措詞,然后加上一句“為了振興國家經濟”,“考慮到當事人這樣做是為了企業的經營權不至于旁落”,“他的問題與普通瀆職罪不能簡單等同”,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能機械地應用,要“適當考慮個別特殊性和時代背景等”,道出從輕發落讓當事人免受牢獄之災的理由。我們從前些年韓國財閥SK集團總裁因涉嫌做假賬被判刑3年,法院也給予了緩刑,法院去年對鄭夢九、今年對李健熙的判決不難得出此規律。
其次,為犯事財閥辯護的多是所屬企業本身及有財閥俱樂部之稱的“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等團體。
現代汽車集團和三星集團為自己申辯的主要理由是:總裁們之所以違規操作,多是為了防止外部尤其是國外投資者敵意收購本企業,以保證經營權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抱怨韓國遺產繼承稅率過高,繼承者無力用現金交納,如用股權抵稅款,又會使自己在企業的股份率降低,致使敵意收購者趁虛攻擊,所以才導致逃稅;如果讓總裁們下獄,企業正常經營必然中斷,這樣只會使韓國企業的外國同行競爭者幸災樂禍。
但韓國公眾通過現代汽車集團和三星案件,則會感覺法律面對有錢有勢的大企業無能無力。一是避重就輕,沒有采信關于三星集團籌集秘密資金賄賂政要的舉報,盡管媒體披露了有被賄賂人舉出了三星集團送禮的鐵證。
二是覺得企業的過去業績成了“減罪符”,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們認為,韓國是金錢凌駕于法律和正義之上的社會。法院對三星案的判決迎合了新總統李明博的“親企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三星案件的爆料人金勇哲原來是三星集團中樞戰略企劃室的法務組組長。他背后的支持者,是代表韓國社會良知的宗教團體——天主教實現正義司祭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