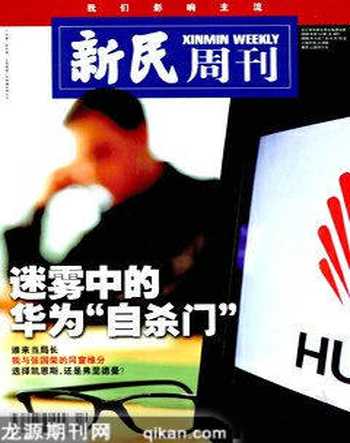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張立國
楊 江 李澤旭
3月下旬的一個午后,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系主任章友德教授與《新民周刊》記者就華為“自殺門”進行了系統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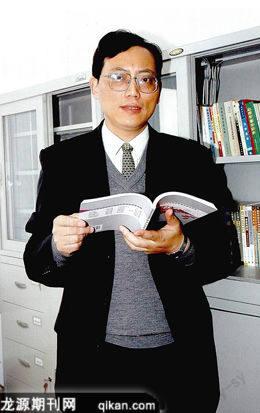
怎么看華為企業文化?
章友德: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企業更多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在華為這樣的股份制企業,全民持股,員工在企業中的經濟地位與掌有的股權多少具有最密切的關聯。
這樣一個背景下,傳統的國有企業中管理者與勞動者的關系,變為了新的環境下資方與雇傭者的關系。資方為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須把所有的員工看作實現他企業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是說,人不再是一個目的而是變為一個手段了。
應該說,華為是30年來中國企業產權變革的重要成果。經營者責任心更強,追求利潤意識更強,較之過去的企業管理者而言,更具有持久的動力。華為走過的艱難的創業道路,給華為所有者或者說任正非提供了一個經驗,那就是一切都是在叢林法則中打拼出來的,他因此對自己形成的企業文化高度認同甚至依賴。
在華為看來,市場化改革、經濟轉型的過程,就是要靠高收入、精英人才、優勝劣汰。而且現有的業績在管理者看來更證明了他的企業文化是有效的,并且會通過內部培訓強化所有人接受這種文化。
一個充滿競爭的群體里,就不會有一只懶惰的羊出現,人人都在奔跑,滯后一步,就會被后者踩死,但前進呢,就是累死。這樣的企業文化是缺少人文關懷的。
華為不僅把員工變為了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且把人的惡的一面,也就是人人都是競爭對手的一面激起了。應該說競爭意識是積極的,但要把握度。
這種競爭意識把人所有的潛能最大限度釋放。但人終究不是狼,企業的這種榨取耗盡了員工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犧牲了家庭、健康,淡化了人的情感需要。華為有6萬個員工,每個人成長的環境不同,這些不同的個體到了這個環境中,必須按照他的企業文化全面適應,每個人的身心都將接受這個新的企業文化的考驗。
這實際是一種外部成本或溢出效應,員工本人的過勞、心理疾病、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親子教育不足等問題,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員工和家庭集中承擔了。如果仍然對這種“普遍現象”長期漠視,最終將導致更加難以彌補的社會后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是疲憊的,但顯然又是矛盾的,因為滿足于這里的收入,滿足于這個來之不易的工作崗位,尤其是在一個好企業是稀缺資源的情況下。
章友德:華為的高層正在用一種信念,即,企業有高遠的目標,你們每個人都有高遠的志向,只有在我這個企業你們才能實現,促動人人都把自己內在的最大的潛能釋放出來。這個時候,任何人主觀上都是不愿意成為弱者的。但問題是很多人是適應不了的。華為要和國際對手去競爭,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公司,但它不知道的是人家怎樣成為那個公司的。是不是都像他這樣把人和人變為叢林法則,只有競爭、付出,而沒有相應的回報,我指的不僅是薪水,還包括人的精神世界。
實際員工可以整合成一個更好的具有協作精神的團隊,未必都要劍拔弩張。
《新民周刊》:但為何很少有華為內部員工質疑華為的企業文化?
章友德:我們注意到在他們參加培訓的時候就已經被灌輸了這種企業文化。每個員工在進華為之前,已經完成了一個自己的社會化的過程,他也是在一路競爭中最終走到華為的,所以他其實潛意識是認同華為這種企業文化的。所以你一方面看到那么多人身心疲憊,但有多少人把矛頭對準華為的?外部看法歸外部,但是企業內部呢,員工最多說壓力大。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新民周刊》:華為的這些精英們為何反倒如此脆弱?
章友德:這涉及“個人的自我預期”,人的需求層次多樣化,最高的層次是自我實現,華為的員工都是在需求的最高層次上,都是有自我實現預期的。我相信,大多數人是認為只有歷經了華為的歷練,才會有自我實現的基礎,一是在華為晉升,二是積累基礎、資金或者學到管理的經驗將來自己創業,甚至一些人進華為就是為了看看任正非是怎么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企業變為一個國際公司的。
所以,華為的員工都是不服輸的,被淘汰的往往被認為是自己適應不了,對于自殺的員工,也往往被其他員工認為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有這種心理的員工,往往都會認為自己不會像張立國、李棟兵這樣脆弱,實際上,如果遇到導火索,他也很可能重蹈覆轍。
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IT人才多是工科畢業,現在的大學課程設置導致工科學生的知識結構不完整,自我化解、排解壓力的能力欠缺。
《新民周刊》:理想的狀態是,企業內部建立相應的機制,當個體遇到危機,需要幫助時及時干預。
章友德:但華為是不崇尚弱者的,華為是一個強者文化,把不適應的人看作就是應該被淘汰的,甚至體制設置就是為了把這些人淘汰。這種文化被灌輸、強化,最終都認同后,內部再沒有人去指責華為。大家都認為外部的批評是因為不了解華為,甚至是誤解了華為。所以華為一直對外界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我內部員工認同我的企業文化啊,而且這個企業是我自己的。
任正非早就說過,媒體說你好,你不要高興,媒體說你不好,你也不要生氣,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這樣類似的話。這說明他有足夠的自信,他相信自己這樣一個企業文化訓練出來的一支團隊是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的。
當華為確定了發展目標后會將全部的壓力,用企業文化的方式逐層分解,但層層分解目標,很可能最終層層提高目標。你會發現最終壓力最大的是剛進來的員工,華為倒下的大多都是這類人。
《新民周刊》:可華為也會覺得冤枉,那些人都不是公司直接原因導致非正常死亡的啊,你可以質疑我的企業文化,但是你不能說我的企業文化就是兇手啊。
章友德:對!這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不能因為是華為的員工自殺了,就說華為是因,自殺是果。那我們又怎么來分析呢?
華為的用工制度其實都是符合規范的,加班給加班費,不拖欠工資,它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個員工自己選擇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不是我企業單方選擇你的吧,也是你選擇了我華為吧。
實際上這樣最終把人看作手段了,人的需求不僅是貨幣,還有生活,還有精神層面的愉悅。但華為把這些都剝離了,轉移為員工自己的事情,而且讓員工認同了與企業無關,是應該自己來解決的。我剛才說了這些都是產品的外部成本,本來就應該是企業來解決的。
我們不能說員工自殺,華為就是直接因素。自殺一定是多因素綜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戀愛失敗,仍覺得在別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溫暖,就不會對人生絕望。但問題是,他可能在絕望時,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壓力。
高層次人才在自我實現過程中,一旦認同了這種企業文化,實際也是把自己當作了手段,他們已經迷失,忘記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實現當作了終極目標。
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華為“自殺門”留給我們怎樣的思考?
章友德:一個優秀的企業除了實施經濟目標,還有沒有其他目標?或者說,為了實現這個經濟目標,除給員工報酬,你還有什么激勵,給員工以什么關懷,讓員工疲憊的身心得以恢復?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在華為,高收入成為企業驅動員工的主要動力,而員工也把金錢看作了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高收入成為了克服高壓力的唯一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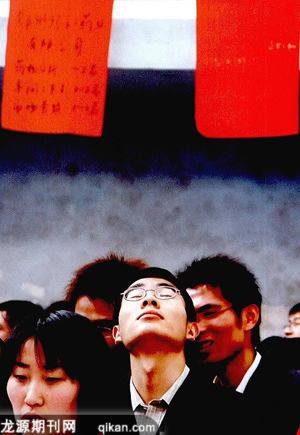
高收入的誘惑,相當多的員工自發地向機器轉變。少數個體無法抵擋住團體的裹脅力量,更何況,若干學校有IT專業,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壓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棄。
《新民周刊》:華為也確實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醫生,還有禁止員工在單位熬夜。
章友德:這絕對不是提幾個口號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制度設計,這樣的倡議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除了本身任務的需要,員工之間也唯恐落后,因為你給他的叢林法則就是這樣。我們承認狼性很重要,華為沒有狼性就沒有今天。但更要記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以人為本更不是用報酬和待遇來衡量的。
給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會成為更加優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這樣一個觀點,在很多公司成長的過程中,伴隨著利潤的增長和資本的擴張,現代科層管理的組織嚴密性、效率始終是一些企業最重要的著力點,而對于人的思考卻常常被淡忘、被有意無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會科層制組織現在都面臨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說我把自己變為螺絲釘,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實際不是螺絲釘,人有思想。現代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科層制出現,每個分支結構都是為實現組織最大目標設計的。但科層制結構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視價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價值理性下,人還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親情。
企業可能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實際上沒有把人當人看待,你的員工有家庭,有子女,下班了應該是回家的,這是一個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但是現在卻是帶著一身壓力回家。
特別是IT行業,這是過去20年中發展最快的產業,最能體現自我創新的行業,精英的更多進入造成這個行業競爭更加白熱化,所有人都更加身心疲憊。
所以為什么這個行業出“自殺門”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有一種觀點,華為有6萬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兩個員工,遠沒到社會上的自殺比例。
章友德:我國每10萬人中有23個人自殺,這是一個平均數,中國多數自殺者是農村婦女,原因在于農村整體相對貧困,農村婦女文化層次又是最低,沒有化解危機的能力。
華為是怎樣的企業?員工是精英中的精英。高素質體現在既能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證自己的身心健康,承擔對家庭、企業、社會的責任。精英階層代表整體人群前進的力量,你們應該擁有更高的應對能力,但是現在你們的人每年都出事,當然引發我們的思考。
你還沒有達到整體人群的自殺比例?你去看看其他企業是否有你這樣的比例!
個體自殺的原因注定有很多謎,因為人已經死了。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由這個現象引發思考。從自殺個體分析華為,可能冤枉你,但從社會角度關注你華為,你一點不冤枉。
關注你還是對你的愛護!何況你的“狼文化”本身充滿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