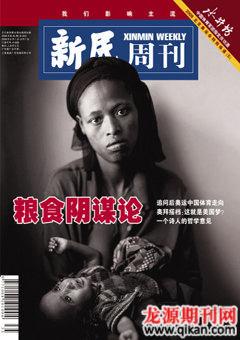悲情市鎮天水圍
嚴 飛

“我就住在這個著名的無人理會的天水圍。”這是劉國昌電影《圍。城》里一句極為普通的臺詞,卻一語道出了香港最大的悲情和無奈。
我是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觀看這部電影的,電影以香港天水圍社區為故事背景,講述了一幫隱蔽青年如何在掙扎之下沉淪犯罪的故事。這其中被導演所刻意聚焦放大出的黑暗和丑陋,與上個月剛剛公映的許鞍華新片《天水圍的日與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天水圍的日與夜》也是一部將鏡頭對準天水圍的電影,許鞍華意欲通過再現天水圍兩個家庭簡單的日常生活,來展示出人性的溫情。然而當電影里出現獨居婆婆為了省錢,只買十元錢的牛肉,炒出兩碟菜心牛肉,一餐作兩餐吃;寡婦母親為了獲得免費派送的紙巾,叮囑兒子步行到很遠的便利店購買報紙這些小細節時,我們感受到的,依舊是天水圍的嘆息與辛酸。
天水圍地處偏遠的香港新界元朗區,是香港人眼中的“悲情市鎮”:雖然該社區只有區區27萬人口,卻是全香港最多內地新移民,最多失業人口,最多低收入貧困人士,最多單親家庭,最多獨居長者和最多青少年問題的社區。在貧窮、失業、孤獨等問題重重影響之下,這里的居民找不到合適的途徑宣泄壓力,于是就如同《圍。城》的情節一般,發生了一宗又一宗震動整個香港的家庭倫常慘劇。
2007年10月,一名領取綜援的媽媽把自己只有12歲大的女兒和9歲的兒子捆手綁腳,硬生生從24樓推下,隨后自己跳樓,3條生命就此終結。2006年7月,3名同是30多歲的單親母親,相約在其中一人的家中寫下遺書說生無可戀,在屋內燒炭身亡……
這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劇僅僅只是天水圍眾多不幸中最為凄慘的——當我2002年在天水圍進行新來港人士輔導調查的工作時,就曾經一度為這里表面安寧之下的觸目驚心感到絕望。然而6年過后的天水圍,貧困人士和新移民家庭的日日哀嘆似乎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糟糕,連歌手李克勤都在歌曲《天水?圍城》里大聲地唱道:“圍住了的血汗圍住了的跌宕/圍住了當初的厚望/越來越渴越來越覺/沒能力去闖出沙漠。”
天水圍“人間沙漠”式的悲情,從何而來?天水圍的前身是一片大魚塘, 1970年代末,隨著香港經濟的快速起飛,當地村民決定告別自祖輩起就開始經營的漁塘鴨場。到了1982年,當時的港英政府收購了天水圍的全部土地。在港英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天水圍周邊的魚塘幾年不到就都被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生氣勃勃的新市鎮。
香港回歸之后的1998年,受到金融風暴的沖擊,全城經濟陷入低谷。天水圍地區曾被特區政府規劃為供應大量居屋樓房的重要地段,但伴隨著金融風暴影響的擴大,大量居屋迫不得已遭到停建,被改建成為接收低收入家庭的公屋。除此之外,那些原本用來建立夾屋,滿足夾心階層(即收入不足以購買私人樓宇,又不合資格申請居屋及公共屋村的中等階層市民)住房問題的用地,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取消后,也被用來建立公屋。一時之間,整個天水圍新市鎮處處公屋林立,公屋居民的比例高達85%之多,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貧民區”。
如果僅僅是物質上的困境,尚可以通過各種政策措施進行硬件上的改善,但精神上的困境卻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消弭。《天水圍十二師奶》一書曾為典型的天水圍家庭主婦總結出了如下特點:都是新移民,文化知識水平不高,丈夫不是患病,就是在內地包二奶;一個異鄉人帶著子女在疏離的社區生活,不僅語言和文化上存在著隔閡,生活上也有諸多不便;最為要命的是,這些新移民婦女,當初都是抱著對香港的巨大期許和理想來到這里,但是香港不是天堂,天水圍似是人間的凄苦地,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無處找尋幫助。
也許在許鞍華的影像中,天水圍依舊充滿著溫情與希望,但當《蝙蝠俠》、《街頭超人》等商業大片在全香港各大小影院日夜輪放的時候,《天水圍的日與夜》卻僅僅只能夠在一家影院上映,并且映期只有6天:現實中的天水圍就是如此孤零而少有人矚目,而這也正是“悲情市鎮”真正的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