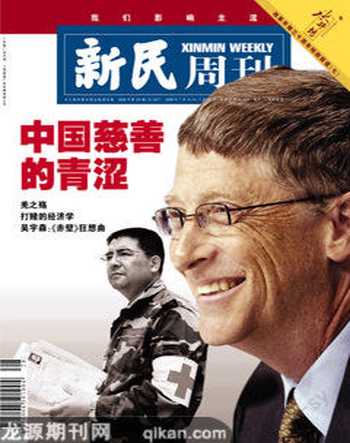羌之殤
賀莉丹 李澤旭

除大量珍貴羌族文化遺址與羌族民俗文物受損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難。
文物劫難
嗅著空氣中濃重的消毒藥水味道,知道距離北川縣城又近了一步。
2008年6月26日上午,黑云壓頂,暴雨滾落,坍塌成粉的北川縣城處在三重關卡的戒嚴狀態(tài)。細心者不難發(fā)現,一圈鐵欄已將北川縣城整個包圍。在歷經短暫的4日開放之后,北川縣政府決定,從2008年6月25日起,對北川縣城實行封閉管制。
綿陽特警大隊陳隊長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就在6月24日,他們在北川廢墟抓到了50個小偷,黃金、電視、冰箱……人贓俱獲,“問幾下就招了”,這些小偷最后被送到在北川縣擂鼓鎮(zhèn)辦公的北川縣公安局。
除戴著口罩執(zhí)勤的公安特警、一身白色防化服的防疫部隊之外,徘徊著不愿離去的是負重翹首的北川百姓,此外是有任務在身的記者與北川官員。
大多數人的姿態(tài)是伸長脖子往關卡內張望。其實,朦朧雨霧下,能看得清的也只有下縣城的那條黃土路與遠方的層巒疊嶂。
“讓我進去!”北川羌族自治縣文化局副局長林繼忠跟把守最后一道關卡的特警理論,他急切地喊,臉紅脖子粗,不斷揚起手中北川縣政府特批的“條子”,上面印章鮮紅。
半小時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進了北川縣城,就“5?12”地震遺址博物館籌建事宜進行現場考察。陪同前往北川的林繼忠卻被攔下。
“他們是北京的,我是北川的,我對當地情況熟悉!”林繼忠動了怒,終于,他獲準通行,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下縣城的爛泥路。
這條路,通向靜謐的死亡之城。45歲的林繼忠并不愿重溫這些揪心的場景。5月12日深夜,在曲山小學廢墟中刨了8個小時,他終于將小女兒林若思抱在手上,10歲的女兒奄奄一息,腿和手都斷了。十幾分鐘后,孩子永遠閉上了眼睛。
“北川縣城死了許多學生,相當于我們斷代了”,林繼忠哽咽著,沉默。這個看起來總是精神抖擻的羌族漢子抬起頭,閉上眼睛,大量的淚水順著眼角淌下。

“保護好北川縣城地震遺址,就是保護了羌文化”,在北川縣城,單霽翔一句話讓林繼忠印象深刻。林繼忠反復說,在北川縣城建的地震遺址博物館理應保持震后真實原貌,以警示后人,例如,在北川縣城廢墟上注明幸存者的逃生位置并放置他們的圖片。生死原本就是一線之隔。
2008年6月25日,這個炙熱的傍晚,北川羌族自治縣羌族民俗博物館館長高澤友正將從北川縣城廢墟表面搶救出來的300多件檔案及館藏字畫分成5箱,送往綿陽市政府資料室暫存,其間斡旋者是四川大禹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德書。北川縣城新址未定,這些來自羌族民俗博物館與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史資料暫存綿陽市,成為當下最好選擇。
北川縣共有805件羌族民俗文物在汶川地震中集體毀滅。“陶器都被震成碎片。很痛惜,這些文物都是無法復制的!”高澤友不斷感慨。
“地震之后,北川縣城的地勢已經改變了,要確定民俗博物館綜合大樓的位置非常困難”,高澤友告訴《新民周刊》記者,發(fā)掘北川縣城深埋文物需經級級報批,目前他們仍在等待,“我們不可能自己挖到廢墟下去找文物,要知道,廢墟底下還有很多遇難者”。
對深埋于地下數十米的羌族文物,44歲的他如數家珍:由木頭、竹子、樹藤制成的大弩,清代末期的,古羌人用于狩獵之用,僅存一把;一條5米多長、5厘米寬的發(fā)辮腰帶,清代中期的,由羌寨每位族人捐出頭發(fā)編成,族人腰痛時可借用,一位羌族土司(封建王朝設置的羌寨管理者,享有世襲特權)轄區(qū)內只有一根發(fā)辮腰帶,“非常珍貴”;羌族祭祀用的罐罐,南北朝的,為羌族土司或羌寨頭人的隨葬品;竹子、木頭、銅、錫等各種材質的油燈,遍布南北朝、唐、宋、明、清;羌人生產、生活用的陶器,遍布漢代與南宋,工藝精湛……
“毀于一旦的還有一只羌人用的清代瓷碗,國家二級文物,花紋精致;一枚羌寨頭人的四方印章,500年前的,晶瑩通透,手感溫潤,用于簽訂戰(zhàn)書或生死狀,是一種權力象征,反映了當時羌族組織結構……”林繼忠樣樣數,一連串。
2007年7月,北川羌族自治縣羌族民俗博物館成立。而早在2003年,對羌族民俗文物的收集就已開始,各色羌族民俗文物由文物工作人員從北川縣青片鄉(xiāng)、片口鄉(xiāng)、禹里鄉(xiāng)、桃龍鄉(xiāng)等關內(北川縣西北鄉(xiāng)鎮(zhèn))羌寨人家中收集而來,包括地勢偏僻的西窩、五龍、爾瑪羌寨。
讓高澤友印象清晰的是一塊雕刻著羌族牧羊人的漢磚,治城(禹里鄉(xiāng))村民在一次挖地時挖到過兩塊此類漢磚,等高澤友興沖沖地跑到村莊時,一塊漢磚已碎,他給了村民幾百元,小心翼翼地將僅存完好的一塊捧回北川縣城,存放于民俗博物館綜合大樓庫房的漢磚在震后影蹤全無,“這種有古羌人的刻畫非常少,它真實地反映了古羌人的游牧生活,無價呵!”
今年4月份,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已開始,高澤友在羌寨中呆了20多天,普查陳家壩、貫嶺、都壩、片口4鄉(xiāng)40多處不可移動文物狀況,“這次普查結果非常好。但這次地震中損毀了三分之一”,北川境內的明朝軍事古堡永平堡是其一,永平堡是史上羌漢融合之見證,高澤友解釋,明朝中葉為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管轄,中央政府在北川設置該軍事要塞,實施“改土歸流”政策,羌族開始逐漸漢化。震后永平堡損毀嚴重,幾成危樓。
為保存羌族文化,2007年,四川省撥給北川縣10萬元用于征集羌族民俗實物,北川縣號召羌人捐獻藏品,不料地震發(fā)生,這些羌族文物均遭損毀。
幸無損毀的是震前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館藏的123件文物,它們被送至綿陽市博物館中心庫房代管。

震前,北川有100余條非物質文化遺產,口弦、羌歷年、許家灣十二花燈為四川省級;綿陽市級有30多條,諸如大禹傳說、羊皮端公舞等;縣級20多條,還有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仍在申報過程中。
羌族文化的震后復蘇在艱難繼續(xù)。6月初,四川省文化廳發(fā)布了《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區(qū)初步重建方案》,該文化生態(tài)保護區(qū)將以茂縣為核心,涵蓋北川、汶川、理縣、平武、松潘等縣,同時將保持羌族原有建筑風格、民風習俗、祭祀禮儀,體現羌族文化原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地質結構特點。
但更為關鍵的震后復蘇在于人的因素。對訓練有素的精通民間藝人在震后的流失,北川縣政協文史委原主任、羌族文化研究專家趙興武憂心忡忡,不停抽煙的他直言,保護羌族文化,“經濟手段必不可少”。
僥幸被找到的“北川羌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與“北川羌族自治縣羌族民俗博物館”兩塊白底黑字招牌,它們孤零零地被擱在安縣安昌鎮(zhèn)新華書店的一處空房內,這是幸存文物工作人員的臨時辦公點。
“只要有人在,地震對羌族文化造成的損失就能夠挽回”,高澤友神色堅定。
在跟一位失去孩子的母親聊天時,高澤友的面容才漸顯悲愴。震后,他先后去過北川縣城13次,妻子尸骨未見,最后一次去北川縣城時,他四顧茫然,“不知道家在哪一塊了。如果不是為了工作、為了搶救資料,我是不想回去的,打擊太大了!”
邊緣羌語
在蜀地版圖中,北川、茂縣、汶川、理縣這條自東北向西南走向的區(qū)域匯集了中國絕大部分的羌族人口,其中,中國約三分之一的羌族人口集中在北川。
此四地均遭汶川地震重創(chuàng),死亡與失蹤的羌族人口達2萬多人,同樣受損的還有在此區(qū)域內的羌寨與羌族民族建筑。震后,北川與汶川縣城均需整體搬遷。
幸存者在努力活著。讓林繼忠惋惜的是,除大量珍貴羌族文化遺址與羌族民俗文物受損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難。

由于羌族沒有文字,羌語與文化習俗的傳承均依靠口口相傳。精通羌語的長者、學者,熟知羌族歷史文化的端公是羌族文化傳承的關鍵人物。北川縣知名羌族文化研究專家謝興鵬、羌族音樂收集人計學文和羌舞收集人李紅果等在此次地震中不幸遇難,給羌族文化傳承帶來重大損失。在林繼忠看來,北川的十幾位端公是重要的保護對象。
但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這是目前羌語普及與傳承的一大主要障礙。
北川縣城往上有一條公路,延伸至金城爾瑪羌寨,蜿蜒的盤山公路讓行者望而生畏,如果步行到山頂,得走6個小時到山頂,如果運氣好的話,你也許能搭乘農民回寨子的順風車。
44歲的楊柳坪村三隊隊長楊正明很爽快地讓記者搭乘了他運送簡易房材料的農用三輪上了山寨,在楊正明眼中,金城爾瑪羌寨只是一個當地政府修建的旅游點,而現在金城爾瑪羌寨的大門也盡數倒塌了。
車行在這條艱難爬坡的公路上,只感覺全身都在劇烈顛簸。這條公路是2005年修通的,這讓山上的羌族人家很方便地跟山下聯系與往來,雖然,楊正明他們“只享受了這條公路不到3年”。33歲的羌族婦人楊彩霞穿了一件紅色的衣裳,搭乘了楊正明的車,她的頭上散發(fā)著定型水的香味,“我們已經不會說羌語了”,楊彩霞說。
楊柳坪村三隊60%以上的人口為羌族,已完全漢化。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賣木竹和白家竹,每斤0.3元,現在竹子還在山上,沒人買。村民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楊正明家的吊腳樓也改造成了磚瓦房,但地震毀壞了水源,村民飲用的還是老井中存的雨水。
41歲的楊柳坪村四隊羌族婦人鄧勝清有一套羌服,是縣上發(fā)的,2003年,北川縣派人到村里教跳沙朗(鍋莊),鄧勝清學會了,盡管開始的時候,她挺害羞的。
6月23日,北川縣科技局羌族工作人員董正玲獨自回了趟北川縣城,她只帶出了3樣身家:兒子董沚函的照片、兒子在曲山幼兒園得的小紅花和她給兒子繡的兩雙羌族挑花刺繡鞋墊。
胖嘟嘟的兒子的各種淘氣表情定格在照片中,永是不變的3歲。她還想把她那套紅色緞面的羌服找出來,但已不知去向。
在15歲去安縣師范學校念書之前,董正玲都生活在北川縣小壩鄉(xiāng)酒廠村,她感受到的羌寨是:河流從酒廠村中間流過,空氣清冽;吊腳樓蟄伏在濃密森林中,最底下一層是豬圈,樓上住人;到最近的集市要2個多小時,2002年,公路才修到家門前。她的爸爸和爺爺都會講羌語。
1992年農歷六月初六,禹里鄉(xiāng)舉行大禹祭祀活動,唱羌歌、跳沙朗,鬧騰騰,“羌人將大禹看作祖先”,從那時起,高澤友開始對羌族文化有興趣,但他也尷尬地發(fā)現,自己不過會講幾句簡單的羌族日常用語而已,小時候奶奶李朝珍教的羌語,他已遺忘得差不多了,了解羌族文化于他而言充滿困難。
高澤友的故鄉(xiāng)北川縣禹里鄉(xiāng)禹里村位于海拔1200米的山腰,小時候,每逢爺爺高友銀賣了漆、買了布,奶奶李朝珍就能給高澤友做件新的羌族斜襟長布衫。初二以前,高澤友都是穿著奶奶做的斜襟長衫和羌族草鞋,爬一個半小時的山去念書。那時,他班上的羌族孩子還都戴著耳朵帽;奶奶跟同輩人聊天時,也用羌語。
到治城(今禹里鄉(xiāng))念書時,高澤友懂得了“趕時髦”,跟漢族孩子一樣,他換上紅色土布質地的背心,這讓他看上去跟漢族孩子沒有兩樣。從治城中學畢業(yè)后,高澤友去了煤礦工作,之后到川西北石油勘探大隊,后來回到禹里鄉(xiāng)擔任林政員、旅游專干。
找資料、聽專家講座,去羌寨,年邁羌人講羌語,他記下,收集了一摞羌族酒歌和羌語,用漢字拼出發(fā)音,“有空就翻一下。但現在被埋了,很可惜”。
暫居北川縣擂鼓鎮(zhèn)災民安置點的曲山鎮(zhèn)東溪溝村羌族婦人李定翠告訴記者,東溪溝村都為羌人,但她們已“講不來羌語;婆婆會講羌語、唱羌歌,但死了十多年了”。

52歲的李定翠不會做羌服,也買不起,腕上銀鐲是4年前大姑姑送的;她很少在村里跳舞,農活太多,但北川縣政府每年會在村上抽調幾個人參加唱羌歌、跳鍋莊培訓。
北川縣文化局副局長林繼忠告訴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北川縣文化館就開始請來青片鄉(xiāng)羌寨的羌民,教北川縣城群眾唱羌歌、跳鍋莊。在他的印象中,上百人集聚在北川縣政府前的壩壩里,流光溢彩中,熱情的羌歌和鍋莊總是從7點多一直沸騰到10點多。
羌語多為生活中用的口頭語,若將漢語文章譯成羌語,就需要將口語化的羌語歸納,相當于意譯,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在北川縣少之又少,31歲的北川羌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副所長陳仕瓊便是為數不多的精通者。
陳仕瓊的故鄉(xiāng)在茂縣北溪鄉(xiāng)杜家坪村,這個羌寨海拔1500米,石砌材質的碉樓嚴謹地分布于青翠山坡上,隱藏于群山的起伏中;半山腰上,云海翻騰,房屋緊緊相連,集中于一處。這個500多人的羌寨依然羌風濃郁,至今,返鄉(xiāng)或跟鄉(xiāng)親對話時,陳仕瓊仍要使用羌語;他的羌歌也唱得滾瓜爛熟,“一輩子都忘不了”。
10歲以前,陳仕瓊都是一身過膝羌族長衫,一雙繡著云朵與花草的云云鞋踏在彎彎山路上。小學四年級,他沿著蛇行的山路,走路1小時到北溪鄉(xiāng),再坐3小時公共汽車去茂縣縣城念書,腳底依然是花草生長的云云鞋。后來他將云云鞋和跑鞋搭配著穿,畢竟,對一個男孩子來說,鞋尖微翹、狀似小船的云云鞋,跑步不方便。
1991年,哥哥陳仕海考上達縣師專政治系時,姑爺興奮得很,將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摘下,一把扣在哥哥的手腕上。父母倒上咂酒(用青稞或小麥釀的酒,用管吸咂),興高采烈地款待鄉(xiāng)親。
在阿壩州師范學校羌語班就讀期間,一次,陳仕瓊穿著云云鞋從阿壩州到成都。在阿壩州,穿云云鞋的人到處可見,大家習以為常;但在成都,物以稀為貴,許多路人盯著他的腳看,“很稀罕的樣子”。
1998年,從阿壩州師范學校畢業(yè)后,陳仕瓊主動要求到偏遠的北川縣青片鄉(xiāng)小學教書,他與他那屆羌語班的44位同窗,都致力于為羌族孩子提供羌漢雙語教學,讓他們更好地接受教育。在那個年代,“一些邊遠地方的羌寨孩子還聽不懂漢語”。
青片鄉(xiāng)的孩子們奔騰的日子,像極了陳仕瓊的兒時。男孩子穿著羌族布質長衫,女孩子從頭到腳,花開一身,那是飛針走線織就的美麗。孩子們喧鬧著,從海拔兩三千米的羌寨,蹦跳下山,到青片鄉(xiāng)小學接觸新的世界。在青片鄉(xiāng)執(zhí)教時,陳仕瓊跟當地羌寨孩子講羌語,他們能互相聽懂。
窮鄉(xiāng)僻壤,師資緊缺。陳仕瓊教他們語文、數學、思想品德……羌人尊師,民風淳樸,孩子們下山時,小手常拽著一捆油綠蔬菜或一溜新鮮豬肉,那是家長千叮萬囑一定要給老師帶的。“我深知他們的艱苦。蔬菜可以留下,肉不可以要”,實在推托不過,陳仕瓊給孩子一瓶酒,讓他們帶上山。禮尚往來。
上世紀90年代,四川省民委為方便羌族地區(qū)教學、更好地普及羌語,研究出一套羌漢雙語適用本,在茂縣、汶川、北川等羌族聚居區(qū)推廣,這套適用本將羌語用漢語拼音標注出來,并標明羌語詞句的漢語注釋。比如,羌語將“吉祥如意” 的發(fā)音用漢語拼音標示為“na ji vha lu”,孩子們可以按照漢字“那基阿路”的發(fā)音來學習這句羌語。
羌語的結構跟英語近似,屬于“賓謂主”結構,比如,羌語中“你吃飯了嗎”的發(fā)音用漢語拼音標示為“unn suduvha seten mi”,直譯后實際的結構在漢語中而言應是,“飯吃了嗎你”。
“羌語分為南部羌語和北部羌語,各自都是完整語系,它們根音大多相同,但發(fā)音有變化,兩種語系都有失傳趨勢。南部羌語主要以茂縣北溪鄉(xiāng)、三農鄉(xiāng)、曲谷鄉(xiāng)三地為主要基礎,阿壩州、北川的羌語語系主要屬于南部羌語;茂縣、理縣、汶川也存在北部羌語”,這套羌漢雙語適用本以南部羌語為主,陳仕瓊看來,這套教材相當實用。
2003年7月6日,國務院批準設立北川羌族自治縣,由此成為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的北川縣急需精通羌語之人,陳仕瓊調至北川縣工作。他每年至少得給北川縣的學生、教師、機關干部、旅游及餐飲服務業(yè)者進行3至4期的羌語培訓,每期培訓至少有300人。參與者相當踴躍。
“由于北川縣靠近安縣,跟安縣經常交易、通婚,目前北川羌語失傳嚴重,處于瀕危狀態(tài),急需普及”,陳仕瓊強調,在北川縣城,精通羌語的最多只有二三十人。在交通相對閉塞的青片鄉(xiāng),有少部分孩子會羌語,孩子們也已習慣用漢語交流。
震前,北川縣委、縣政府就已意識到普及羌語的重要性,北川縣許多中小學校每周都給學生開一至兩次羌語課。但這顯然還不夠。在陳仕瓊看來,這種課外活動形式的羌語課需要變成羌族學生的必修課,一個3至5年的細致的羌語保護計劃也亟待制定,“我們的培訓力量有限,孩子們如果平時不用羌語交流,久而久之就忘了”,羌語普及,要從源頭抓起。
流暢的羌語脫口而出時,眼袋明顯的陳仕瓊看來既精神又耐心。68歲的母親與6歲的兒子在地震中罹難,連日憂心的他偶爾才嘆: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6月24日回了趟北川縣城,家已經垮平了,兒子的照片拿不出來了,真遺憾……
地震也摧毀了陳仕瓊的故鄉(xiāng)杜家坪村,那里的碉樓嚴重坍塌,這個處于搬遷范圍的羌族村莊尚不知以后要在何處扎根,陳仕瓊也擔心地緣、人緣因素的改變對羌族文化傳承可能帶來的影響。
端公何在
從綿陽市出發(fā),車行經江油市、閉門鎖戶的西羌九黃山猿王洞景區(qū),再經北川縣甘溪鄉(xiāng)、桂溪鄉(xiāng),公路始往海拔高處延伸,山勢險峻。黛色大山似一個被剃壞了的頭,東禿一塊、西缺一邊,那是地震造就的巨大的傾瀉式的山體滑坡。手機信號一度中斷。
我們的越野車行進在路上,顛簸得緊,沒有任何準備,就看見,沿途不斷有孩子從帳篷中飛奔出來,跑到公路沿線站定,齊齊敬禮,一個挨一個,小身體挺得筆直。司機說,孩子們是看見了車前懸掛的“北川縣抗震搶險救災”字樣。
整個北川縣陳家壩鄉(xiāng)就是一個巨大的災民安置點,陳家壩小學成了危房,陳家壩鄉(xiāng)政府的牌子被挖出來,擺在公路旁露天辦公。陳家壩鄉(xiāng),羌人占70%,漢人為10% ,其余為回、藏人,此次地震造成陳家壩鄉(xiāng)95% 的房屋震塌毀損,1.3萬余人受災。
云興村、太洪村、金鼓村過后,就是紅巖村。70歲的陳家壩鄉(xiāng)文化站退休職工蔣國斌在紅巖村的干女兒家等我們,蔣國斌在西河村的房屋全部倒塌,只能在干女兒家搭建一個簡易帳篷居住。
“鑼鼓打得鬧騰騰,主家請我接喜神,對天對地拜三拜,飛云走馬赴臺來。喜神娘娘好風采,八副羅裙雙排開,喜神娘娘你從哪里來?我從西方羅曼來……”蔣國斌現場給記者表演了一段“接喜神”端公調,端公唱詞本應用羌語,但現在在陳家壩鄉(xiāng)許多人都已不會羌語,蔣國斌祖輩都是羌人,但他也不會講羌語,端公調于是改為用漢語唱。
1983年,到北川縣文教局下設的陳家壩鄉(xiāng)文化站工作之后,蔣國斌開始收集諸如接喜神、立廟、除邪安神的等端公調唱詞;1999年,蔣國斌跟隨年長羌族端公陳興章學打羊皮鼓,他還組織端公參加北川縣的羌族節(jié)慶演出,他本人也參與表演打羊皮鼓,“辦喜事、喪事不用打羊皮鼓,打羊皮鼓是為請神、給病人安神,有降妖伏魔的意思”。
他有底子。14歲時,在治城念書;15歲時,跟著父親在治城打鐵;1956年,他進了北川縣川劇團,從武生一直唱到文生、丑角,還唱自己創(chuàng)作的川劇金錢板《血戰(zhàn)走馬嶺》,為贊揚明代的羌族頭人帶領羌人反抗明廷圍剿而作。
“解放之后,端公就沒有收過徒弟,連我,都成了最后跟他們學習的人”,蔣國斌感喟,“人而無恒,不可學醫(yī)巫。想成為端公,就要真心實意地學習”。
蔣國斌帶著記者在一片簡易房區(qū)域中找尋78歲的羌族端公李昌田,李昌田祖輩都是陳家壩鄉(xiāng)老廠村的端公,其父李代云畢生做端公,81歲離世前,已將平生技藝授予三子李昌德、李昌田、李昌元。
端公也稱釋比、許,即執(zhí)行人與鬼、神之間交往的巫師。羌族社會認為,端公是羌族原始宗教的傳承人,均為男性。于沒有文字的羌族而言,端公口中的敘事詩、唱詞或歷史傳說,組就了鮮活生動的羌族歷史,端公因此被看成是具有“法力”,在羌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也是羌民中最權威的民族文化傳承者與知識集大成者。
在一處人頭攢動的簡易房中,李昌田探出頭來,老頭精瘦,穿了件發(fā)黃的舊襯衣,其貌不揚,有點蔫。從11歲開始,李昌田就跟隨父親學習端公技藝:打羊皮鼓、唱端公調、占卜、采草藥……“越學越深,越學越難”,30多歲時,他出師了,“有病人,就去醫(yī)病;村民家里不順利,要‘請神,也要去”,過會兒,他又補充道,真正生大病,還是要去住院的。
每做一場法事,李昌田都要穿上戰(zhàn)裙(打腰裙)和神褂,頭戴手掌型的頭麻。村民要給答謝禮,不過在李昌田看來,給多少,就算多少;他還得種他的兩畝地,以維持生計。在平時,他是普通的勞作者。
李昌田披了件軍綠色的襯衣,帶著記者穿越損毀嚴重的鄉(xiāng)政府街道,前往他在雙堰村老廠村四組的家。山體滑坡已將回家的公路埋沒,“底下還埋了很多人”,李、蔣二位老人嘆。
李家3間瓦房盡數坍塌,裂痕肆行于裸露的水泥墻體上。李昌田最小的兒子、40歲的李勝強胡子拉茬,埋頭從自家廢墟中將一些稍微值錢的家伙翻出來,背簍、衣服,花花綠綠攤了一地。一條小路蜿蜒上山,即是青蔥玉米地。
兩面橢圓形的羊皮鼓、一把有銹漬的石刀,都被李勝強小心拾掇出來,他知道,這是父親李昌田的寶貝。羊皮鼓是李昌田親手繃的,“要生皮,不能熟皮”; 石刀傳了幾代、100多年了。
蔣國斌在一旁解釋,從端公使用的石刀和麻鞭這些工具中可以看出古羌民活動的痕跡,“比如在古代,石刀用于宰殺牲畜、剝皮除毛,麻鞭原是古羌民用來牧羊的”。
在老廠村村民李昌銀眼中,老廠四組近300口人,只有李昌田兄弟3位端公,“村民都很尊敬他們,附近村社的村民有時也請他們過去”。
但是,端公已不再成為現在羌族年輕人的選擇,在他們眼中,端公這種古老神秘的職業(yè)似乎應該封存于古書與歷史中。李昌田的4個兒子都在外地打工,小兒子李勝強選擇在山西的一家煤礦做礦工,下礦井充滿危險,但對李勝強而言,每月2000元至3000元的薪水是一筆不小收入。“太難了,不肯鉆了”,對于沒有選擇繼承父親的衣缽,李勝強這樣解釋。
李昌田的弟弟李昌元在汶川地震中遇難,李昌田形容自己是“死了又活過來”,他輾轉江油市,最終的選擇依然是折返故土。
李昌田唱起端公調,敲起羊皮鼓,繞花手勢,活靈熟稔。震后,再次接觸自己安身立命的家伙,他的精神矍鑠起來,話也多了。
他的石刀,一頭是一方尖頭鐵柄,另一頭是一圈銅環(huán),6個鐵圈掛在銅環(huán)上,“一頭可以鏟爐灰,一頭可以搖”,李昌田搖起叮咚作響的石刀。鏗鏘有力的唱詞吟誦起來,仿佛回到了那個久遠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