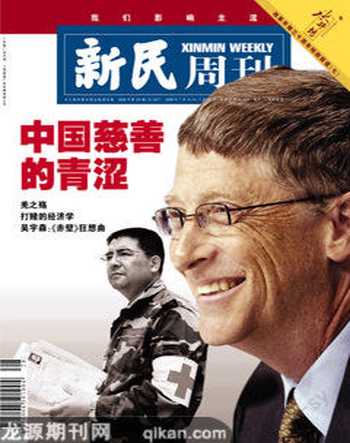羌衣
賀莉丹 李澤旭

洪水眼看著要漫上來,水勢洶涌。母廣芬抱起小紙箱,往外飛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覺得費(fèi)了這么多心血去做這些羌衣,一定要把它們搶出來”。
2008年6月底,在安縣安昌鎮(zhèn)一個近河的災(zāi)民安置點(diǎn),天藍(lán)色救災(zāi)帳篷比鄰而居。暑氣逼人,38歲的北川縣漩坪羌族鄉(xiāng)石龍村一組村民母廣芬在繡一只包,手勢靈動,煙臺醫(yī)療隊(duì)的劉媽媽幫母廣芬的女兒胡興梅體檢,繡包是為答謝。
“羌繡本來就麻煩,用心繡,10天到20天才能繡好”,母廣芬抿嘴,嘴角跟著上彎,“看,人都走了,我還沒繡好”。她是一位面容秀麗的羌族婦人,膚色黝黑,耳上銀月珰。
傍晚,6歲的女兒胡興梅換上母廣芬親手做的一套羌衣,從帳篷中飛奔出來。這件羌衣,是母廣芬在震后逃難中背出來的,鮮艷紫紅與耀眼明黃打底,桃紅牡丹朵朵盛放,是細(xì)心描繪的美麗,寓意吉祥富貴。
挑花刺繡需縝密思量,母廣芬得先在紙上畫好樣子再開工。光衣服就花費(fèi)了她4個多月,做搭配的帽子需要1個多月。一針一線,馬虎不得。
搶救羌衣
5月14日早晨,在距地震2天后,母廣芬和丈夫胡敏下山回家,“要給娃娃拿衣服,娃娃冷得不得了”。
他們居住的這棟兩層的磚瓦房是2000年蓋的,貸款2萬元,今年才還清。一樓已被洪水吞沒,前門靠水,后門靠山,他們撬開二樓后門,進(jìn)去。
二樓是他們的客廳和臥室,機(jī)緣巧合,女兒的兩套羌衣、兒子的一套羌衣與丈夫的兩件衣服此前就被母廣芬收拾在一個小紙箱子中。
洪水眼看著要漫上來,水勢洶涌。母廣芬抱起小紙箱,往外飛奔,“也不知怎么回事,只覺得費(fèi)這么多心血去做這些羌衣,一定要把它們搶出來”。潛意識很強(qiáng)烈。
1997年,兒子胡飛5歲時,胡敏遠(yuǎn)赴位于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東南部的茂縣做泥工,母廣芬跟著丈夫,去茂縣打零工,偶遇一位精通羌繡的左老太太。左老太太會繡七八十種鞋墊,花色各異,在茂縣旅游區(qū),這些羌繡鞋墊可賣到20元一雙;左老太太還會做云云鞋,鞋面繡花,樣式別致,當(dāng)時可賣到100元一雙,銷路尚佳。繡羌繡,做羌衣、云云鞋,母廣芬跟著左老太太,樣樣學(xué)會,閑暇時繡上幾針,成為她的主要愛好。
他們逃離居所的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當(dāng)天中午,母廣芬家的樓房全部被洪水吞沒,“見不到頂了”。
她依然惦記著那些沒拿得出來的東西:11年前在茂縣花120元買的一根銀項(xiàng)鏈,一克老銀子才2元,“很亮”;給丈夫和兒子做的十幾雙羌繡鞋墊,每做一雙都要十幾天;給他們做的3雙云云鞋,兒子胡飛說,勾針勾的底,繡花面,媽媽做一雙鞋,要一個月……
“都在家里放著,都沒拿出來,來不及了!”母廣芬樣樣數(shù),聲聲嘆,能拿出來的這點(diǎn)羌衣,已是她家的全部財產(chǎn)。
石龍村世代為羌族聚居地,除少數(shù)從外地嫁過來的漢人媳婦外,絕大部分均為羌人。
生活不易,母廣芬的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三姐弟中,她是長姐,長姐如母,讀到小學(xué)二年級時,為掙工分,不得不輟學(xué);13歲時,她和同村小伙胡敏訂了娃娃親,胡敏在湖北宜賓當(dāng)了兩年兵回鄉(xiāng),1989年,他倆成婚時,胡敏找他四舅借了300元錢,婚事是跟他妹妹一起辦的,一嫁一娶,減少開支。最窘迫之際,他們“連2元錢都借不到”。但母廣芬很坦然,“沒錢沒關(guān)系,只要我老公自己肯學(xué)手藝,只要兩人關(guān)系好”。
她很懂得將瑣碎的小日子操持起來:養(yǎng)了30多只雞,震前,還在攢錢準(zhǔn)備買頭豬;跟所有勤勉的羌族婦人一樣,她每年會做一兩百斤臘肉,掛于房梁,黃酥酥的……丈夫胡敏必須外出打工以維持生計,他做泥匠,倘若干滿一個月,能有1500元至2000元收入,這是一家的主要經(jīng)濟(jì)來源。2007年,他們夫婦在北川縣城打工,胡敏一天掙60元,母廣芬挑地磚跟沙子,每天有25元至30元。
“幸虧今年沒在北川縣城做”,跟一位鄉(xiāng)親提及這段經(jīng)歷時,母廣芬幽幽感慨,有些后怕。
兒子胡飛常想起那些沸騰的過往,胡飛的羌歌唱得不錯,在漩坪中學(xué)讀初中期間,他學(xué)會了跳鍋莊(沙朗),北川縣政府曾組織漩坪的孩子集中學(xué)跳鍋莊,胡興梅也會跳了。
每逢農(nóng)歷十月初一的羌?xì)v年,在北川縣城、漩坪鄉(xiāng)政府,許多羌人都要穿上傳統(tǒng)的羌衣,這時的夜晚是醉人的,族人在壩壩里燃起篝火,空氣中彌漫著烤全羊的油香,人們圍著火堆唱羌歌、跳鍋莊,“有人要跳通宵,人擠人,鬧熱得很”,母廣芬記憶猶新。同樣熱鬧的還有農(nóng)歷六月初六的轉(zhuǎn)山會(祭山會),男女老幼,人聲鼎沸,盛裝出席。
在北川羌族自治縣北部偏遠(yuǎn)的小寨子溝自然保護(hù)區(qū)的五龍寨,山高谷狹,羌人在此地世代繁衍,喝咂酒、跳鍋莊、敲羊皮鼓等羌族習(xí)俗悉數(shù)保存,“在五龍寨,許多人都會做羌衣”,胡飛說。但在石龍村,更普及的是繡羌繡鞋墊,像母廣芬這樣會做羌衣的人,少之又少了。
遷徙
離開,成為唯一的選擇。
悲愴的遷徙開始了。5月16日清晨6點(diǎn),母廣芬一家跟隨石龍村一組200多號羌族族人,一起往山外走。一些行動不便的老弱病殘留在村中,等待救援。
出發(fā)前,母廣芬到2里之外的一處山澗,接了點(diǎn)山泉,又從山上農(nóng)戶家借了個鍋,將水燒開,灌在兩個撿來的礦泉水瓶中;別人給她的30個煮雞蛋,她也背上。從家里搶救出來的羌衣,她塞進(jìn)一個蛇皮袋里,和兒子輪流背著,丈夫抱著女兒。
一家人上路了。震前通往北川縣城的路位于大山底下,此刻已被洪水吞噬,他們必須在密林中探出一條新路。
有些路段窄到僅能擱下一只腳,泥水四濺,“一步一步,納著納著走;走不動的人,咬牙都要走,大家只想著逃命”;山體滑坡厲害之處,不斷有塌方發(fā)生,“山垮得嘩嘩響”,一位鄉(xiāng)親負(fù)責(zé)盯著頂上是否有山石滾落,其余人一個接一個,跟兔子一樣,梭過去。這是一支長長的隊(duì)伍,怕被砸,所有人都不敢靠得太近。
走到草山溝,母廣芬抬頭,高山直拔入云,“往山上看,帽子能掉到地上”。他們從一個山脊下來,又轉(zhuǎn)入另一個山脊,似壁虎,貼著巖壁爬行。腳底是萬丈深淵,余震不斷,地在吼,山在晃,石頭轟隆隆地滾落,稍有不慎,即會殞命,“膽子小的人是瞇著眼睛,被牽過去的”。
所有的行李都成為前行負(fù)累,人們開始?xì)獯跤酰呑哌吶訓(xùn)|西,一些人把外套都甩了,“好多人走路都沒法了,沒法拿東西,就跑個光人出來”,羌衣不過幾斤重,母廣芬的步子越來越沉。
路上開始可以撿到一些吃的了,這些東西,前面的人們是帶不走了。母廣芬撿到一袋奶粉、6個面包。他們遇到一個外地滯留游客,女子拄一根棍棍,腳底磨出血泡,一瘸一拐,她告訴母廣芬,已走了3天,她身穿的褲子是路上撿的,原來那條磨爛了。母廣芬給了女子一瓶水、3個雞蛋。
水其實(shí)是最珍貴的。他們只剩一瓶了,去找小山澗,那里有小股泉水淌下,還算清澈,用手捧著喝,“很多大溝里的水是渾的,鄉(xiāng)親們說,那喝不得,有毒!”
走到曹家溝,他們碰見進(jìn)山到村里搜救未撤離群眾的解放軍,汗流浹背的解放軍搶著幫母廣芬背女兒胡興梅,她如何也不肯,“要不得,你們太辛苦了!”推托不過,解放軍給了胡興梅一瓶礦泉水、一個面包。解放軍開始喊話,讓群眾減重前行。“兵哥勸我說,把衣服甩了吧,下面有的是衣服。我就是舍不得甩,一直背著”,現(xiàn)在扔了,太可惜了,母廣芬想。
翻越5座大山,當(dāng)晚8點(diǎn),他們走到了北川縣擂鼓鎮(zhèn),黑壓壓的人群,在路口齊聚,等候前往綿陽市的車輛。2個多小時后,他們被送至永新中學(xué)安置點(diǎn),凌晨2點(diǎn),他們尚未分到鋪蓋。需要鋪蓋的人太多了。胡敏父子在一堆尚未來得及分發(fā)的賑災(zāi)衣服上和衣而眠;母廣芬的腳腫了,她帶著女兒,跟母親擠著躺在一塊木板上,她摸了摸那個蛇皮袋,一路艱辛,背出來的羌衣還在,她稍微放了點(diǎn)心。
6月1日,在他們棲身的這個由彩條編織布搭建的災(zāi)民安置點(diǎn),人們都睡在磚頭上架著的木板上。母廣芬從蛇皮袋中翻出羌衣,給女兒胡興梅換上,小女孩登時成為全場矚目的焦點(diǎn),胡興梅和小伙伴唐佳、劉露露邊唱兒歌邊跳舞,“母雞母雞叫咯咯,雞蛋已生落”,雀躍得很。孩子們的笑臉,彌足珍貴。大人們開始給孩子們鼓掌。3個孩子興奮得小臉紅撲撲。
“只要一家人都平安了,我們還可以重新來”,仍在等待安置決定的母廣芬說,即使居無定所,她仍熱情邀請記者到帳篷中做客。6月初,兒子胡飛去了綿陽市區(qū)一家火鍋店打工,那里會給他一個月500多元;半個多月后,丈夫胡敏去了永新鎮(zhèn)上幫忙裝卸救災(zāi)物資,9個人卸一車,一共120元。
故土難舍,羌寨難離,卻回不去了。母廣芬聽說,她們村有可能被整村安置到煙臺,也可能到內(nèi)蒙古……這都沒關(guān)系,活著,就有希望,就得好好活下去,“國家安排我們在哪里,就是哪里”,她堅(jiān)定地說,自己會帶上羌衣,一起走的。這是跟羌寨僅存的連接,不思量,自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