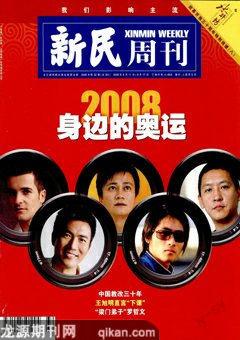李承鵬:在稿紙和熒屏上奧熱
李承鵬 王 倩

照過去的經歷看,我這17天的時間會非常趕。2006年世界杯時我的生活寫照是,白天“彌留之際”,晚上“回光返照”。一天只睡三個小時。
我的奧運生活就是寫專欄和做節目——每天給報紙寫一篇評論,還要進棚錄幾檔電視(或網絡視頻)節目。上午,我會和奧運冠軍們一起錄制全國26家都市電視臺聯合制作的夜間大型談話類節目《大話奧運》;晚上6點檔是《實話實說》欄目在奧運期間的大型直播互動節目;每天還要去新浪錄它們的視頻節目《金牌響叮當》;可能還會有第四檔節目,是CSPN(中國體育聯播平臺)晚上10點檔的奧運直播節目,歐洲杯期間我和CSPN已經合作過了,和黃健翔一起評球。
很多人喜歡我的文字,特別的李承鵬,別人寫不出的。也有人挺煩我的。現在我已經明白說話和寫字是兩種技術范疇的活,說話要讓大家哈哈大笑的,寫字讓大家會心一笑就夠了。我會在專欄里說C羅“這個背著書包放學不回家的嘻哈青年”,說德科“長著巴西農民的臉,頹廢中卻有一絲優雅”,這些是我文字中的優雅,但上了電視就需要口語化。
我和黃健翔一起評歐洲杯,說土耳其前鋒(想過葡萄牙后衛)“小心腰被擰成麻花”,說德國后衛“長達半年的轉身”,這種味道和文字不同的。而且我們倆在一起特別會說段子,話語方式和其他說球的人不同的。我第一次上電視是1995年去四川衛視解說英超,緊張得就只想上廁所,一年后才慢慢消除了緊張感。
照過去的經歷看,我這17天的時間會非常趕。2006年世界杯時我的生活寫照是,白天“彌留之際”,晚上“回光返照”。一天只睡三個小時,給報紙寫三篇稿,給電視坐兩次臺。我的球評基本都是在央視600平方米大演播室二樓的導播室后面那個走道邊上一個三級樓梯上完成的,編導和化妝師隨時監視我的寫作進度,電視臺的眾哥們來來往往地看著我如同一個怪物(摘自李承鵬博客《世界杯日記》)。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我肯定會去現場看比賽。男足和女足決賽是肯定要看的,中國對希臘的男籃小組賽門票我也有的,我還要去看拳擊決賽,鄒市明很有把握奪金牌的,肯定得看這場。還有時間能看其他比賽,我也一定能弄到門票,這倒不用擔心。
在媒體這行已經呆了18年,在奧運現場報道了很多比賽,但對這些比賽當時的具體印象,我真的不太想得起來了。專業記者在現場采訪結束后,腦子都是空白的。凡是能把自己當時的經歷說得很清楚的,一定是平庸的記者和評論員。前線記者看到的只是比賽現場的瞬間,他獲得的資訊還不如后方的消息更綜合全面。我在前方的感覺經常是兩眼一摸黑,國內居委會老太太們都知道中國已經拿到了16金時,我還以為只拿了14金呢。
作為北京市民,生活是有不便,但都為了奧運嘛。我的車是雙號,今天和明天正好輪到單號,只能打的。但雙號的時候,該堵車的地方還是堵。我身邊有兩朋友都買了自行車,說是要騎車上下班。聽說有很多人在找人拼車,但北京太大了,想找一朋友,還要住得近的,去同一條路線,挺不容易的。而且總不能一輛寶馬和一輛奔奔拼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