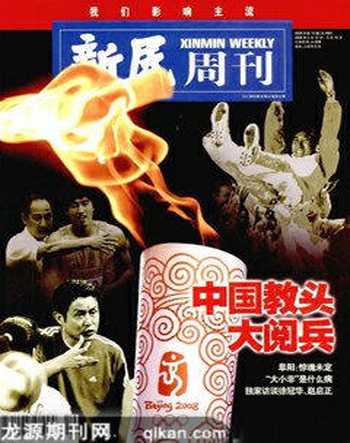徐冠華:破解企業技術創新難題
蘇慶先

至于說“搞創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對于創新的認識和支持,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特別是政府部門,應該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如何能使“中國制造”長久地贏得世界市場?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科技部原部長、同濟大學中國科技管理研究院院長徐冠華院士指出,關鍵途徑就是堅持自主創新、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中國制造以高價值引領世界市場、而不是以低價格打入世界市場。
為推動建設創新型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舉辦、同濟大學和上海張江集團聯合承辦的“浦江創新論壇”即將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浦東召開,論壇的核心議題,就是探討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中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論壇舉辦前夕,《新民周刊》與徐院士進行了電話連線。
不搞創新是等死,搞創新是找死?
新民周刊:我國目前正在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并確定了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但是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搞創新是等死,搞創新是找死。因為創新需要大量投入,但收效卻又不能立竿見影,很多情況是:企業投了很多錢進去,幾年內都看不到成果,最后因資金短缺而死掉。所以,企業哪怕是等死,也不敢貿然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去搞創新。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徐冠華:對很多企業來說,“等死”也好,“找死”也罷,都是對當前狀況的一個形象的總結。
說“不搞創新就等死”,是企業認識上的一個飛躍,當然也是一種切膚之痛。企業如果沒有創新,就很難在競爭中生存、發展。
至于說“搞創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對于創新的認識和支持,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特別是政府部門,應該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讓企業勇于去搞創新,并且有能力去搞創新。
鼓勵企業創新政府該做什么
新民周刊:企業是創新的主體,這已經成為共識,那么政府應扮演什么角色呢?
徐冠華:政府要支持企業創新,需要從環境的建設著手,把創新環境的建設,作為支持企業創新的一個基礎的、主要的手段。
比如稅收政策,其核心是用稅收減免來鼓勵企業創新,讓企業感到創新既有付出,也能得到實惠。具體來說,就是采取對企業技術開發費用稅前抵扣的政策,有效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這是全世界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也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盡管有些個別省市自行制訂了具體細則,但在國家整體層面上,具體細則仍然沒有出臺,這在一定程度上銷蝕了企業的創新動力。
徐冠華:除稅收政策外,用好政府采購政策,有利于新興產業的發展,對支持企業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但目前這一政策急需得到落實。以前有種說法,叫做“同等優先”,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全面的,也無法實施。
因為“同等”實際上不存在。我舉個例子,比如軟件,一個產品一旦進入市場,如果沒有經過千千萬萬用戶的使用,是不可能發現潛在漏洞的,它需要不斷修改、完善。一個小公司這樣,大公司也如此,比如微軟的軟件就有不少“補丁”,如果一開始就要求產品非常完善,中國軟件產品永遠不可能進入市場。另外,在價格上,當我們的公司推出一個新產品的時候,跨國公司的產品往往通過降價把你擠垮,我國的小公司怎么與之競爭?所以,以價格和技術水平“同等優先”為原則的政府采購,容易演化為“國外產品優先”,使國內一些優秀的產品被排除于市場之外。
再比如我們的大飛機項目,即使我們的產品取得了“適航證”,飛機搞得再好,與飛了數十億公里的波音、空客飛機相比,我們的飛機終歸是新的。如果沒有政府采購支持的話,我們可以說是很難和國外產品競爭的。
政府不宜自己操辦高科技企業
新民周刊:創新的人才投入和資金投入是巨大的,我國的中小企業是否有這種能力?
徐冠華:我國65%的發明專利是由中小企業獲得的,80%的新產品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我國54個國家高新區內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超過80%。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鑒于高科技企業風險大、高科技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特點,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不一定自己直接操辦這些高競爭性的科技企業,這樣風險太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創造環境,讓市場進行大浪淘沙、優勝劣汰。
實踐也證明,國際上一些知名的大企業(像惠普、微軟、戴爾等),都是從小企業滾動發展、成長起來的;這些年來,我國的聯想、海爾、華為等企業也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可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科技企業成長的主要形式。
為何不以高校為技術創新主體?
新民周刊:目前很多高校在搞科研成果產業化,這是否與“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相背離?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高校應如何定位?
徐冠華:對于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當然,高校的任務首先是培養創新人才,同時也要在科技創新中做出自己的貢獻。高校的貢獻應體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做好基礎研究、前沿高技術研究。現在問題是,我們的基礎技術積累不夠,很容易出現創新動力供應不足的問題。其二,在以企業創新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工作中,發揮高校的重要作用。
現在很多高校質疑,為什么創新要以企業為主體、而不是以高校為主呢?我的看法是,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活動的過程,它不僅包含科技的創新,還包含管理、市場、商業模式以及金融運作方面的創新。我們不可能要求大多數大學教授或研究員都可以完成這一個全過程,即每一個人既是技術專家,又是企業家,這不現實。
大學的自身特點決定,它們必然注重技術指標的先進性。但技術指標的先進,往往并不意味著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比如,技術很先進,但產品的價格高,沒人買,它就不具備競爭力;還比如一項技術,如果不能和其他技術集成,就不能形成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是很多科技成果轉化并不成功的一個原因。
把支持創新作為國家基本戰略
新民周刊: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一些國家把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大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形成日益強大的競爭優勢,如日本、芬蘭、韓國等。國際學術界把這一類國家稱之為“技術創新型國家”或“創新型國家”。請問徐院士,這些國家的共同特征和典型經驗是什么?
徐冠華:目前世界上有20個左右的國家屬于這類國家。它們的共同特征是:科技進步貢獻率在70%以上;研發開支占GDP的指標大都在2%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都在30%以下。這些國家獲得的三方專利(美國、歐洲和日本授權的專利)數占世界總量的97%。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韓國是從落后國家發展為創新型國家的成功范例。1962年,韓國人均GDP只有82美元,與我國當時的水平大體相當;到2001年達到8900美元,比我國高出9倍之多。2007年,韓國的人均GDP更是達到20000美元,遙遙領先于中國。更重要的是,在半導體、汽車、造船、鋼鐵、電子、信息通訊等領域,韓國都比我國較晚起步,但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已走到我們前面,并躋身世界前列。
韓國在許多重要產業技術領域的創新能力培育上取得了突出成績。1990年,韓國政府決定修建漢城至釜山的高速鐵路,并決定引進法國的技術。從1995年引進第一輛法國高速列車開始,它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已掌握了高速列車研發和制造技術,并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時速為350公里的高速列車,提出向我國出口。韓國的核電技術,從引進、消化到自主制造,前后用了20年時間,現在已經向世界輸出核電技術和裝備。汽車制造業,從引進日美技術到形成自主品牌出口國際市場,前后用了10年時間。移動通訊產業,從引進美國的CDMA技術到實現產業化,前后只用了4年時間,目前已占據全球90%的CDMA市場份額。
我們研究發現,韓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培養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
一是始終致力于培育和發展自身的技術能力。從60年代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開始,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經費比例達到1:5。
二是持續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0.77%增長到2001年的2.96%,近些年來一直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遠高于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
三是大力支持企業研發活動。企業研究開發機構從1978年的48個,增加到現在的超過10000個。企業已經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像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等公司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技術創新的領先企業。韓國正在實施新的科技發展規劃,重要目標是2015年成為亞太地區的科研中心,并進入世界前10個領先國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