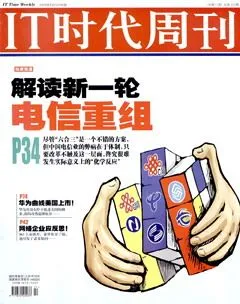中國缺失個(gè)人對社會的信托責(zé)任
郎咸平
早期,歐美職業(yè)經(jīng)理人基于信仰而有信托責(zé)任;今天,對法律的畏懼讓他們不得不替社會創(chuàng)造財(cái)富。
現(xiàn)在中國職業(yè)經(jīng)理人處在什么時(shí)代呢?我認(rèn)為是歐洲的中古時(shí)期,一切只為自己打算,所以我們的企業(yè)家如王石、馬云,才會講出“不愿多捐”這種話。
就地震一事,談一個(gè)沉重的話題:除了因?yàn)榫杩钍录爸摹比f科及阿里巴巴之外,截至5月21日,國際上的幾個(gè)大公司,尤其是在中國賺了大錢的大公司也沒怎么捐錢,如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dāng)勞、LV、大金、寶潔、摩托羅拉等。
但是我還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場,我不是來罵人的,而是想從文化、從歷史的層面來討論問題。我們來談?wù)搩蓚€(gè)人:一位是比爾·蓋茨,一位是巴菲特。他們兩個(gè)不是簡單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他們是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gè)擁有超大型上市公司的億萬富翁。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分別成立了不同的基金會,叫公益基金會。比爾·蓋茨的基金會叫比爾和梅琳達(dá)一蓋茨基金會,他把幾乎所有的財(cái)產(chǎn)都捐給了基金會。他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財(cái)富取之于社會,要還之于社會,我只是幫助大家管理這份財(cái)富而已。”
比爾·蓋茨說他只給子女每人留100萬美元,供養(yǎng)他們到大學(xué)畢業(yè)之后,他這個(gè)做父親的職責(zé)就盡到了;巴菲特前年也把自己的一些錢捐進(jìn)了他的基金會,他的思維和比爾-蓋茨是一樣的。我絕對不是在夸獎比爾·蓋茨,也不是責(zé)備我們的企業(yè)家。

請大家想一想,他們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業(yè)家,為什么想法如此不同?此外我還要告訴大家,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大家千萬不要說,比爾·蓋茨是對的,王石、馬云他們是錯的,不是這么簡單。我們不要拿一把道德的利劍隨意揮舞,因?yàn)檫@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現(xiàn)在不少專家學(xué)者說,國營企業(yè)做不好,是因?yàn)闁|西不是自己的,還提出個(gè)“冰棍理論”。所謂“冰棍理論”就是企業(yè)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會像冰棍一樣逐漸融化,還不如在融化之前送給國企老總。這些專家學(xué)者就是這樣教育民眾的。
在這種教育之下,我們中華文化優(yōu)良的傳統(tǒng)美德、是非善惡判斷標(biāo)準(zhǔn),已經(jīng)蕩然無存。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信托責(zé)任呢?他對老百姓的責(zé)任呢?都變得不重要。
我講到這兒大家就已經(jīng)明白了。在這種背景之下,馬云或者王石這么講話,你覺得奇怪嗎?這種歷史文化所孕育的企業(yè)家就這種水平,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至于可口可樂、摩托羅拉為什么不在中國捐錢?他們沒有職業(yè)經(jīng)理人的信托責(zé)任嗎?不是沒有,情況非常復(fù)雜。由于種種原因,歐洲企業(yè)原有的信托理念到了14世紀(jì)之后頓然瓦解,所以從歐洲中世紀(jì)開始,這種由宗教而來的信托責(zé)任同樣沒有了。
到了19世紀(jì)、20世紀(jì),像可口可樂等企業(yè)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階段。這段歷史非常重要,那就是從1890年起美國政府開始反托拉斯,搞了一個(gè)《反壟斷法》,用嚴(yán)刑峻法逼迫美國企業(yè)“不得不有信托責(zé)任”。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發(fā)的,19世紀(jì)之后是強(qiáng)迫的。
大家想想看,美國的上市公司和中國的不太一樣:中國的大股東很多都是家族、個(gè)人,但美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民都是中小股民。
因此,美國政府利用法律的力量強(qiáng)迫這些職業(yè)經(jīng)理人要替中小股民創(chuàng)造財(cái)富。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法律伺候、坐牢,就這么嚴(yán)格和簡單。
這種制度的好處,就是讓歐洲一千年以前的信托精神、信托制度以相近的形式得以延續(xù)(當(dāng)然原因已經(jīng)與宗教無關(guān)),逼迫職業(yè)經(jīng)理人有社會責(zé)任感,替這個(gè)社會創(chuàng)造財(cái)富,因?yàn)樗械纳鲜泄径际沁@個(gè)社會的中小股民、老百姓所持股的。
那么今天中國的許多職業(yè)經(jīng)理人有什么敬畏的嗎?沒有的,我們不信神。那么我們這個(gè)國家有像美國一樣嚴(yán)格的法律,逼迫他們不敢不有信托責(zé)任嗎?暫時(shí)還沒有、
其結(jié)果,就是一切只為自己打算。所以大家不要感到奇怪,為什么會有只捐1元錢的舉動,這是我們這個(gè)轉(zhuǎn)型時(shí)期社會的一個(gè)特殊產(chǎn)物。
難道比爾·蓋茨跟巴菲特比我們的企業(yè)家更有道德良心嗎?我不相信。但是我告訴你,我們有著不同的歷史,所以我們的企業(yè)家像王石、馬云,才會講出這種話。
每一個(gè)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所以我們要呼吁,做好對下一代的教育。大家要想一想,我們中很多人過去一切只為自己打算的做法對不對?要怎么教育下一代?這種現(xiàn)象可能延展到什么地步?
今天大家不要光責(zé)怪王石跟馬云,要想想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想想個(gè)人對社會的信托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