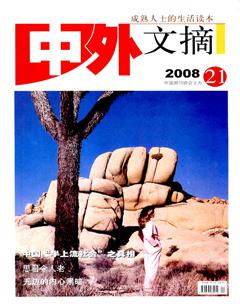通達圓融的人生
治 權
“一部白鹿原兩代恩怨,五載霸柳居十年苦寒”,這副對聯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寫給誰的。我與陳忠實的私交一直很好,我敬重他的文章,他看重我的書法;我喜歡吃陜北飯,他也喜歡。于是我們便經常在這些飯館碰面,有時還很親密地聊上一通。
不過,這樣的友誼只是近幾年才建立起來的。路遙活著的時候,我不認識陳忠實,因為我和路遙是同鄉,走得就近一些,因此從路遙口里大致知道陳忠實的一些情況。路遙說,作協這個地方,幾乎不出作家,所謂的作家,其實是“坐家”——坐在家里不干事,甚至與真正的作家搗亂,但有一個人除外,那就是陳忠實。他說陳忠實文學功底深厚,寫作實踐時間長,又有關中“愣娃”勁兒。因此路遙說,要在作協站住腳,僅有幾個短東西(其時路遙已經發了幾個中篇,尤以《人生》著名)不行,一定要回陜北,寫點像樣的東西。所謂像樣的東西,就是后來的《平凡的世界》。路遙是一個想到并能做到的人,他因此在陜北沉寂六年,《平凡的世界》最終獲得茅盾文學獎。
應該說,路遙是陳忠實的真正知音,他對陳忠實的看法十二分的準確。而陳忠實這時也正如路遙所說,墜入一種萬般痛苦之中。陳忠實其時已寫出一百多萬字的作品,有報告文學,短篇小說,散文隨筆乃至許多雜感,短篇小說連續兩次獲全國文學獎。但這一切,在路遙的《人生》面前,都算不了什么,都已相形見絀、黯然失色了。《人生》獲全國中篇小說獎,并被吳天明拍成電影,一時間紅遍了中國。人們來作協,都不找別人了,好像作協只有一個作家,那就是路遙!陳忠實后來說,他在作協是待不下去了!離開!只有離開,別無他法。陳忠實回到了他的家鄉,回到了妻子身邊——他妻子那時是農村戶口,養一群下蛋的母雞。
這情形很有點越王勾踐的悲壯。他每天清晨起來,喝一碗包谷稀飯,吃兩個白饃,便開始創作。沒有靈感就泡一杯濃茶,寫到高興處就吼秦腔,一章寫完,滿村找人下棋,楚河漢界地廝殺,猶如方格文字的鋪陳,陳忠實說,那是他當時最簡單也是最快樂的休閑。整整五年過去了,一本一本摞起來,字字心血,滿篇真言。捆起來有四五塊磚那么厚,抱在懷里分量沉重。陳忠實高興了,幾年心血沒有白費,賴好有了這堆東西,但他還是不能釋懷。作品是寫出來了,然而能否出版,能否“打響”都還是未知數。他因此對妻子說:“五年來,我就弄下這么一堆東西,現在我把它帶到西安去,打響了,回來接你們娘兒幾個到城市里去生活;打不響,一把火燒掉,回來我跟你一起養雞!”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陳忠實懷里的那一堆東西叫《白鹿原》,抱到西安后,不僅“打響”了,而且還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后來又被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老子在《道德經》中講:“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人生的事情大致如此。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獲茅盾文學獎后,他很快就被有關部門內定為省作協主席。路遙其時摩拳擦掌,大有一番宏圖再展的構想。然而天不假年,路遙不久便被肝病打倒,去時年僅44歲。路遙死后,蟄居五年的陳忠實懷抱《白鹿原》回到西安,成為作協主席的最佳人選。我對陳忠實說:“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年滿清與李自成開了一個玩笑,現在你又與路遙開了一個玩笑。”陳忠實聽了突然默然,老半天才說:“從人的良知來講,我倒真不希望是這樣一個結果。作協主席的位子是什么,實在是身外之物。我當初寫作《白鹿原》,只是覺得在那樣一種形勢下,我應該有一部大部頭作品、好作品,至于其他,那只是意外的事情。我想路遙當時創作《平凡的世界》,也應該是這樣的心情。這正如江姐她們在渣滓洞時的信念只是共產主義,而并沒有想什么要當省長之類的事情一樣。”
陳忠實的話讓我默然,也有些自愧,知道自己這個玩笑開得有點過頭。是的,人世間的爭斗大多發生在“享樂”之時,而“患難”之時更多的卻是“謙讓、團結”。陳忠實在以后的日子里,似乎一直葆有這樣一種風度,做人十分低調,也很講究細節,這也似乎是我們自路遙之后一直能保持良好的朋友之誼的基礎。
前不久,省作協換屆,陳忠實辭去作協主席的職務,賈平凹當選。我本想給陳忠實打個電話,但終于沒有。陳忠實早已到了通達圓融的境界,“去留肝膽兩昆侖”,當“主席”的時候是個“意外”,辭職的時候更多的是自覺,我何必要畫蛇添足呢?
(摘自《做人與處世>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