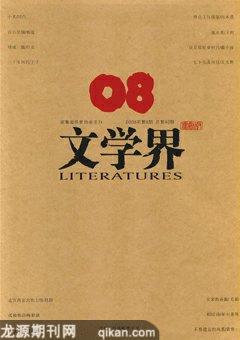小米(中篇小說)
凸 凹
一
謝小愚臨窗而坐,凝望著西山的那片天。
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西山頂上的云,層次著,像海灣的水,一波一波的。遠日像燒熟了的一粒炭火,紅得無力,但還是把云染紅了。這多么像沒有激情的愛情。他對自己說。
謝小愚是縣文化館的創作員,發表了不少作品,但一直是不溫不火,所以,他早就沒了野心,也不把自己當作家看了——不過是一份職業,生活著而已。
現在的文化館,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單位,辦公處所,是租來的,在銀行大樓的頂層。行長原來是個文學愛好者,對文藝有一點感情,在舊城改造,文化館舊址拆除,新館又籌建無期的時候,“賜”了幾間辦公用房。他說,堂堂的一個京西大縣,怎么就不能養幾個文人?
銀行大樓是本縣的最高建筑,共十一層。本來想建到二十一層,但北臨一個軍用機場,有規定,不能有十二層以上的建筑,只好簡約。這是個銀灰色的建筑,一水兒的落地玻璃窗,從外邊遠看,晶瑩剔透,富麗堂皇,熒光閃閃。
從樓里出來的人,都被路人高看。謝小愚有不名譽的感覺,搖頭笑笑,我算個什么屌?
他寫過一首詩,叫《十一樓的窗》——
這個房間在十一樓的西面
玻璃窗大得像沒有窗
窗前有一張床
單人
卻隸屬于一個四十歲的已婚男人
那個男人很無聊
因為他不停地寫作
作品篇篇都能發表
卻像篇篇都沒有發表
稿費單子一握進手里
他就掉眼淚
文學的職業
卻與文學無關
后來連眼淚都掉不出了
就凄苦出掉眼淚的樣子
弄得眼圈紅紅的
像一個很女人的女知己
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后來他竟相信
真有這么一個女知己真的為自己死掉了
她死前留下了一張手繪
畫的是一張單人床
面貌與十一樓窗前的那張一模一樣
他確信
她的死因
就是對這張床的渴望
雖然她從來沒到他的房間來過
確信著確信著
他的眼神便開始渙散
頭也負債般地低垂
他開始懲戒自己
不修邊幅,拒絕吃喝
然而他卻一天天發胖
胖得像一面墻
站在窗前
把那張床遮黑了
一天, 一個細脆的聲音
把他從昏睡中驚醒
發現一只陌生的黑鳥站在窗臺上
隔著玻璃望著他
臉型嫵媚
像女人動情時才有的那樣
他心情亢奮
手腳輕緩
幽魂一般把臉貼在窗上
黑鳥果然未被驚動
且平靜地看著他
他心中有了一絲亮色
那鳥從容地挪了一下身子
留下了一攤新鮮的鳥糞
他皺了一下眉頭
鳥畢竟是鳥而不是女人
不屬于期待
他推開窗子
鳥并不驚走
感動之下
在鳥的黑色羽毛上撫摸了兩下
鳥只是呱呱地叫了兩聲
沒一絲惶恐
陌生的鳥不怕陌生的人
男人也像鳥一樣呱呱了兩聲
后來,他退回了身子
從書柜兼貯藏柜上
找到了一只干硬的面包
他掰了一塊
立刻就碎在手心里了
回到窗前時
那只黑鳥已不在了
他搖搖頭
把面包屑撒在窗臺上
他自信,那只黑鳥還會再來
面包屑是預留的情義
甚至是隱隱的得意
黑鳥果然又來了
自然察覺了人的用心
但是
只是遲疑了一下
便從面包屑上踩了過去
停到了一個干凈的地方
羽翼收攏了一下就飛走了
剛才駐足的地方
又留下了一攤新鮮的鳥糞
男人的心抽縮了一下
難道這世間還有不食之鳥
他不能相信
再撒一層
黑鳥依舊來
依舊不食
只遺糞便
到了后來,陽光柔灑的窗臺上
赫然的一列鳥糞
組成了一個豪華的省略號
男人的心被刺痛了
無心寫作
久久地站在窗前發呆
鳥竟不再來
那鳥糞成了唯一的證明
證明這個死寂的地方
曾經有過鳥
一種比人還自由的東西
因為知道鳥不會再來
虛空的心反而充實了一些
無望賜給了他等待的理由
竟等來了一場小雨
把窗臺上的那列鳥糞浸潤了
陽光安靜地照射了幾天之后
每攤鳥糞上竟鉆出了針樣的嫩芽
那一排小翠
小小的小小的
小到他心里去了
嫩芽綻放不久便開始枯萎
眼睜睜地見證翠色短暫之后
他心中最溫柔的部分被觸動了
他咧咧地哭了起來
然后他打開了窗
決絕地站到窗臺上去
伸開雙臂做好了向外飛翔的姿勢
他看見
邈遠處那只黑鳥朝他飛來
窄窄的小臉上泛濫著豁然的笑
他明白
他一生的價值
就在這一次的飛翔了
身子朝前傾去的瞬間
身后想起了輕柔的敲門聲
他一怔,凝固在那里
開門吧,我知道你就在房間里
一個熟悉的女音自信而曖昧地說道
他苦笑了一下
出于本能
也出于對私秘氣息的反感
他只好結束這個過程
給女人開門
送走女人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窗
無可奈何地搖起頭來
此時的心境居然異常地平靜
飛翔的欲望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躺倒在單人床上
期待著
奇怪地
那份激情再也沒有出現在期待之中
無所用心的日子里
他的頭發漸漸地白了
白得令人肅然起敬
他再也不在窗前佇立
因為那會讓他感到羞恥
這首詩,可以說就是他的生活寫照,那個敲門而送進“熟悉的女音”的,是搞舞蹈的吳曉娜。吳曉娜總“粘”著他,每天都要來幾次。吳曉娜與他年齡相仿,面相庸常,為了填平時光的刻痕,總敷以過多的脂粉,就更庸常。但她的身姿卻始終異常地好,胸聳臀翹,曲線裊娜。這就讓他感到可笑,暗以老妖作比,懶得與她發生點多余的事情。
吳曉娜知道他對自己沒興趣,為什么還“粘”上來,是因為寂寞。
文藝吃香的時候,吳曉娜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各鄉鎮搞文化活動,排演舞蹈,爭著請她當指導老師,許多鄉下小伙子把她視作偶像。但很快就時興了交誼舞,聲光電色,男男女女,娛樂其中,費時費力的“正規”舞蹈就被冷落了,她也就不再有用武之地。就只有寄希望于搞些創作節目,到市里參加舞蹈比賽和區縣匯演。但是她缺乏創作才華,送審的節目不是被淘汰,就是叼陪末座,沒有脫穎而出的可能。從一個中心人物,一下子跌落為可有可無的角色,她承受不了,每天都到謝小愚這里來發牢騷:群眾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怎么越來越沒文化了?
謝小愚沒好氣地反問道,你這是問誰呢?
正凝望著,天霎地就黑下來。不是一般的黑,黑得不見萬物,像末日來臨。緊接著就是一陣驚雷,就是一陣呼嘯,密集的東西砸在窗玻璃上,叮當亂響。起初是驚悚,稍后就是興奮,甚至希望那玻璃被砸碎,他好破窗而出、乘風而去。
他索性合上雙眼,沉浸在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之中。
快感真是短暫,像響馬一溜煙地跑過,緊接著就是寂靜。
讓人驚恐的寂靜。
他試著睜開眼睛,發現窗外響晴一片,西天的落日好像晨曦中的初升,紅得銳利,割破了夜幕的胞衣,娩出了漫天的彩霞,可恥地美著。
廣闊的落地窗竟也無一絲破綻,他搖搖頭,罵了一句:囚籠。
手機響了,是他老婆林成鳳打來的。
謝小愚,你看見下雹子了嗎?劈頭就問。
謝小愚皺了一下眉頭,冷冷地問道,什么事?
我要去查看一下災情,晚飯你就別等我了。
呃,那好。
你是怎么了,這么有氣無力的?老婆問。
他找不到一個妥帖的措辭,嘿嘿一笑,啪地就把電話掛了。
我謝小愚已無心溫柔,你就擔待一下吧。
他站起身來,看著漫天的霞彩,心中一亮:走,去菜市場,買小米。
他的那輛紅色的破桑塔納,就露天停在院墻的一角。他本能地查看了一下,承受了一陣猝發的冰雨,車體上竟然一個麻坑都沒有,他一笑,這他媽的鋼板,跟人一樣,又賤又皮實。
但很快他就收斂了笑,因為他還是發現,車的右尾,有一道新的擦痕,傷口上敷以暗青的樹屑。
院墻外有棵高大的皂莢樹,虬曲的枝干諂媚地探進院里,經受不住冰雹的打擊,斷了幾枝。較大的一枝就落在車右尾部的水泥地上。
車子開出院子,就是兩排人行道樹。他挑了挑眉毛,故意偏打了一下車輪,讓車的左尾朝一棵樹的樹干上蹭了一下。
他下車看了一下,很得意,擦痕正與右邊的對稱,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來。
他的這輛車,是從舊車市場買的。買車的原因很簡單,他老婆林成鳳是城關鎮主管農業的副鎮長,有一部紅旗牌的專車。他覺得這很不公平,自己也“專”了一輛。老婆的車一旦有刮蹭,公家就修了,而他的車,得自己掏腰包。他覺得對一部舊車,正如對一個老情人,用心深了,就顯得很矯情了,索性就不修。袒露著傷痕,還風流有自,反而有個性,有品質。但傷痕必須對稱,一對稱,就不是傷痕,正如一個品牌的牛仔褲,兩個膝蓋都打著補丁,不是舊,而是時尚。
林成鳳發現了這一點,說,你們文人都有病,喜歡自我欺騙。
謝小愚點點頭,你說得不錯,還有點深度。
他到了城南菜市場,把車子隨便一停就往里走。一個戴紅袖標的人把他叫住,你怎么停在這兒?
你說我停哪兒?
那個人指了指遠處的停車場。
謝小愚沒理他,還往里走。
那個人說,小心給你拖走。
謝小愚笑笑,你隨便。
那個人不說話了。因為他知道,這種開舊車的人不好惹,就像個癌細胞,不動它還會安然無恙,一動,反而擴散了。
謝小愚到了買小米的地方,問,小米多少錢一斤?
小販反問道,你要哪種?見謝小愚皺了一下眉頭,小販說,一種三塊,一種兩塊五。
有什么不同?
小販把手插進一只口袋,撈上一把,然后攤開手掌。你看,這就是三塊的,金黃金黃的,脫皮精米,免淘洗。
小販又把手插進另一只口袋。你看,這就是兩塊五的,土灰土灰的,谷皮多,得多淘幾遍。
謝小愚眼睛一亮,那好,給我來五斤兩塊五的。
小販猶豫了一下,說,先生,一看您就是有身份的人,您還是買三塊的好。
謝小愚瞪了小販一眼,你看我哪兒寫著身份呢?
謝小愚買了五斤兩塊五的小米,像終于猜透了一個疑難謎底,有些興奮,雖然那個戴袖標的人就站在他車的跟前,也視而不見,拉開車門就要上去。那個人說,這就走了?
謝小愚一愣,你要干嗎?
我給你看了半天車,你連一聲謝都不說?那個人很委屈。
聽口氣人家沒有刁難他的意思,謝小愚給了他一支中華牌的煙,謝了。
那個人吸了一口,竟把身子靠在他的車門上。哥們,你是不是太小氣了?
你什么意思?
那個人瞟了兩眼他手中的煙盒。
謝小愚一下子明白過來,把整盒煙扔給了他。
這還差不多。
中華煙是林成鳳給他的。他總覺得煙里有腐敗的氣味,并沒有高貴的品質,抽得輕蔑,隨意。創作室的煙缸里,都是老大截子的煙蒂。吳曉娜說,你真能作踐。他說,又沒作踐你。吳曉娜說,那就作踐一回。他一笑,你想得倒美。
一盒煙扔出去,就像扔出了一個屁,他想笑,又隱忍了。
車子開出了菜市場,他覺得那個市場管理員人不錯,厚顏無恥,功利市儈,但真實。
二
謝小愚出身在京西大山里的一個小山村。父母是地道的山民,如果不趕上恢復高考,他肯定會一輩子窩在那里。
那里的土地都是旱地,種不了小麥,只能種玉米、高粱和谷子。玉米、高粱產量高,但不好吃,山里人管其叫粗糧。谷子產量很低,但小米燜飯香而有咬勁,是難得的細糧。由于產量低,只有在年節的時候,才可以上飯桌。所以,山里人對小米又恨又愛,感情深厚。
謝小愚在城市里生活之后,吃什么美食,都覺得沒滋沒味,他貪戀小米。
談戀愛的時候,林成鳳認為這是美德,證明謝小愚這個人有樸實本性,靠得住。一個屋檐下生活得久了,她就有些不能忍受了,覺得這是山里人的劣根性。這也不能怨她,吃小米她有生理反應,嗓子眼咽不下去。
謝小愚一到秋天,就會急迫地回一趟老家,他會弄回來一口袋新下來的小米。
小米是他與家鄉血肉相連的臍帶。
遺憾的是,近年來,老家也不種谷子了。退耕還林,吃國家供給的大米白面。
族叔當著村里的支書,謝小愚對他說,你干嗎不種幾畝谷子?小米現在是全新口味,是細糧中的細糧。
族叔搖搖頭,說,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趕情你生活在城里。那意思是說,山里好不容易吃上了大米白面,你卻呼喚小米,安的什么心?
謝小愚憂傷地生出感慨:遠離小米的,深情地眷念小米;可以與小米廝守的,卻那么厭棄小米,這叫怎么回事呢?
林成鳳說,這就是人性。
謝小愚很生氣,去你媽的,拽什么拽?
林成鳳說,你就不能尊重我點?
謝小愚說,我對你還不夠尊重?尊重得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看你是嫌棄我了。林成鳳很傷心。
你才知道?謝小愚感到還不過癮。
接下來,兩個人半個月不說話。
不說話,林成鳳可以容忍;但她絕不容忍跟她分床——只要謝小愚睡在另一個屋里,林成鳳就會破門而入,掀開被子,扔掉枕頭,不把他搞到自己的床上去,決不罷手。
你這叫干嗎?沒皮沒臉,簡直是個村里的潑婦。
林成鳳一笑,咱本來就是村里出來的,沒那么多的講究。
林成鳳篤信一個鄉村哲學:金繩,銀繩,不如肉繩,要想拴住男人,一定要讓他近身——異夢尚可,分床無門。
真是無可奈何。
謝小愚只好在客廳里待得很晚,直到眼皮重得不可撐持,才懷著滿腔的屈辱,“窩”到女人的床上去。
白天又讀又寫,到了晚上,絕無讀寫的心情。便在客廳里看碟。
看碟是京城作家的雅好,他們別有用心,是為了偷立意,偷構思,偷細節;謝小愚出身質樸,宅心仁厚,他鄙視這種做法。他之于碟,是安頓無奈,與女人斗爭。
他的碟都是從京城作家那里借來的。市面見不到,屬于“盜”。盜的東西,異象紛呈,亂七八糟,別開生面。他看得心迷情亂,覺得自己的世界真是小,活得沒有意義。
肚子叫了一聲。
他摁了一下暫停鍵,踅到廚間。
冰箱里有半碗晚上吃剩下的小米飯,他看上一眼,淚水就下來了。
下班的時候,他遇到一個游販在賣新下來的香椿,立刻就買了兩把。新香椿賊貴,一把三兩的樣子,就賣到三十塊錢。但是他覺得,從尊崇自然的角度,這個價位是合適的。春意一濃,香椿就老,就無人問津了,若再被人“寵幸”,就得等到來春。苦夏,寒秋,雪冬,漫漫時光,承受遺忘,隱忍地積蓄,才終于綻出幾叢新芽——寸心卑微,幾近奢侈啊。
涼拌新香椿,現燜小米飯,乃神仙口味!他的腸胃,本能地就劇烈蠕動。
所以,他一進門就喊,林成鳳,給老公燜點小米飯。
林成鳳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香椿,說,吃香椿打鹵面豈不更好?
他說,新香椿,小米飯,會給人帶來好心情,你應該善解人意才是。
我就不該給你置備小米,林成鳳嘟囔了一句,很不情愿地進了廚房。
這一刻,他生出一絲多余的溫柔。因為,雖然林成鳳認為他的小米口味是一種劣根性,但還是定期地給他把小米買回來,讓他無話可說。
飯得了,林成鳳卻不上飯桌,坐在一旁撇嘴。
謝小愚看在眼里,心皺了一下,你干嗎不吃?
林成鳳瞪了他一眼,又進了廚間,再出來的時候,竟端著一碗方便面。
謝小愚的心又皺了一下,搖了搖頭,只好獨享美味。
他心里有一種隱隱的不快,好像吃的是嗟來之食,便故意把吃飯的聲音弄得很響。
飯竟越來越香,以至于超過以往的飯量。
林成鳳啪地把碗蹲在飯桌上,嚇了謝小愚一跳。他抬起頭看著她,眼神里送去一個問號。
林成鳳冷冷地說道,你吃沒吃過人飯?
話語雖尖刻,但謝小愚還是理解她的用意——他胖得都出現了“三高”(血壓高,血糖高,轉氨酶高),他們和睦的時候,林成鳳總是叮囑他要加強鍛煉,注意飲食。所以,他沒有生氣,難為情地笑笑,把碗里的半碗飯放下了。
這時,這半碗小米飯勾起了他滿腹的委屈,他覺得自己很可憐。
他突然冒出來一個念頭:跟丫挺的離婚。
有了這個想法,就兀地生出一種力量,他狠狠地抹了一把淚水,打開爐灶,磕破一枚雞蛋,做蛋炒飯。他把鍋鏟撞擊的聲音弄得很響。就是要讓你聽見,你憑什么能安然入睡?就因為你長得漂亮,我就得稀罕你?
飯炒得了,連同吃剩下的拌香椿,一同端到茶幾上。
他摁下播放鍵,故意把音量弄大了一些。
但臥室里沒有絲毫動靜。
他的屈辱便被放大了,把酒拿來。
因為“三高”,他已經戒酒了,但是,此時開戒。
喝過一杯酒,情緒更亢奮了一些——在一只鍋里討飯吃,竟沒有相同的口味,這樣的女人有什么意思?對,跟她離。
這么點小小的齟齬就想著離婚,這跟他們的婚姻基礎有關。
謝小愚學的是中文系,大學畢業,分到本縣的文化館。整天沉浸在文學的世界里,他敏感而憂郁。他最喜歡的一部書,是繆塞的《一個世紀兒的懺悔》,從這部書里,他得出一個結論:憂郁是愛情的母語。
一到黃昏,在晦暗的夜色中,他的憂郁來得更加強烈,彳亍在街頭,總想遇到一個美麗的女孩,跟她發生點兒什么。
但是小城的女孩大都帶有土色,與書中描繪的優雅遠些。他抱憾不已。
那天,他低頭過馬路的時候,被車撞上了。
撞他的是一輛紅色的自行車,從車上摔下來一個梳披肩發的女孩。女孩爬起來,朝他送來歉意的一笑。
這是致命的一笑。
謝小愚責怪的話,一下子咽了回去。
女孩子一笑,綻出兩顆深深的酒窩,既甜蜜又燦爛。有驚心動魄的美。
他呆呆地看著人家,眼前一片迷霧。他下意識地想,你算是撞到槍口上了。
那個女孩居然就工作在與文化館毗鄰的城關鎮機關。他大喜過望:這是個很近的射程。
他開始瞄準。
奇怪地,那個女孩,面對槍口,還露出歡喜,像期待著被擊中一樣。
僅僅兩次交往,他們就進了一片桑樹地,擁抱,接吻,身子扭動得像兩只饑餓的蠶。那個女孩呼出的氣味很醉人,甜絲絲的,像咀嚼干草時嘗到的那樣。他小時候,常隨父親上山打干草,口渴的時候,父親就叫他把草稈放到嘴里嚼一嚼,說能生津解渴。果然就解渴,而且那個味道沁人心脾。便培育出一個干草的味蕾。
這個味蕾,過于發達,牽動了他的情欲,他感到懷里的女孩極美好,手情不自禁地伸進人家的領口。他摸到了一顆飽滿的乳頭。女孩失聲叫了一聲,慢慢地癱倒下去。
這是個巨大的誘惑,他不假思索地覆蓋上去。
結束之后,那個女孩蜷縮著身子,嚶嚶抽泣。謝小愚手足無措,意識到,他惹麻煩了。
但很快,女孩自己坐了起來,竟破涕一笑,說,咱們去吃點夜宵吧。
居然沒有嚴重的事情。
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他的心情立刻就沉重起來。
這個叫林成鳳的女孩,還是個農村戶口,雖然在機關工作,卻是個臨時工。她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也沒考上專業學校,在家務農。鎮里一個主要領導在麥收下鄉的時候,在麥田里遇到了她。她的美貌讓這個領導大吃一驚,頓生憐惜,把她弄進了鎮機關。說是等到機會給她轉成正式干部,但那個領導很快就調走了,她的事就懸在那里。
這個情況讓謝小愚產生了許多猜想,不能釋懷。
這層憂郁,不可言說,只能皴在心里。
還有一層憂郁,是緣自林成鳳的性情——
比如他們一同騎車,見他騎得有些漫不經心,她說道,你騎穩當點好不好,別讓車撞了。他知道這是在關心他,但這個口氣顯得很不溫柔,不應該出自女孩之口。
比如到她家里吃飯。她母親燜的帶魚有些咸,謝小愚不敢多下筷子,她便端起盤子給他往碗里撥,嘴上還說,你怎么這么假,吃,吃。他知道她是怕他吃不好,是一種愛意,但做得是那么霸道,不容你選擇。
比如他們做愛。溫柔的程序中,她會給他講“狗煉丹”的故事。所謂狗煉丹,是農村對狗交配的說法。小時候,她在村口見過兩次,所以她描繪得有聲有色。她還作比,你看你,屁股一聳一聳的,像不像那只公狗?嘻嘻。謝小愚羞愧的直皺眉頭,心里說,怎么這么粗俗,哪里像女孩子。
比如跟人家吵架,她輕易地就能罵出男人都難以啟齒的粗口。
美艷的外貌,粗鄙的性情。
謝小愚有些難以承受,慢慢地,竟開始鄙視她的美貌。
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林成鳳幾天也見不到謝小愚的身影。
林成鳳終于有一天把他堵在屋里。謝小愚,你給我說清楚,你想干嗎?
小林,你看咱們之間是不是有些不合適?謝小愚囁嚅道。
林成鳳朝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姓謝的,你搞我的時候,怎么沒覺得不合適?搞舒坦了,卻覺得不合適了,你還是不是人?
這是兩回事。
林成鳳抖落了一下衣襟,居然抖落出一把刀子。謝小愚,你給我聽著,不能總是你合適,你要是敢甩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他們便進入了婚姻。
按當時的政策,一工一農戶,不享受福利分房,所以,婚后他們一點也不浪漫,而是操持磚、瓦、灰、沙,自己蓋房。
房子蓋起來了,謝小愚手上打滿了血泡,很長時間無心寫作。皮肉受苦是小事,要命的是,在最溫柔的時候,竟最徹底地看到了生活的艱辛與堅硬,痛感詩與浪漫是那樣的無用,生出幻滅的陰影。
林成鳳這一段時間,變得異常溫柔,一切家務都不讓謝小愚插手,對他百依百順。但他還是高興不起來,覺得自己的愛情,就像遇到大旱的新芽,剛一鉆出地面,就干死了。他甚至不愿意想到“愛情”這個字眼。
他懶得跟她親熱。
林成鳳也不計較,把自己主動送上去。她想,石頭在手里握久了,也是熱的,更何況金枝玉葉的一個大活人。她沒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嚴重,覺得謝小愚不過是夢想色彩濃了些,對實際的婚姻生活準備不足,暫時還不適應而已。
謝小愚在林成鳳的身上機械地動作著,思緒卻想著另一件事:在大學里,他曾經有過一個戀人,他們經常做愛,女孩子還為他做了幾次人工流產。到了最后那年,他感到那個女孩“小資情調”重了些,讓他這個鄉下人找不到心靈安妥的感覺,便提出分手。女孩子想了想,說,好。這個態度多少讓他感到吃驚,頓生慚愧,說,對不起了。女孩子笑笑,說,你這么說,很沒意思,褻瀆愛情。這之后,女孩子不僅沒有不依不饒的糾纏,畢業分別的那一天,還送給他一件手織毛衣,她說,本來就是給你織的,還是送給你吧。那一刻,他柔情大動,眼淚奪眶而出。只要女孩子稍有一個表示,他會毫不猶豫地重新回到她的懷抱。但是,女孩子只說了一句請你多保重吧,笑著走開了。
在噴發的一瞬間,他向上挺舉了一下,叫了一聲,陸小蘭。
陸小蘭是誰?身下的林成鳳問道。
什么陸小蘭?謝小愚反問道。
林成鳳把他掀翻下去,你心里清楚。
你別自討沒趣。他有些羞惱。
以為林成鳳要發作,沒想到,她只是沉默了一會,竟笑著說道,你就是心里想著陸小蘭,不還是得跟我做愛?有能耐你天天喊。
她的意思是說,男女是靠肉體套牢的,空想沒用。
林成鳳譏諷的口氣讓謝小愚難以承受,林成鳳,你怎么一點自尊都沒有?
林成鳳正色道,謝小愚,你扯淡!
第二天下班,謝小愚一進門就奔廚房,按以往的情形,一定有停當了的飯菜等著他。可今天卻是灶臺冰冷,空空如也。他氣憤地摔了一下廚房的門,對正在看電視的林成鳳質問道,你怎么連飯都不做?
林成鳳眼皮都不抬一下,笑著說,你讓陸小蘭給你做。
謝小愚不愿中了她的圈套,苦笑了一下,把身上的臟衣服脫下來,往林成鳳腳下一扔,那好,你去洗衣服,我來做飯。
林成鳳還是連眼皮都不抬一下,我沒這個義務,你去找陸小蘭給你洗。
謝小愚實在不能隱忍了,吼道,林成鳳,你要干嗎?
看電視。
謝小愚啪地把電視關了。
林成鳳笑著又把電視打開。
你現在怎么這樣?
是你讓我這樣。
謝小愚愣在那里,痛苦地感到,他又往深處淪陷了一步。
奇怪地,淪陷反而給了他一種動力,他拼命地讀寫,作品不斷地發表,在文壇有了小小的聲名,就連外地都有文學團體請他去講課。在文學青年的簇擁下,他感到,女人的溫柔,甚至愛情的甜蜜,其實是不重要的,事業才是生活的支點。
重心的轉移,鈍化了心中的遺憾,他把婚姻維系了下來。
人們都羨慕他們,說他與林成鳳郎才女貌,是天生的一對。
他麻木地一笑,不作分辨。
三
半碗小米飯,因為酒的緣故,在肚子里發酵了,竟誘發了一股莫名其妙的、而且還是異常強烈的情欲。
他推開了臥室的門。
林成鳳竟醒著,嘟囔了一句,這么晚了還不睡,抽的什么風?
謝小愚立在門邊半天沒說話。他在想,形而下的東西居然對人有那么大的支配作用,還真不可抗拒——雖然鄙視跟這個女人的肉體之歡,但眼下還真的需要她的肉體。
這讓他有些難為情。
但是他又想,如果他提出要求,如果她識趣,就屈從于婚姻吧。
他坐在床邊,輕輕地推了推林成鳳,終于說道,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身體?
之所以說得如此粗鄙,是因為他還放不下最后的尊嚴。
林成鳳哼了一聲,扭過身去,你還是找陸小蘭借吧。
謝小愚僵在那里。
像剛要結痂的的傷口又被撕裂一樣,痛而屈辱,難以平復。那好,我們離婚吧。他說。
林成鳳一笑,竟說,離就離。
早晨一上班,他就對吳曉娜說,我要跟林成鳳離婚了。
吳曉娜撇了撇嘴,你開什么玩笑?
真的,林成鳳她也同意。
這就更不真實了。吳曉娜說,你們這是在說氣話,婚姻就像風箏,牽引的線握在女人的手里,即便她栽了跟頭,手也是不會撒開的。
那我就橫空割上一刀。
那得狠,得冷酷,你是那樣的人嗎?
你說我是什么樣的人?
吳曉娜笑而不語,轉身走了。
這種態度,類似輕蔑,謝小愚頹然坐下,久久地發呆。
午飯過了,他還坐在那里,吳曉娜進來問他,你還吃不吃飯?
我吃你!謝小愚惡狠狠地說道。
那好,你等著。吳曉娜扭扭地走了。
謝小愚捕捉到了吳曉娜的背影。這個背影腰窩深陷,臀重而翹,風情萬種。他不禁想到,我何不借機用它一次?
他懷著一種游戲的心情撥吳曉娜手機的號碼,剛要按“呼出鍵”,又停住了。因為他有一種預感,吳曉娜的話不像是戲語,她肯定會自己送上門來。
他耐心地等著。
門無聲地開了,進來的果然是吳曉娜。
她的頭發濕漉漉地披在肩上,遠遠地就聞到一股名牌洗浴液的香味。濃烈,驚險,讓他心動,又讓他厭惡。
她手里端著兩個果盤,一盤是櫻桃,一盤是菱棗。都是剛上市的,口感很好。她說。
這種體貼,讓謝小愚聞到了淫穢的味道,他說,那好,咱們在床上吃。
他看了一眼窗前的單人床,搖搖頭,該死,為什么偏偏就有床?
吳曉娜笑笑,把窗簾拉上了。然后,不緊不慢地解上衣的扣子。眼睛直視著謝小愚,笑瞇瞇的。
謝小愚本能地低了一下頭,但很快又抬了起來。女人的笑,與挑釁相仿,他不能敗下陣來。
吳曉娜竟沒穿內衣,外衣的扣子剛解下兩粒,兩個乳房便爭搶著滾了出來。
她的乳房肥大,卻挺拔,質地華美。
謝小愚在驚嘆的同時,竟感受到了一股徹骨的寒冷。
因為他想到了林成鳳。
林成鳳的到場,給了他一個痛苦的坐標——吳曉娜豐乳肥臀,性感噴薄,而面相式微;林成鳳美貌如花,詩意盎然,而身材平庸——遺憾有自,均不完美——吳曉娜可悲,林成鳳亦可悲。
你以為你是誰?
你不可能東床美貌,西床美體,占盡人間春色。一旦在遺憾中邁進,會亂了口味,便感受不到女性的美好,只剩下輕薄了。
所以,真要是那樣,最可悲的還是他謝小愚自己。
寒冷讓他卻步,他擺擺手,說,吳曉娜,我服你了,但我還沒有準備好,放在來日好不好?
吳曉娜有些羞惱,瞪了他一眼,謝小愚,你這個人真不怎么樣。
謝小愚說,吳曉娜,真對不起,我這個人的確不怎么樣。
吳曉娜說,謝小愚,你以后別再跟我說離婚的事,因為你不可能離婚。
為什么?
只有到了能夠無所顧忌地跟別的女人瞎混時,男人才有勇氣離婚。
都說搞舞蹈的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沒想到,你卻是個例外。
你剛知道?
接下來,他們開始吃櫻桃菱棗,都感到時鮮的水果就是好吃。他們娓娓而談,心無塊壘,好像不曾有難堪的事情發生。
送走吳曉娜,再想到與林成鳳離婚的事,謝小愚自己都感到可笑。
但卻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是陸小蘭打來的。
謝小愚很吃驚。
陸小蘭臨別時送給他的那件手織毛衣,給了他一分警惕,他不愿意藕斷絲連、拖泥帶水,便更改了電話號碼,斷了聯系。
你是怎么知道我電話的?謝小愚劈頭就問。
這個很容易,如果女人愿意。陸小蘭說。
接下來兩個人半天不說話。
還是陸小蘭首先打破了沉悶,你怎么不問問我過得怎么樣?
那好,請問,你過得還好?
不好。
為什么?
我很想要個孩子,可是結婚這么多年了,一直不能如愿。
為什么?
我總是習慣性流產。
為什么?
你還不知道?
謝小愚心頭一震,你告訴我這些,是什么意思?難道你要讓我跟我老婆離婚?
陸小蘭笑笑,謝小愚,你怎么還是那么狹隘?
謝小愚笑不起來,那你為什么要告訴我?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
陸小蘭還告訴他,由于始終沒有自己的孩子,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很不好,老公對她動不動就又打又罵,但是又不跟她離婚,她倍受煎熬,心里很灰。
陸小蘭對他說,你不要有什么壓力,我并不想讓你對記憶中的情感承擔什么,只是想讓你知道,男女之間是兒戲不得的,即便是兒戲,也有兒戲之外的后果。所以,你一定要善待你老婆,她一旦受到傷害,恐怕不會如我。
那你怎么辦?謝小愚隨口問道。
兩個字,忍受。
謝小愚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話到嘴邊又感到這很無恥,便咽下去了,只是說,你有事就打電話。
陸小蘭說,你放心,我不會再打擾你了。
接過陸小蘭的電話,像身體里的核心部分被抽調了,整個下午都頹然地坐在那里。陽光和煦而無力,落地窗上爬了幾只大頭蒼蠅,也久久不動。他感到很刺眼,離開座位去哄趕它們。但人在里,蒼蠅在外,被透明而堅硬的玻璃隔著,他的拍打不被理睬,蒼蠅鎮定地趴在原處,像死了一樣。
他只好踅回座位,有人不如蠅之感。
但是,當暮色分娩出夕陽的紅潤的時候,血液突然涌動起來,他聽到了一個叫“自由”的呼喚。
他霍地站起,離,一定得離!
因為女人如縲紲,讓男人困頓、矮化、失真,以至于舉足無措,找不到自我。
自由,對,就是自由!
形而上的誘因來得比具體的理由更具有說服力,因為它類似信念,冠冕堂皇,激動人心。
信念一旦堅定,他有些得意洋洋。他提前回到家里。
沒想到,林成鳳比他回來得還早,坐在沙發上,滿臉愁苦。他一笑,你是不是正等著我簽離婚協議書?
林成鳳竟站起身來,撲進他的懷里,嗚嗚地哭了。
他說,別這樣,俗話說,長痛不如短痛,離了就好了。謝小愚以為林成鳳是在為就要破裂的婚姻唱挽歌。
林成鳳哭著說,恐怕你打錯了算盤。
你這有什么意思,謝小愚想推開她,但越推她抱得越緊,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個物件。
謝小愚比什么時候都厭惡她,哼了一聲。
林成鳳說,我可沒有你那么多多余的心思,我就要被單位裁減了。
什么?謝小愚感到很意外。
林成鳳告訴他,鎮上新上任了一個黨委書記,搞機構改革,要裁減一大批人,因為她不是正式干部,理所當然地上了第一批裁減的名單。
怎么,連我謝小愚的老婆都敢裁減?他心一沉,隨口說道。
林成鳳凄然一笑,搖搖頭,一副無助的樣子。
謝小愚明白她想說而又不忍心說的話,你以為你是誰,不過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作家而已。
他頓生悲憫,輕輕地在林成鳳的后背上拍了拍。林成鳳呃了一聲,馴順地伏在他胸前,嗚噥道,我橫豎是你的老婆,這時候提離婚的事,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謝小愚柔軟的心被鋒利地割了一刀,他對林成鳳說,你在家里等著,我出去一下。
謝小愚先回了一趟文化館,把載有他作品的報刊裝在手提包里,然后直奔城關鎮的辦公大樓。
那個黨委書記正在辦公室里。他進門就作了自我介紹,我是謝小愚,作家。黨委書記一愣,作家?寫什么的?謝小愚說,什么都寫。他把那些報刊攤在書記的辦公桌上,其中的一本著名刊物上,整個封面,登著他的一張照片。書記眼睛一亮,不簡單,還是封面人物,你請坐。
看來這個身份的證明還是管用的,謝小愚心緒從容了一些,坐下了。
他說,我來是為林成鳳的事,他是我夫人。
書記說,是嗎?
謝小愚靈機一動,說,我聽林成鳳說,您很有魄力,正在搞機構改革。
書記一笑,不敢當,只是不改不成。
謝小愚說,我也是改革派,所以,我想對您的改革進行追蹤采訪,寫一篇大文章,在市報上發表。
書記先是一笑,而后卻搖了搖頭,說,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未必就能成功,所以,我不想做什么宣傳。
謝小愚心頭一震,目光有些游移。但游移的目光讓他捕捉到了書記的形象:西服革履,鬢發講究。這給了他一個判斷,此人有弱點,愛惜羽毛。他說,您說得很對,但是我想,現在是資訊時代,人們非常關注媒體,往往是從媒體上獲取是非與成敗的判斷。所以,那些成功的改革者,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邊干邊說,甚至不干先說。不說,誰能了解你的意圖?不說,誰又能理解你的苦心?所以,搞不搞宣傳,不是一件小事,它能讓改革者最大程度地得到社會認同和人心支持。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進則八面風助,退則四方同情,換言之,成則崇高,敗則悲壯,盡顯風流。
說得好,說得好。書記說,那就宣傳?
自然。謝小愚說,您盡管交給我。
書記說,謝先生,你來得正好,縣統計局要在鄉鎮建一支專業統計員隊伍,也給了咱們鎮一個名額。不過,不是戴帽分配,得報名競考,一旦考上,就是正經的公務員了,你看機會多好?趕緊讓尊夫人報名,我私下里關照一下,爭取讓她考上。
林成鳳報了名,領到了復習提綱。謝小愚一看,考試范圍基本上是高中課程,不禁一笑,對林成鳳說,這太容易了,真是白給的機會。林成鳳卻皺緊了眉頭,這么難的題目,你卻認為容易,你安的什么心?
謝小愚問,你是不是高中畢業?
當然,不過,高中三年基本上是混過來的。
既然是這樣,我自認倒霉,幫你輔導。
接下來的日子,謝小愚放棄了自己的寫作,白天跟蹤采訪書記的改革,晚上輔導林成鳳的功課。
白天的采訪很順利,晚上的輔導卻遇到麻煩。一個章節,他反復講解,林成鳳就是聽不懂,好不容易聽懂了,一做習題,就錯得一塌糊涂。他笑著嘟囔了一句,你怎么這么笨?
雖然是一句玩笑,林成鳳卻不堪忍受,她賭氣地把課本扔到一邊,含著眼淚說到,你謝小愚要是真的有能耐,就給我找一個不用考試的名額。
謝小愚趕緊哄勸,沒關系,咱們再來。
林成鳳索性把身子扔到床上,姑奶奶不想受這份洋罪,咱不考了還不成。
謝小愚再也不能容忍了,說道,當老師的還沒煩呢,當學生的卻煩了,你還講不講道理?
硬著頭皮考下來了,林成鳳只考了四十多分。如此分數,實在無法做手腳,名額自然屬于了別人。謝小愚暗自苦笑,因為試卷上的題都是基礎知識,答起來很容易。所謂考試,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他覺得林成鳳真是一只繡花枕頭,不禁嘆道,我怎么娶了這么個女人?
這個結局也出乎書記的意料,他皺了皺眉頭,說,只好再尋找機會吧。
書記的這個表情和語氣,讓謝小愚感到很沒面子,對林成鳳多了一層厭惡,心里說,跟這樣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真的沒什么意思。但是他又想,自己究竟是人家的丈夫,在人家遇到最基本的生存問題的時候提出離婚,離作家的良知遠些,也離男人的尊嚴遠些。
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為書記作形象宣傳。他心里清楚,他是為能夠順利地實現離婚的意圖而戰。
在這個期間,林成鳳懷孕了。當她興沖沖地把喜信告訴謝小愚的時候,謝小愚卻冷冷地說,做掉。林成鳳當時就哭了,罵道,謝小愚,你混蛋!他搖搖頭,笑著說,你不要意氣用事,你自己的身份問題還沒有解決,再被孩子拖累,你還有什么競爭實力?就等著被裁減吧。
其實他心里有別的想法:他看到過一個法國人搞的分析報告,說兒女的智力遺傳主要來自母親——就林成鳳那個智商水平,怎么能跟她生孩子?這輩子都別想。
林成鳳說,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怕你不好離婚。
謝小愚說,你要是這么想,我也沒辦法。
做掉孩子之后,林成鳳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解決自己的身份,不然我就太虧了。
謝小愚點點頭,我支持你。
在謝小愚的努力之下,書記出了大名,成了本縣的改革人物,被縣里列入縣級后備干部。書記與他成了好朋友,對他說,林成鳳的事他自有辦法。
林成鳳的工作崗位被調整了,從機關財務室調到農業科。農業科的下鄉任務很重,是沒人愿意去的科室。林成鳳一聲不吭地去了,因為她理解領導的用意,在艱苦的部門獲取的利益會多些,別人的議論也會少些。領導還囑咐她,你要一邊工作,一邊把農業函授大學的課程學下來。不僅僅為了文憑,而是為了適應工作,管農業的,不懂農業技術怎么成?
林成鳳白天下鄉,晚上學習,很辛苦。但她默默地承受著,沒有一絲怨言。
經受風吹日曬,林成鳳的臉黑了,手上還起了很多皮疹,美麗大打折扣。謝小愚看在眼里,悲從心生,他覺得,在生存的硬道理面前,女人的美麗,男人的才華,都是沒有用的東西。因為感到自己的無能,他羞于再動離婚的念頭。日子就這樣過下來了。
但書記給的這個期待,既不確定,又顯得漫長,在凄惶中,他的寫作熱情大減,沒有寫出什么重要作品。
兩年后,林成鳳不僅拿下了大專文憑,業務也變得十分熟練,在農業科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便水到渠成地轉了干,而且被提拔為科長。
但林成鳳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歡喜,她臉色陰沉,寡言少語,與原來的那個單純快樂的女人判若兩人。
謝小愚很不理解,問,林成鳳,該得意的時候你怎么不得意?
林成鳳說,我為什么要得意?為了你終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跟我離婚?
謝小愚被點中了穴脈,心中的飽滿立刻就被抽空了。被識破了的羞惱使他感到這個話題很沒意思,便說,你什么時候變得這樣刻薄了?即便是離婚,也是以后的事,眼下,我還要享受一下自己的奮斗成果。
四
從市場回到家里,謝小愚一直就興奮著。
今天是怎么了,莫名其妙地就想去買小米。
那兩塊五一斤的小米果真皮子多,他淘來淘去,還是有土灰的谷皮漾在水面。他索性不淘了,就那樣下鍋燜了。
溫火和煦,飯色漸黃,他聞到了一股久違了的味道,這種味道,屬于童年的記憶,屬于他的出身。
他迫不及待地嘗了一口,啊,正是故鄉的那種純正。
這場冰雨來的!
冰雨給了他一個意外的沖動,給了他一個猜透謎底的機會:二塊五與三塊的小米,雖然只有五毛錢之差,卻有著霄壤之別——怪不得這么多年來,雖然碗中始終沒有斷了小米,卻總也咀嚼不出令人安妥的滋味,原來就是因為這五毛錢的精化,把本分與本質加工掉了。
謝小愚干炸了一碗辣椒。在老家,沒有新香椿的節氣,干炸辣椒,是吃小米飯最好的配菜。
香透肺腑!謝小愚吃得滿頭大汗。
饕餮一番之后,他愣在飯桌前。
他在做形而上的聯想,他覺得這小小的五毛錢之差能說明很多問題。
比如婚姻。在老家,婚姻的內涵是很簡單的,就是娶妻生子,養兒防老。但一有了文化,情致就變了,不僅女人要美麗,還要溫柔,還要聰明,還要有共同語言和浪漫情調,否則就失意,就不滿,就要裂變。
比如生活。自己最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要通過上學高考走出那個封閉落后的山村,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端上一個鐵飯碗,解決衣食之憂,獲取一份生存保障。沒想到,這些目標實現之后,竟生出了其他的念頭:不僅要搞文學,要發表作品,還要獲獎,成大名,成焦點人物,被人家看重,有社會地位,否則就無聊,就心灰意懶,就痛苦不安。
唉!那十一樓的窗,華麗,奢侈,多余。因而,雖闊大,卻小。心靈無法自由伸展,便似囚籠。
不知吳曉娜她怎么想。
謝小愚不禁搖搖頭。
小米飯吃多了,他的胃很脹,便下樓去散步。他發現,小區水泥廊架上的藤蘿,被暴風吹落在地上,遍體鱗傷,像一條條的死蛇。走出小區,來到街頭,看到行人稀少,路燈冷清,素日牛屄哄哄的人行道樹蔫頭耷腦,殘枝遍地,無人收拾。他感到,雨后的響晴,絢麗的夕照,不僅美得可恥,而且毫無意義。
他突然就想到了林成鳳。
一個柔弱的女人,冰雹后的第一反應是察看災情,而自己,一個自視甚高、整天為別人指出意義的人,卻在享受個人口味,并為消解過剩的熱量而閑逛——謝小愚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
他撥了林成鳳的手機,卻是一片忙音。
過了一會,他自己的手機響了。他的心像被燙了一下,趕緊接通了電話。
卻是吳曉娜。
謝小愚,你在干嗎?
在遛彎兒。
你倒很有閑情逸致啊。
吃撐了。
林成鳳倒很會飼養你。
扯淡,她可沒你那么精細。
吃什么精飼料了,會撐著?
還有什么,小米飯而已。
你可真沒意思,市場里有的是小米,足可以滿足你那點可憐的愛好,還至于那么慌不擇食?
大街上有的是漂亮女人,未必就對我的口味。
謝小愚,你別耍貧嘴了,我跟他談妥了。
跟誰談妥了?
能跟誰?我的那口子唄,他同意跟我離婚了。
你離不離婚跟我有什么關系?
自然有關系,我可是精品小米。
我不喜歡精品小米,我喜歡糙米,谷皮特多的那種。
謝小愚,你裝什么蒜?你不是特想離婚嗎?
但是,我現在還沒解決好為什么離、為誰離的問題。
你真可笑。吳曉娜有些惱。
對方的態度,讓謝小愚感到自己好像增加了一個層次,心里說,你吳曉娜才可笑呢,你離了,我就得跟著離?這是哪兒的道理。
他覺得他與吳曉娜的生存狀態太一樣了——悠閑,懶散,單調,無聊,寂寞,虛空……和她攪在一起,只能做減法,發展到最后,由于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會發霉,會爛掉。
吳曉娜,我實話告訴你,我們之間沒戲,你不要自尋煩惱。謝小愚說完,把電話掛了。
只平靜了片刻,電話又響了起來。
還是吳曉娜。
他不接,電話很執著地響。
響了幾次之后,對方發來一條短信:謝小愚,我不會放過你的。
他索性把電話關了。搞舞蹈的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理智,不明事理。他心里不悅,腳底不穩,踩上一節斷枝,打了一個趔趄。他苦笑了一下,這種樹木都是速生,斷了就斷了,不能嫁接,只能期待著萌出新芽。他一時興起,去踢那斷枝,竟踢得很遠,他不禁放聲大笑,因為他突然發現,自己還很年輕,有的是力氣。
或許林成鳳已經回來了。他想到。
便急急地趕回家去。他是想,一個女人,過得這樣辛苦,應該給她一點憐惜,比如給她端上一杯水,熱一下已經擱涼了的飯菜。
越是炎熱的夏天,越是應該有熱的飯菜,不然會鬧腸炎,會拉肚子。他現在的心思很家常,卻感受到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溫厚。
林成鳳還沒有回來。
他決定等她。
他打開電視。電視節目很平庸,他看不下去,便換上影碟。碟里的情節玄、懸、炫,他感到有些鬧,也索性關掉。
他搖頭笑笑,他頓悟到:在有所牽掛的等待中,人竟容不下其他的什么。
他靜靜地坐在沙發上。
墻上的掛鐘走得很響。
以前怎么不響?
以往那顆自以為是、空蕩漂浮的心,不禁謙卑了一下。這一謙卑,心跳竟便換了節奏,沉甸甸的。
突然就想到了《沙恭達羅》里的一個句子——
因為臀部肥重,她走得很慢,裊娜出萬端風情。
他笑笑,覺得這個意象很美,從體態的從容,能看到內心的圓滿與充盈。
已經到了下半夜,以為林成鳳一定不會再回來了,卻聽到門鎖響了一下,他下意識地跳了起來,急迫地迎了上去。
女人推開門,看到一個肥大的身子堵在眼前,嚇了一跳,你?
謝小愚赧然一笑,不好意思,未經批準,我在等你。
還有吃的沒有?
不好意思,只有小米飯。
小米飯就小米飯吧。
那好,我去給你熱一熱。
不用了,一個搞農業的,胃皮實得能裝下沙子。
林成鳳吃得狼吞虎咽,無一絲女性嫵媚。
她是真餓了,顧不得挑剔口味了。
躺到床上之后,謝小愚居然主動擁抱了林成鳳,對她說,我們能不能親熱一下?
林成鳳一驚,你今天是怎么了?
嘻嘻,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人家都累得快散架了,哪兒還有這份心情?
嘻嘻,你不是想要個孩子嗎?
林成鳳猛地坐了起來,這么說,你不想離婚了?
嘻嘻,我一個落魄文人,哪敢跟鎮長大人鬧離婚?
謝小愚你正經點好不好?林成鳳說,跟你說實話,我在察看災情的時候,看到受災群眾臉上的表情,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尿不到一個壺里,還是離了好。
謝小愚愣了,久久地木在那里,不知說什么好。
你是累了,還是先睡吧。他終于說道。
林成鳳剛一躺平了身子,就開始打鼾,鼾聲很響,比男人還理直氣壯。
謝小愚笑笑,對自己說,林成鳳是個沒心沒肺的人,切莫把她的話當真,她不過是耍耍性子而已。
林成鳳的鼾聲弄得謝小愚失眠了,但是,他就那么躺著,一動也不動。
他怕弄醒了她。他默默地叨念著:二塊五、三塊,二塊五、三塊,二塊五、三塊……
他覺得自己很好。
一個吃小米長大的人,性情溫和,善良。
唉,幸虧有小米!
責任編輯:趙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