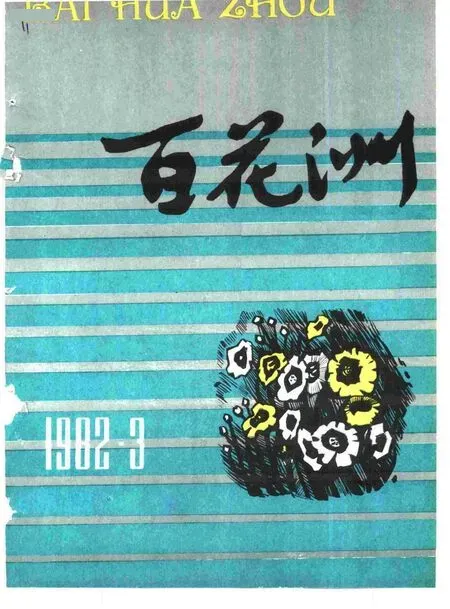山北一片好地方
曹多勇
1
水英販雞的想法是突然一下萌生出來的。
這天晌午頭,該睡午覺的水英躺在床上卻睡不著。在房屋外面的不遠處,有幾只公雞“喔、喔、喔”地一聲接著一聲地拼命叫起來。按說午時一過不是公雞打鳴的鐘點,幾只該殺的公雞就是違反常規、不合時宜地把一個寧靜的晌午攪得支離破碎,也把水英的午睡攪得支離破碎。每天清早三點半鐘,水英跟男人孫大路就得起床騎著一輛三輪車去十里外的一家大型農貿批發市場批發蔬菜,要趕早上七八點鐘準時在菜市場出攤子,上午賣半天菜,下午還得接著賣剩下的菜。這樣一天一天連軸轉,一個長長的晌午覺能缺少、能打斷嗎?水英心里帶著一股氣爬起床,手里摸著一根棍子就出門找幾只公雞的麻煩了。
“喔、喔、喔——”,幾只公雞不知道禍事臨頭,依舊比賽似地鳴叫著。
水英手里的棍子一揚一揚的,嘴里大聲地怒罵著,看我不打斷你們的雞腿,看我不砸爛你們的雞頭。
一群雞就閑散在房屋旁邊的一片空地里。小公雞、小母雞共有十幾只,都是今年新長起來的,論斤兩不足二斤,論毛色剛分公母。一只只小母雞新奇地看著身旁打鳴的小公雞,也想學小公雞打鳴,一張尖尖的雞嘴張開來,一副雞脖子七歪八扭地往半天空里伸,結果嗚叫出來的聲音有點不倫不類,不像是公雞打鳴的“喔、喔”聲,也不像是母雞下蛋的“咯、咯”聲。發生在雞身上的性別奧秘雞卻不明白。小母雞學不好小公雞打鳴,還左思右想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小公雞打鳴也是練習性的,嗓音稚嫩,底氣不足,往往高音處上不去,打一半就得停下來,雖一副勁頭十足的樣子但一下就衰落下來了。正好有一只公雞打鳴打一半上不去、下不來的時候,看見水英走過來。這是一只害羞的小公雞,它注意的不是水英臉上的怒氣,也不是水英手里提著的一根棍子,而是自己的雞面子。小公雞打鳴沒能打完整,見著水英不好意思了,一張雞臉“嚓啦”紅起來,比大紅色的雞冠還要紅。小公雞很快地離開空曠的場地,悶頭悶腦地往草堆后面躲。另一只小公雞冷不防地叼住一只小母雞的脖頸子,往小母雞身上亂撲騰。這只小母雞肯定是嚇壞了,“嘎——”地一聲驚叫,往前一躥,掙脫掉幾根雞毛,跑開了。小公雞摔倒在地上,呆愣半天爬起來。
——呸,你個淘氣的小家伙活該!
水英心里的一股氣“哧啦”一聲消散開來。要是把十幾只小公雞、小母雞看成一個個孩子的話,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一個大人跟一群孩子計較什么呢?
水英的一顆心平靜下來,安靜地站在一旁看著這群小公雞、小母雞。在水英遠遠的臉對面,同樣地有一對雞夫妻也在看著這群小公雞、小母雞。母雞長著一身褐色雞毛,圓圓滾滾,膘肥身胖的,好像一天能下兩三只雞蛋。公雞長著一身大紅色雞毛,高昂著雞頭,十分警覺地看著遠處的水英,像是太陽下一團永不熄滅的火苗。這對雞夫妻一動不動,相依相撫,恩愛無比。在水英的眼中,這群小公雞、小母雞是頑皮的,也是可愛的;這對雞夫妻是高傲的,也是幸福的。
水英就是提著棍子往回走的時候想到販雞去賣的。
水英想到販雞賣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想比現在販蔬菜賺錢多。眼下水英跟著男人整天在菜市場上販蔬菜,起早貪黑、受累熬人不說,主要是掙的錢顧不住一家四口人的花銷,顧不住兩個孩子上學,更過不上衣食無憂的好日子。水英是個急性子的女人,是個想做什么事立時三刻就要做什么事的女人。從門外走回頭,水英的一張臉通紅,頭腦一點困意沒有了,耳朵再聽見房屋外面的小公雞打鳴就一陣一陣莫名其妙地興奮,一副要做大事的樣子。說開來也就是心里不時地盤算著從哪一天開始販雞適合。水英身旁的孫大路倒是睡得很踏實,嘴丫流著一條閃亮的口水,還能把一聲一聲的鼾聲很均勻地打出來。水英坐起身搭手搖晃搖晃身旁的孫大路,想跟他嘮叨嘮叨心里話,想跟他商量商量販雞這件事。
水英一邊推一邊說,大龍大(爸),你醒醒。
水英跟前兩個孩子,大的是個男孩,名字叫大龍;小的是個女孩,名字叫小鳳。
孫大路鼻子里哼一聲,沒醒來。
水英一邊推一邊說,小鳳大,你醒醒,我跟你說一件事。
孫大路停斷鼾聲,眼睛斜拉開一條縫隙看一看水英,依舊沒有醒過來。
水英一邊推一邊說,大龍大、小鳳大,你醒醒,我跟你說一件事,我倆販雞賣怎么樣?
孫大路“嘩啦”閉上眼睛,鼻子唔噥著說一聲,吃雞好。
水英推男人的一雙手停下來,心里灌進一股涼氣,身子一點一點冷下來。水英心里憋屈得有點想哭,又有點哭不出眼淚的樣子。
孫大路答非所問不是他睡著沒醒透,他原本就不是一個明白人。
從外表上看孫大路是一個高高大大的男人,像是身上有一股使不盡的牛力。實際上他卻是一個殘廢了的男人,三年前的一場小煤礦透水事故,孫大路活著一條性命爬上井口,四肢好好的,一根汗毛沒丟失,卻嚇破了膽子,整天丟魂似的提不起精神。水英心想過個一年半載的,自己的男人吃一吃藥、打一打針興許能夠回緩過來。哪知自己的男人卻像一根朽木樁子,隨著光陰的流逝一天比一天更加枯朽下來了。也就是說,從三年前的那一刻起,孫大路就徒具一個肉身,缺少靈魂、缺少主見了。水英心里想著什么事情,只能自己跟自己商量,自己跟自己拿主見。
水英自己跟自己商量說,過些天就著手販雞?
水英自己回答自己說,過些天就著手販雞。
水英自己跟自己商量說,過些天真的販雞?
水英自己跟自己拿主見說,好!
“喔、喔、喔——”屋外傳過一陣長長的又宏又亮的雞鳴聲。顯然是那只大紅公雞叫出來的,真的像是一個大大的驚嘆號。“喔、喔、喔——”一只大公雞領唱著,“喔、喔、喔——”幾只小公雞合唱著。聽著大公雞、小公雞一唱一和的,水英心里豁然開來,亮堂開來。
就這么水英自己做主決定了販雞的事情。
2
這三年,水英在菜市場一前一后做過三種買賣。頭一年是賣蔬菜,第二年是賣大米,第三年還是賣蔬菜。要是真販雞的話,算是水英做的第四種買賣。
那一年,孫大路出事故,知道自己大事小事都不能做,就跟水英說,你離開我重新找一個男人吧。水英說,你這是說的哪家混帳話,我離開,你怎么辦?跟前的兩個孩子怎么辦?這個家怎么辦?孫大路說,你跟著我,不離開,我還不是一個殘廢的男人?這個家又怎么辦?跟前的兩個孩子又怎么辦?水英說,有我呢,這個家不用你操心,兩個孩子不用你操心,我自有我的辦法。水英嘴上說是有辦法,心里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家里的幾畝山地薄,種糧食只夠填飽肚子,家里的油鹽花銷沒有著落,兩個孩子上學沒有著落。水英想出的第一個辦法,就是劃出兩畝山地種蔬菜。水英跟男人說,你在家種菜,我騎腳踏車去山北城市里賣菜。水英家的北邊兩里地有一溜山,叫舜耕山。站在山頂往北看,一大片樓房連著一大片樓房,是這座城市的機關大樓,是這座城市居民的住宅小區,再遠處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流,叫淮河。往南看,一大片莊稼連著一大片莊稼,點綴其間的是雞窩似
的小村莊。水英就住在這其中的一個村莊里。水英這是頭一年、也是頭一次來山北菜市場賣蔬菜。自家山地里種白菜,水英就來賣白菜;自家山地里種蘿卜,水英就來賣蘿卜。山地薄,種糧食歉收,種蔬菜天旱地澇的也是收不多。一年蔬菜種下來,水英忙前忙后,起早貪黑,除去油鹽花銷錢,兩個孩子的學費錢還是沒著落。兩個孩子一齊上初中,哪個學期開學都得不少錢。水英想日子不能這么稀里糊涂地往下過,再說這么稀里糊涂地過日子也過不下去呀。
水英跟男人說,我倆從山南販大米去山北的菜市場賣?
男人點頭說一聲,照(行)。
水英說,我倆販大米就得在山北租房屋住下來,就得把家丟下來,兩個孩子自己照顧自己。
男人點頭依舊說一聲,照。
孫大路哪里還有主心骨,要是水英說販人去菜市場賣,他也會點頭同意的。
一溜山地往南就是一片平地,那里的人家種水稻。水英在菜市場附近租下一間房屋,雇一輛拖拉機去山南把一車大米拉過來,就算是生意開張了——這是水英想出的第二個辦法,也是水英做的第二種買賣。粗算一斤大米能賺幾分錢,如若一年能有十萬斤大米賣下來也能掙不少錢。水英做生意不貪財,買大米撿最好的大米買,賣大米按一般米的價格賣。一趕氣兩三個月生意做下來,手里的錢加上庫存的貨,一算賬真是比自家種蔬菜、賣蔬菜強不少。
春天過去是夏天,六月的梅雨天里,房屋靠著堆米的一面墻往里滲雨,一粗心大意,上千斤米受潮發霉。水英頭一次遇見這種倒霉事,陰沉著一張臉,一連兩頓沒吃飯。水英埋怨老天,埋怨老天不該一趕氣下這么多雨。水英埋怨房屋,埋怨房屋不該偷偷摸摸地往里邊滲雨。水英埋怨自己,埋怨自己不該這么粗心大意。水英唯獨不去埋怨孫大路,男人是一個自己顧不住自己的人,埋怨他有個什么用處呢?水英一頓飯不吃,孫大路跟著一頓飯不吃。水英兩頓飯不吃,孫大路也跟著兩頓飯不吃。
水英問,我不吃飯,你怎么也不吃飯呀?
男人說,你不吃飯,我怎么能吃飯呢?
生意停下來,早上的飯菜剩下來,晌午熱一熱又剩下來,眼見挨近一天的傍晚里,水英把事理想開了。做生意哪能只賺不賠呢?賺錢不笑賠錢不哭,這才是個生意人嘛。水英麻利地把剩飯剩菜重新熱一遍,盛一碗遞給男人,盛一碗留給自己。孫大路兩眼呆愣愣地看著水英,不相信老婆會吃飯。
水英說,我倆快點吃飯。
男人問,你真吃飯?
水英說,我倆吃過飯把發霉的大米當做飼料賣給養豬場。
男人相信了。
水英吃飯“稀里嘩啦”的,又香又趕口。孫大路吃飯更是“稀里嘩啦”的,像是三天沒吃飯。
這年下起頭一場小雪的時候,春節也就近了。孫大路經常犯冷熱病,犯冷病比熱病勤,冬天犯病比夏天犯病勤。這是孫大路的心病,一種醫治不好的毛病。熱夏天,孫大路的冷病說一聲犯起來也是兩只胳膊死死地抱著自己抖個不停。這幾天,孫大路一直說身上出冷,水英害怕他犯冷熱病。水英跟自己的男人說,下雪天你在家帶著兩個孩子,我去那邊要一要賬,回頭就過年了。兩個孩子在家上學,眼下已經放寒假。水英一路“喀嚓、喀嚓”踏著白雪把男人送回家,又一路“喀嚓、喀嚓”返回菜市場。
賒賬最多的是兩家小飯館,兩家小飯館也是水英賣大米的大戶人家。水英按月把大米送過去,飯館老板總是說錢不湊手,給一點,欠一點。一次累計一次,一年累計下來,哪家都欠上千塊錢。兩家飯館離菜市場不算太遠,水英去頭一家小飯館,見頭一家小飯館關著門。水英去第二家小飯館,見第二家小飯館關著門。水英的一只左眼皮“啪啦、啪啦”跳起來,一張嘴大張開倒吸一肚子涼氣。水英預感事情不好了。一打聽,兩家小飯館老板不聲不響地前兩天關門跑掉了。不止欠水英一家的大米錢,還欠房東的房租錢,還欠街道里的水電費。小飯館老板是南方蠻子,說是浙江人,具體是浙江哪個地方人誰也不知道。你說你去哪個地方找?反過頭來說,就是知道小飯館老板是具體哪個地方人,為這千把兩千塊錢的欠賬水英又怎么去找呀?水英回到租用的一間房屋里,直挺挺地躺床上,兩眼大睜著睡了一天一夜。雪天的夜晚是亮的,雪天的白天更亮,水英卻覺得雪天的夜是黑的,雪天的白天也是黑的。黑色的冷氣一陣陣席卷過來,緊緊地包裹著水英。水英白天黑夜看不見窗戶外面的一絲亮光,也看不見今后日子的一絲亮光。水英想到了死,想到了以死來解脫眼前的一團黑,來逃脫今后看不見光亮的日子。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難心的事情。水英在死亡的黑胡同里想了好長時間,也沒把一條死亡的路子想妥當。說到底,水英心里還是不舍得丟棄這個家、丟棄一個殘廢的男人、丟棄兩個沒有長大成人的孩子。已是五更天時分,門縫里傳來“喔喔喔”的雞叫聲。明明亮亮的雞叫聲,像是一只強有力的手指,撕開包裹水英眼前的黑暗,透出一道五彩的光亮。
水英想:要是我死去,這個家不就真的塌下來了嗎?
水英一骨碌爬起來,把臉洗一洗,把頭梳一梳,趕一趟早菜市,把該買的肉買了、該買的魚買了、該買的其他年貨買了,一齊裝進三輪車的車斗里,兩條腿使足力氣一個勁地往山南老家趕回去。
這個春節過后,水英就在菜市場販菜賣了。這是水英在菜市場上做的第三種買賣。
3
一聲雞叫,叫醒水英。水英在菜市場販一年蔬菜生意不錯。
一群雞叫,叫醒水英。水英覺得在菜市場販雞肯定比販蔬菜還要好。
這天下午三點多鐘,水英就準備好下午上菜市場的三輪車。孫大路也愣鼻愣眼地爬起床,望著門外忙碌著的水英,并沒覺察出睡覺前的水英與睡覺后的水英有什么不同。男人看不出水英心里有什么變樣,不代表水英心里就沒有變化。實際上從決定販雞的那一時刻起,水英在心里就一步一步地做著販雞的準備工作。水英跟自己的男人說,下午你去菜市場多看一會蔬菜攤子。孫大路驚訝地問,你留在家里干什么?孫大路很少單獨一個人看蔬菜攤子,水英也不敢讓他單獨一個人看蔬菜攤子。看跑一點蔬菜,看跑一點零錢,一天的辛苦就算白費了。可在買賣中,水英又不能缺少孫大路。缺少靈魂的男人也還是一個男人,缺少主見的男人也還是她的一個依靠。半夜三更天一路去蔬菜批發市場,有孫大路跟隨著,黑咕隆咚的路上水英心里就不害怕。大白天在菜市場跟各種人打交道,有孫大路站一旁,水英心里就不慌張。說到底,孫大路并不是一個傻透氣的男人,原本是一根直挺挺的木柱,經過一場事故,一下倒下來,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信心與勇氣罷了。
水英說,我不留在家里干什么。
孫大路還是問,那你干什么?
水英說,我什么也不干。
水英住著的地方離菜市場不遠。這是一處下午菜市場,午后四點鐘上人,天黑罷市。上午去別處的早菜市場賣剩下來的蔬菜或早上有意留下來的蔬菜一起拉下午菜市場上賣掉。水英租房屋選擇在下午菜市場附近,一是圖早早晚晚上菜市場方便,二是圖早早晚晚回山南看
孩子方便。家在山南二里地,菜市場在山北二里地,沒有一條直來直去的路,繞一條彎路回家少說要走十幾里路遠。在水英的生活里,缺少不掉男人,更是缺少不掉兩個孩子。大龍十六歲上初三,小鳳十四歲上初一,一所初中學校就在村子不遠的鎮子里。水英時常不回家,兄妹二人留在家里,自己照顧自己。早早晚晚的水英抽空回一趟家看一看。除去種莊稼、除去收莊稼,幾畝地里的農活都是靠著兄妹二人上學放學插空起早貪黑地做。要是趕上禮拜六、禮拜天不上課,莊稼地里又沒什么要緊的農活,兄妹倆就會一齊跑過來,幫著水英賣賣菜,團聚成一家人。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兩個孩子賣蔬菜,稱秤、算賬、收錢,比水英還麻利。這種時候,水英就能騰出手,收拾收拾家,洗一洗臟衣服,燒一頓像樣的飯菜,一家四口人坐一塊好好地吃一頓。這種時候也是水英最滿足最幸福的時候。水英暫時忘記了男人的不幸,忘記了家庭的苦難,忘記了自己的艱辛,看著眼前的一雙兒女,覺得日子會一天比一天過得好。水英正是抱著“日子會一天比一天過得好”的想法才決定販雞的。一年來販菜的收入也不錯。可這不錯也只是“日掙日銷”的不錯,手里見天掙著錢,見天卻余不著錢,要是遇見一件什么需要花錢的事,日子還是磕磕絆絆過不下去。一句話,水英就是想販雞能比現在販菜掙錢多,就是想往后的日子能比眼下的日子過得好。
水英把青菜攤子交給孫大路看管,整個下午哪里也不去,就站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上看著人來人往的菜市場。
水英這是在觀察菜市場,觀察菜市場上幾家賣雞的。
菜市場的地盤屬于當地一個村子,其經營權理所當然地也屬于這個村子。負責管理、負責收費的都是這個村子里的村干部。在下午菜市場上做買賣的,少部分是自己種菜自己賣菜的本地村民,大部分是外地人。這大部分人中的大部分人是皖北淮陽的。前十幾年這地方屬于行署專區、沒有改劃市的時候,其面積占安徽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安徽的一半,貧困人口怕是要占安徽的七八成之多。這么一處窮山惡水之地,近些年連連出過不少震驚全國的事件。比如說,出過一個腐敗副省長,在山東濟南被判處死刑;比如說,還出過一樁假牛奶事件,致死好多名嬰兒。這座城市距離淮陽地區最近,大量地擁進這個地方的人,也就一點不用奇怪了。不熟悉這個菜市場的當地人偶爾上一趟菜市場,聽見菜販子操著同一種異地腔調,隔著攤位“俺大叔、俺大舅,俺大姨、俺大媽”地相互叫喊著,會愣愣怔怔地好大一會,有一種身處異地他鄉的荒誕感。初來乍到的水英來這個菜市場上做買賣,有好長一段時間不習慣,好像淮陽人是當地人,她反倒是個外鄉人。上午這個菜市場上買賣很少,或沒有買賣。下午四點以后,陸陸續續地買賣就興隆起來了。買菜的有附近住宅小區里的居民,也有附近市委、市政府機關里的工作人員。他們上午忙著手上的各種工作,抽不開身子,傍晚趕一趟菜市,正好順路下班回家去。也可以這么說,就是因為市委、市政府機關里的工作人員上午沒時間去菜市場買菜,這個下午菜市場才應運而生的。
從上述對這個菜市場的簡單描述里,也許能窺探出這座城市的特殊布局來。這是一座煤城,是依著煤井的先后順序一片一片發展起來的。分不出哪里是城區、哪里是郊區,也可以說到處都是城區、到處都是郊區。就是在這座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帶——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距離這個農村的下午菜市場也只不過十分鐘的路程。城鄉一體化似乎成了這座沒有什么特點的城市的一大特點。不過這樣的一種城市格局也自有它的益處,那些從四周涌進這座城市中心地帶的農村人,很容易從附近農村租到廉價的住房。水英,還有菜市場上的其他菜販子就夜伏晝出,生活在下午菜市場附近的這個村子里。
菜市場原本就有三家賣雞的攤子,另外還有一戶專門殺雞的攤子。三家賣雞的是淮陽人,一戶殺雞的也是淮陽人。水英仔細留意這三戶賣雞的人家,其中一戶人家賣的是品種雞。品種雞便宜,價錢與草雞相差一多半,吃嘴里的滋味也與草雞不一樣,相差一多半。顧客圖便宜,就買品種雞,也就沒必要跟草雞做比較了。其他兩戶人家賣草雞,他們是淮陽人,賣的也是淮陽的草雞。淮陽人分散在這座城市的各個菜市場,包攬著大部分賣雞生意。他們自成體系,分工合作,買雞的專門買雞,運雞的專門運雞,賣雞的專門賣雞。買雞的是供貨商,運雞的是運營商,賣雞的是經銷商。淮陽農村地方大,那里的草雞相對于本地的草雞便宜得多,供貨商在那邊把一只只草雞購買好,運營商開著大貨車把上千只、上萬只草雞拉過來,分散給各個菜市場里的經銷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淮陽路途遙遠,買回頭的草雞,少說隔一天才能賣出去。經過這么三折騰兩折騰的,一只只草雞就缺少精神氣,像是一只只瘟雞。相比較,水英要是買本地草雞、賣本地草雞的話,當天買當天賣,一只只草雞毛色鮮艷,精氣神十足,一看就是貨真價實的當地草雞。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有了這么一句俗話做保證,水英做販雞生意就有了六七成把握。
另外的三四成把握就要說到菜市場上買雞的人了。水英三年生意做下來,大致把上這個菜市場買菜的分做三類人。第一類人是家住菜市場附近、擁進這座城市的農村人,他們少數人就在菜市場上做買賣,大多數人分散在這座城市的各處,做著各種營生。這類人買菜是撿剩菜買,揀便宜菜買,吃雞也多吃相對便宜的品種雞。水英賣草雞不能指望這類人。第二類人是家住菜市場附近的城市人。這類人雜,貧富不均,一部分人買剩菜,一部分人買新鮮菜,可以想見的是一部分人吃雞買品種雞,一部分人吃雞買草雞。水英最看重的是市委、市政府機關里的工作人員。這類人口袋里的錢不一定最多,上菜市場買菜卻喜歡揀最好的買,最貴的買,上午剩下的菜別指望賣給他們。水英每天去蔬菜批發市場批發回頭的蔬菜,要是有一百斤蔬菜的話,拉七十斤去上午菜市場賣,余下三十斤去下午菜市場賣。上午的菜市場大,賣菜、買菜的人多。下午的菜市場小,賣菜、買菜的人少。一般情況下,上午能剩十來斤蔬菜,下午一塊拉上菜市場。上午的剩菜下午賣不賺錢,賺錢的是留下來的新鮮菜。晚上一算賬,往往是下午比上午掙錢多。要是一天掙三十塊錢的話,上午掙十塊,下午掙二十塊。說起這里邊的原因就在這些市委、市政府機關里的工作人員身上。
水英賣草雞就指望這類人。
水英把事情想明白、想清楚,回到菜攤子上收攏菜攤子,不賣菜了。
孫大路問,怎么不賣菜了?
水英說,我倆回山南家。
孫大路問,不種莊稼、不收莊稼,回山南干什么?
水英說,回家看孩子。
孫大路開始覺得水英有點不對勁,遲遲疑疑地問,剩這么多菜怎么辦?
水英說,留自家吃。
菜市場上這么多人,水英還是不便把賣雞的想法說出來。
4
中間相隔一天,水英真就騎著三輪車把兩籠子鮮活亂蹦的草雞從山南拉過來。一路上公
雞、母雞擁擠一團,“嘎、嘎、嘎”歡快地喊叫著,水英心里卻虛飄飄的沒有一點根底。
最初水英想把賣雞的攤子與淮陽人的三個賣雞的攤子一起擺放在菜市場的頂東邊。菜市場東西走向,劃分著各種買賣區域:蔬菜區,水果區,肉類區,禽蛋區等等。賣雞的區域就規劃在菜市場頂東邊。水英推著三輪車走進菜市場,心里更虛了,猶猶豫豫的,覺得把雞籠子擺放在哪里都是不合適,都是爭搶別人的生意。果真,水英把攤子靠北擺,北邊的一家有意見;水英把攤子靠南擺,南邊的一家有意見;水英把攤子靠中間,中間的一家有意見。水英心里發虛,孫大路心里不虛。孫大路回家知道水英要販雞賣,一副高漲起來的熱情比水英還要高。水英去鎮上焊雞籠子,孫大路跑在水英的前面;水英去集上買草雞,孫大路跑在水英的前面。
孫大路上前質問淮陽人說,你們三家能在菜市場上賣雞,我們家怎么就不能在菜市場賣雞?
三家人一齊回答說,我們沒說不讓你們家在菜市場賣雞,我們只說你們家不能跟我們三家擺在一齊賣雞。
孫大路說,你們淮陽人怎么這么不講理?
三家人一齊說,你去問問菜市場上的其他人,是我們淮陽人不講理,還是你們兩口子爭搶我們的生意不講理。
孫大路兩眼通紅,像一只斗架的公雞。水英拉回孫大路,知道看起來是一樁小事情,也不是吵架所能解決的。在這個菜市場上淮陽人是一霸,仗著自己人多勢眾,一點也不會把水英兩口子放在眼里。
水英好言好語地問三家人,像是征求意見似的問,你們說我家賣雞的攤子不擺在菜市場東邊,應該擺在哪里?
三家人還是一齊回答說,你就擺在菜市場西頭的一片空地里。
水英站在菜市場東頭,抬眼看著一條長長的菜市場,長長的菜市場西頭是一片空地。幾只丟棄的塑料袋被一股旋風鼓動起來,飄浮在半空中。
水英不與三戶賣雞的淮陽人論理,去找菜市場的管理人員。負責管理菜市場的村干部不在菜市場,整天坐在村委會。水英去找村干部論理,問他們三戶淮陽賣雞的人家憑什么讓我把賣雞的攤子擺在菜市場西頭。村干部說,你不愿意擺西頭,就去別處的菜市場。水英說村干部,你不主持公道,還幫著外鄉人說話。村干部說,人家賣雞賣得好好的,你半路插進來,人家能高興嗎?水英說,聽你說話的口氣,我是不該在這個菜市場上賣雞了?村干部說,賣不賣雞是你自己的事情。水英說,我偏要呆在這個菜市場。
水英推著三輪車從菜市場的東邊慢慢地往西邊走。孫大路耷拉著腦袋跟后面,像一只剛剛斗敗的公雞。
孫大路問,真在菜市場西邊賣雞?
水英說,菜市場西頭空朗,做生意心里敞亮。
哪知道水英頭一只草雞賣出去,又遇見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菜市場東邊三戶淮陽人家賣雞,一戶淮陽人家殺雞,賣雞的、殺雞的各做各的生意。顧客在菜市場東邊的任何一戶淮陽人家買雞,只要再花一塊錢就能把一只活雞宰殺出來。顧客去菜市場西邊的水英攤子上買草雞,拎到菜市場東邊宰殺,殺雞的人家不給殺。殺雞的人家有理由,說我們幾戶人家是一家人,我們家賣雞當然我們家殺,你手里的雞是從誰手里買的去找誰殺。現今城市還有誰家自己殺雞,買一只活雞提回家怎么吃進嘴?顧客一轉臉去菜市場西邊,把手里拎著的一只活雞交還給水英。水英心里明白,這是幾戶淮陽人家聯合起來拿捏自己。水英收起賣出去的草雞,也收起賣雞的攤子。
孫大路問,我們不賣雞啦?
水英說,怎么會不賣雞呢?
孫大路不知道水英把賣雞的攤子收起來還怎么去賣雞。
進出菜市場只有一條東西向的路。水英推著三輪車從菜市場的西邊快速地往東邊走。賣雞的、殺雞的淮陽人斜眼看著水英,掛滿一臉得意的笑容。水英把一張臉昂起來,不看路,不看人,只看天,只看天空一片飄動變幻的白云。
隔一天,水英推著三輪車又走進菜市場。這一趟水英的三輪車上沒有雞籠子,車里放著一只煺雞毛的機器,一只生火、燒水、燙雞的火爐子,還有一張破舊的木桌子,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物件。水英一副興沖沖的樣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孫大路跟著水英一齊走過來,腦袋耷拉著,還是一副斗敗公雞的樣子。
孫大路說,我害怕。
水英問,你害怕什么?
孫大路說,我害怕淮陽人找茬子。
水英說,他們能吃人?
水英推著三輪車從東邊走進菜市場,幾個賣雞的、殺雞的淮陽人眼睛干直干直的,臉上一點笑色沒有了。水英把這些東西擺放妥當,第二趟把一籠子山南草雞推過來。山南草雞跟淮陽草雞就是不一樣,關進籠子里,還有一片不甘任人宰殺的鳴叫聲。
5
水英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就喜歡爬家門前的舜耕山,看一看山北的一條明亮亮的淮河,看一看山北的好多座高高矮矮的樓房。那時候,水英在心里暗暗地想,趕明長大嫁往山北的人家去。不圖別的,就圖山北的人家多,過日子熱鬧。山南邊一個小村子連著一個小村子,也有不少戶人家,只是一家一家的房屋窩在山溝里,怎么看著都是一副受委屈的樣子。水英長成一個大姑娘,頭一戶婆家說的就是孫大路。孫大路家的村子與水英家的村子緊挨著,一并排窩在山南里,水英心里先一沉,想著搖頭不同意。緊接著水英知道孫大路在山北的一家小煤礦上班,心里又一喜,點頭同意處處看。半年后,水英快要結婚時,說出心里話。
水英說,我倆成過家,我想跟著你一起去山北過日子。
孫大路說,好呀,省得我上下班來來回回地跑冤枉路。
小煤礦是當地一個鄉政府開的,離一個村子很近。孫大路在這個村子里花錢租下一間房屋,就把水英從山南的老家接過來一起住,一起過日子。山南的幾畝薄地丟給別人經管,丟給別人去種。不年不節的,不需要回娘家,水英連一趟山南都不回。相對來說,小煤礦的工資高一點。孫大路按月把工資開出來,回家交在水英的手心里,倆口子按月把日子過下來,還能余下一點錢。
孫大路說,攢夠錢回家蓋房屋。
山南是父母留下來的三間老房子、矮房子。
水英說,蓋房屋也要在山北找地方蓋,回山南蓋房屋做什么?
孫大路敷衍著說,好好好,我們攢足錢,在山北找地方蓋一座大樓,蓋一座皇宮,你就是住在皇宮里的娘娘了。
水英一臉幸福地笑著,小姑娘時做過的一個夢依舊延續著。
結婚一年半,水英生下兒子大龍;中間相隔一年半,水英又生下閨女小鳳。一家四口人再住在一間房屋里就不寬敞了。孫大路上白班要睡足覺,上夜班更要睡足覺。兩個孩子吵吵鬧鬧的沒個鐘點,只得多租一間房屋專門留給孫大路睡覺。多租一間房屋,多付一份租金,多出兩個孩子,花錢更是如流水一般。按月開錢,按月花光,還不夠,節余下來的蓋房錢一點一點往外抽。
孫大路說,這樣過日子不能算個事。
水英說,掙錢多、掙錢少是你男人的事,我的事就是帶好大龍、小鳳這兩個孩子。
水英這么說話是心里失去主張也沒辦法。
孫大路的辦法就是更換一個工資更高的
小煤礦。新換的小煤礦與原來的小煤礦挨一塊,東西相距不足兩百米,從地表上看不出兩個小煤礦的區別,當然也就看不出工資一高一低的原因。分別從兩個小煤礦的礦井走下去,東邊的小煤礦往東邊扒煤炭,西邊的小煤礦往西邊扒煤炭,西邊的地面是一片莊稼地,東邊的地面是一口大水塘。小煤礦扒的煤炭都是國家大煤礦掏剩下來的余煤。這口大水塘也是國家大煤礦掏出來的塌陷塘。一幫人整天整月整年在這么一口塌陷塘下面扒煤炭,還不是在一只睡熟的老虎屁股上撓癢癢。要是有一天塌陷塘的水漏下去,一只睡熟的老虎醒過來,肯定是一場滅頂的災難。孫大路知道這種情況還要去,是圖一個月能多出三百多塊錢。孫大路沒敢跟水英說實情,水英還埋怨孫大路說,你怎么不早去東邊的小煤礦呢?
,孫大路說,人家東邊的小煤礦一直不缺少人手。
孫大路說過這句話,心里一沉一沉的,頭頂上無形地多懸著一把致命的利劍。
大龍七歲該上小學了,水英犯難為。小煤礦附近的村子里有小學,大龍能進這所小學校上學,只是一學期要多繳幾百塊錢。一個孩子一年多出幾百塊錢,過年把小鳳上學,兩個孩子加一塊就多出一筆不少的錢。實際上,孫大路下小煤礦掙一份工資,除去顧著一家四口人的吃喝拉撒,確實沒錢顧著兩個孩子在山北上學。水英心里不想離開山北回山南,嘴上說不出理由。
水英猶猶豫豫地問,怎么辦?
孫大路果斷地說,回山南。
眼見秋季天新學年開學,水英只好帶著兩個孩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山南。這時候,水英不去怪怨天,不去怪怨地,卻怪怨起自己來。怪怨自己當初嫁人就不應該嫁孫大路,就應該嫁一戶真正的山北人家。
水英自己問自己,我干嘛要嫁給孫大路?
水英自己回答自己說,這是命攤的。
水英回山南家里,與孫大路聚得少,分得多。一溜舜耕山遮擋在眼前,水英看不見山北的一片地方,也看不透山北的一片地方。整天水英面向山北一聲長長的嘆息連著一聲短短的嘆息,一聲短短的嘆息又連著一聲長長的嘆息。漸漸地,水英把長長短短的嘆息都憋在肚子里,認命了。水英認命的同時又把希望寄托在兩個孩子長大后的日子里。水英想,候兩個孩子長大,該能離開山南回山北,跟著孫大路一起過日子了吧。
老天爺沒容水英沿著這條路線把日子一天一天按部就班地過下去,
這一天,趕上孫大路井下當班,大水塘裂開一道大口子,小煤窯下面猛然涌進一個大浪頭,把一部分人往回沖多遠,卻把更多的人吞進肚子里。頃刻間,孫大路等少數幾個人揀著一條性命活過來,其余的幾十條人命沒有了。事故驚動黨中央、國務院,電視臺一連跟蹤報道好幾天。孫大路在醫院里前后住半個月,冷熱的毛病忽然一下嚴重了,只是還是冷的多、熱的少。醫生說,這是心病,只能靠心理醫治,要說好也就好了,要說不好一點辦法也沒有。醫生還說,這種病怕冷不要緊,要緊的是怕熱,一怕熱,犯病一久就……醫生把話止住。水英卻明白醫生沒說出來的是什么話。
事故處理的結果是,死人賠四萬——傷亡撫恤金,活人賠兩萬——精神補助費。孫大路帶著一條活命,帶著兩萬塊錢回山南。村人都說孫大路揀著一個大便宜。水英卻知道自己的男人已經成為一個廢掉的男人。孫大路原本是這個家的一根頂梁柱,現在他一塌下來,這個家也就相跟著眼看著塌下來。水英不想這個家跟著男人一起塌下來,只能硬著頭皮頂上去。三年來,水英一直不斷地想著各種辦法苦苦地支撐著這個家,同時也是在苦苦地支撐著自己的一個夢想,一個把日子往好里過的夢想。如果說水英小時候向往著山北,是圖山北的樓房高,人家多,熱鬧。現在水英向往著山北,是圖山北的菜市場能做買賣能掙錢能把日子往好里過。
水英始終堅信著自己的看法:山北就是一片好地方。
6
現在在整個菜市場上最招惹人眼的就是水英販雞的攤子。
水英的攤子孤孤零零地擺在菜市場的最西頭,還撐著一把很大的遮陽傘。一把黃色的遮陽傘下面是一輛三輪車,車上架著雞籠子,籠子里裝著一只只鮮活亂蹦的山南草雞。此外,旁邊是一只鐵皮爐子,爐子上坐著一只鐵皮桶,鐵皮桶里燒著燙雞的熱水。挨著爐子是一只煺雞毛的機器,挨著煺雞毛機器是一張破舊的桌子——這些就是水英做買賣的全部家當。要是沒有顧客,水英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坐在攤子前面等候著,呈現出來的是一副懶散的樣子,是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是一副不堪生活重負的樣子。一旦有顧客走過來,水英就像換上另外一個人,一下子精神起來,一下子興奮起來,一下子言語多起來。水英與顧客講價錢,水英幫顧客挑選雞,水英稱秤、算賬、收錢。要是把一樁生意分出前后兩部分的話,水英面對顧客做著上面這些事情,只是生意的前面一部分。是從容的,是誠心的,是謙讓的。接下來進行生意的后面一部分,殺雞、燙雞、煺雞、剖雞。水英做這些事情已經很熟練了,有一種忘我的熟練,有一種下意識的熟練。水英殺雞是免費的,不另外收錢。前后只需兩、三分鐘的工夫,一只草雞就收拾好,裝進塑料袋子遞在顧客手上。
賣出一只雞,粗算一下,毛錢能賺三塊錢。要是一天能賣出十只雞的話,就趕上原先販菜的收入;要是一天能賣出十五只、二十只雞的話就比原先販菜強。一段日子做下來,每天平均賣二十幾只雞是正常的。這樣一天凈賺五六十塊錢是穩當的。
水英樂滋滋地問男人,你說我們還要去做什么?去偷人家、去搶人家?
孫大路說,去偷人家、去搶人家還犯法呢,還不定能偷、能搶這么多呢。
水英說,我看還是販雞的生意好。
孫大路說,我看販雞的生意真不錯。
菜市場上很少見著孫大路。孫大路高高大大的,站著像是一座鐵塔,愣鼻愣眼的卻又像一個十足的傻瓜。孫大路呆在賣雞的攤子旁邊,顧客見著他心里有點發怵,有點害怕,有意無意地影響做生意。賣雞與賣菜有些不同,一是攤子的地方不同,賣菜與其他菜販子擁擁擠擠地在一起,孫大路站一旁顯得不是怎么礙眼,賣雞的攤子孤孤零零的,顧客沒到賣雞的地方,眼睛早看見站在一旁的孫大路。二是賣菜人多人雜,沒有孫大路做幫手,水英的兩只手確實忙不過來。賣雞相對清閑一點,顧客少一點,水英一個人忙一忙也就忙過去了。
水英很少讓男人過來幫忙,她跟孫大路說,沒事你就在家睡覺。
水英說的家就是菜市場附近租住的這間房屋。
孫大路說,我在家睡不著覺。
水英說,你睡不著也要睡。
水英不能把實情跟孫大路說,免得傷害孫大路。
這樣孫大路每天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陪著水英一起從山南把草雞運過來。
水英開頭做販雞生意不貪價錢,也不貪斤兩,看重的是把一條做生意的路子趟出來。
去山南集市上收購草雞,肯定要比淮陽賣雞的貴那么塊把錢一斤,水英賣雞的價格卻與淮陽的草雞一樣價格。在賣雞的斤兩上也是很有講究的。水英上午從山南集市上買回草雞,一直到下午進菜市場,一點雞飼料不喂。一只
只草雞相當于空著嗉子賣出去。相反地,淮陽賣草雞的臨進菜市場,都把一只只雞嗉子撐多大。他們喂雞,不是讓雞自己往嘴里吃,也不是喂正經八百的雞飼料。攪拌一盆稀飯狀的碎米糠,或干脆拌石膏粉。碎米糠斤兩重,石膏粉斤兩更重。攪拌好“雞飼料”,逮住一只只雞硬是扒開雞嘴,一團一團“雞飼料”往嗉子里塞,直到把一只只雞嗉子撐個圓圓鼓鼓的、實在塞不進去才罷手。這樣一只雞少說也多出三兩雞嗉子。要是一失手,撐破雞嗉子,雞一會半會的死不掉,倒是顧客把雞買回家,任你怎么洗也不能把一只雞洗干凈。雞的脖子里,雞的肚子里,甚至雞肉的夾縫里,到處都是“雞飼料”,像是雞身上長出來的不是雞肉、雞骨頭,只是長“雞飼料”。
水英不貪價錢,不在雞的斤兩上做手腳,就在嘴上巧妙地把這些優勢宣傳出去。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有時候,好酒落在深巷里,酒家也是需要吆喝吆喝的。水英對人熱情、嘴甜,見著一般大小的男顧客連聲喊“大兄弟”,見著年歲相仿的女顧客連聲喊“大妹子”。
水英說,大兄弟、大妹子,你們過來看一看,我這可是正宗的山南草雞,我賣價十塊錢一斤,給你們一個優惠的價格,打九折。
淮陽人賣雞是九塊錢一斤,水英這么一吆喝一叫賣,表面上比淮陽人貴一塊錢一斤,實際賣出的價錢是一樣的。
水英說,大兄弟、大妹子,你們伸手捏一捏雞嗉子,看一看是不是空嗉子,要是我喂飽它們,一只雞能多出二兩秤,要是我黑心往雞嗉子里塞碎米糠、塞石膏粉,不是更壓斤兩嗎?
水英嘴上拿自己賣雞說事理,實際上卻把矛頭指向淮陽賣雞的人,說他們坑害人,爛良心。
水英這么吆喝一番,叫賣一番,眼睛望著顧客,心里話是買淮陽人的草雞,還是買我的草雞,你們自己去掂量吧。就是長著一副豬腦子的顧客,這么聽水英一吆喝一介紹一宣傳,也知道是買淮陽人的草雞劃算,還是買水英的草雞劃算呀。
要是顧客真不買雞,水英也不生氣,說大兄弟、大妹子,你們去菜市場上轉一圈,看一看,要是遇見我家這樣的草雞,你們拎過來,我出十五塊錢一斤買下來。
水英賣的雞確實是貨真價實的山南草雞,菜市場上也確實找不出其他賣山南草雞的人家。
眼見農歷八月十五中秋節快到了。水英想抓住這個節日多販一點雞,多賺一點錢。
中秋節是人類團圓的日子,喜慶的日子,卻是雞類死亡的日子,哀鳴的日子。按照風俗習慣,淮河兩岸的人家過中秋節,家家少不掉這么兩樣吃物,一樣是吃烙饃,一樣是吃紅燒雞。烙饃簡單,和一團發面,稱半斤芝麻,芝麻放鍋里炒熟,在缽子里搗碎,做烙饃的餡子。搗碎的芝麻里拌上鹽,烙出來的饃是咸饃;搗碎的芝麻里拌上糖,烙出來的饃是甜饃。中秋節這一天逮一只公雞,宰殺、煺毛、開膛、剖肚洗出來剁成肉塊,蔥姜油鹽、花椒大料一齊放鍋里紅燒出來。家里有著這么兩種吃物,一個中秋節就區別開其他的節日,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文化意味來。
無疑中秋節前的好多天里,雞類也成了人類禮尚往來的重要角色。各種各樣的禮尚往來中,數毛腳女婿去老丈人家最少不掉要送雞。臨近中秋節,毛腳女婿要準備一箱酒,要準備四盒月餅,紅毛紅冠的大紅公雞少說要送六只,也有送八只,十二只的。單是這一樣,整個中秋節需要多少只雞?
水英及時調整買雞、賣雞的辦法。賣雞原本是賣下午半天,現在是上午、下午都出攤子。在山南集市上購買雞原本是水英的事,現在水英交給孫大路不放心,托付給兒子大龍辦。大龍成績不算好,初中畢業閑在家里沒有上高中。大龍跟著水英上集市上購買過幾回雞,一條一綹的像個小大人。許多賣雞人想占他的便宜,結果吃虧的反倒是自己。水英笑著說兒子,看來你天生是個做生意的材料。
兒子負責買雞,男人負責運雞,水英負責賣雞,一個比一個忙碌。一家人整天都是雞、雞、雞,錢、錢、錢。八月十五前面的十來天里,一天比一天賣雞多,也就一天比一天掙錢多。先是一天賣四十只、五十只,后來一天賣七十只、八十只,最多的時候一天賣上百只。這些天,水英讓兒子在山南集市上挑選最好的大紅公雞收購,一只只大紅色公雞來到菜市場賣出的也是最好的價格。水英把雞的價格賣得比淮陽人家的貴,卻還比他們賣的多。送禮講究的是一個臉面,誰人在乎價格的貴賤。這么一番景況,淮陽幾戶賣雞的人家看進眼里,害起紅眼病。他們的一只只眼睛里充滿血、燃起火。
水英心里想著淮陽人遲早會找她的麻煩,卻沒想著孫大路支撐不住倒了下來。
7
孫大路這回犯病,不是怕冷,是怕熱。涼爽的秋天里,熱出一頭一身汗,一張嘴還一張一張的像是喘不過來氣。那樣子像是心里燃起一堆火,烘烤著身體,烘烤著生命。一副犯病的樣子是過去沒有的。水英停止做生意,騎上三輪車,帶著男人,帶著剩下的雞,一并回山南。水英沒有把男人送進醫院里,知道男人的病醫院里治不好,知道男人的大限已經不遠了。
水英問,我們回家吧?
孫大路答應說,我們回家。
水英兩只腳吃勁地蹬著三輪車,前面的一條路一點一點迎過來,水英望不見路的最頂端;孫大路坐在三輪車上臉朝后,眼前的一條路一點一點遠過去,孫大路也望不見路的最末端。
水英嫁給孫大路的時候,就知道他身上有忽冷忽熱的毛病,只不過那時候輕微,沒覺得是個大毛病,更沒覺得會喪害性命。夏天里,孫大路熱起來會比別人熱,熱得受不了,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淌。孫大路說,我熱得難受,我不住地淌汗,我怎么會這么熱呢?水英說,夏天不熱,還能冬天熱,夏天不淌汗,還能冬天淌汗?水英這么說話是根本沒把男人的熱當做一種病。夏天里,要是孫大路犯冷病,就一個勁地發抖,蓋一床棉被冷,蓋兩床棉被冷,蓋三床棉被還是一個冷。孫大路的冷是骨子眼里冷,能感覺著一陣一陣的冷風從心里冒出來。夏天里,孫大路熱,水英能說正常,孫大路冷,水英不能大睜兩眼說正常了吧?水英把孫大路的冷當做打皮汗(瘧疾)治療好多回。
水英帶著孫大路去小煤礦附近的小醫院,不做檢查,不找瘧原蟲,拿幾粒管皮汗的藥片回家吃。
水英還用土辦法治療孫大路的皮汗病。逮一只癩猴子(蟾蜍)剖開肚子,扒除腸子,敷在左手的手脖子上,癩猴子外面放兩片破開的秫秫梃子,秫秫梃子外面捆綁上大紅色的頭繩子,還要一個勁地坐在太陽下面暴曬。淮河岸邊的村人認為打皮汗是皮汗鬼作的怪,癩猴子縛手上,太陽地里一照曬,皮汗鬼跑掉了,就不敢附身上。
反過頭來說,孫大路要是在冬天里犯冷熱病,犯冷病容易馬虎過去,一犯熱病,動靜就會大起來。滴水成冰的大冷天,孫大路能扇電風扇。憑著水英的經驗,找不出孫大路犯的是什么毛病。水英帶著男人去一家大醫院。大醫院里的醫生說孫大路這是神經功能紊亂癥。這話水英聽不懂。醫生說,孫大路這個人一年四季跟別人過得不一樣,別人過冬天,他過夏天,別人過夏天,他過冬天。水英問,那怎么夏天他熱起來比別人熱,冬天冷起來比別人冷呢?醫生
說話又繞回頭,所以說他這是神經功能紊亂癥。
其實,孫大路的病因,他自己知道。
小煤礦發生透水事故,孫大路揀著一條命,在醫院前后住半個月回家里。這是一家更大的醫院,花錢是花小煤礦上的錢,水英就提出來要把孫大路忽冷忽熱的毛病好好地仔細地查一查。
孫大路說,不用查了,我的毛病是怎樣得上身的,我自己知道。
水英把一雙眼睛睜大了,睜圓了,使足勁地“啊”一聲。
孫大路說,我這是害怕下井落下的。
開初下小煤礦,孫大路在井上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在井下走不動路、干不動活。一天一天的,孫大路覺得自己是一趟一趟進出鬼門關。水英說,你這么害怕下小煤礦還干嘛下小煤礦?孫大路說,我人沒本事,又死死板板的,不下小煤礦能干什么?孫大路也離開過小煤礦做其他事情,做來做去做不下去,掙不著錢,還是回到小煤礦。漸漸地,孫大路心里的害怕似乎好一點,卻染上忽冷忽熱的毛病。一年一年的,孫大路也是稀里糊涂地犯著病。直到這場透水事故過后,孫大路才說出忽冷忽熱毛病的原因。水英說,你現在不用下小煤礦,也就不用害怕了。哪知道,孫大路不用下小煤礦,忽冷忽熱的毛病沒有好,反倒愈來愈嚴重。
水英說,你現在還害怕什么呢?
孫大路說,我也說不清楚。
孫大路死前的幾天里反復做著同樣一個夢,那就是在一個黑洞里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無窮無盡的怎么也見不出一個光亮的盡頭。孫大路一驚醒過來,能出一大身汗。
孫大路說,我怎么覺得好像一直在塌陷塘下面的那座小煤礦里呢?
水英說,小煤礦出事故早關閉掉,不要說是你,就是別人也是一個人下不去。
一場透水事故發生后,連著塌陷塘附近的幾座小煤礦都停下來。
孫大路不相信地說,你明天帶我去塌陷塘看一看。
水英說,帶你去看看就帶你去看看。
水英還是前面蹬著三輪車,孫大路還是后面坐著三輪車,兩人一起走出村子,翻過舜耕山,又一次走進這座山北煤城,一點一點接近塌陷塘。塌陷塘連著上百畝、上千畝的塌陷區。塌陷區是附近的一座大型煤礦建國后扒煤遺留下來的,幾十年間長滿各種雜樹,是一片斷絕人跡荒無人煙的地方。只是到了近些年,開起一座座小煤礦,才有了一點人的氣息。水英跟著孫大路在這里住了好幾年,一直呆在租房屋的村子里,沒來過塌陷區,沒見過小煤礦。水英今天拉著孫大路,頭一次進塌陷區,頭一次見著塌陷塘,頭一次見著小煤礦。——選擇一片地方,蓋出幾間房屋,往地下掏出一個洞,就是一座小煤礦;招幾十個人走下去,把煤炭扒出來,賣掉就是錢。人們“錢、錢、錢”地喊叫著,這片沉寂的塌陷區不再沉寂了,熱鬧起來了。整個塌陷區被小煤礦一塊一塊分割開,一片一片占據著。水英拉著孫大路走進塌陷區,一條煤矸石路坑坑洼洼的不平整,路上走滿一輛接著一輛的拉煤車,灰頭灰臉的,疲憊不堪的,一陣風吹過來,彌漫起的灰塵卷揚向半天空。
孫大路手指指著前面說,那就是塌陷塘。
水英一抬眼果真見著一口大水塘。水塘水青幽幽,里邊沉積著堿性的煤矸石,水塘邊少生雜草,水塘里更是不長魚蝦。更主要的是因透水事故關閉的小煤礦全部又開起來,看周圍房屋蓋的間數,看周圍煤炭扒出來的堆子,像是比原先開采的數量多。
孫大路手往西邊指著說,那座小煤礦是我開頭干活的地方。
孫大路手往東邊指著說,那座小煤礦是我后來干活的地方。
水英反倒不知道在孫大路面前說什么話好。
孫大路說,我死后你得依著我兩件事。
水英知道這是孫大路交代后事了。
孫大路說,頭一件事是,大龍長大就是餓死也不要進小煤礦混飯吃。
水英點頭答應下來。
孫大路說,第二件事是,小鳳長大就是找不著婆家也不要嫁給扒煤的。
水英點頭答應下來。
水英心里有一句話想問一問孫大路,沒去問。這句話是難道這一輩子你做錯了,我也做錯了,你不該下小煤礦扒煤炭,我不該嫁給你?
孫大路連續出汗一個月,嘴里的一口氣愈喘愈弱,像一條游絲似的猛然一下斷裂開。水英親手安葬孫大路,沒落一滴眼淚。在水英的的心里,孫大路早一天走上黃泉路,對他是一種解脫,對自己也是一種解脫。一兒一女倒是一哭再哭,他們不知道失去父親的日子該怎么往下過。水英說,我還是去山北菜市場上賣草雞。
8
前后一個月,菜市場變化不小。連接菜市場的一段泥濘道路修好了。一片露天菜市場搭上了頂棚。這么兩種變化似乎與水英做生意關系不大。水英沒想到的是,菜市場西邊自己賣雞的地方,占上另外一家賣雞的。水英一聽這人的說話口音,一看這人賣雞的毛色,就斷定是一個淮陽人。一個賣雞的與另一個賣雞的哪有道理好說呢。水英丟下手里賣雞的三輪車,去找村委會干部。
村委會干部說,要找你就去菜市場辦公室找李麻子吧。
水英說,我來反映別人占我攤位的事情,我找李麻子做什么?
村委會干部說,我們村委會不再具體管理菜市場,已經交給李麻子。
水英算是把話聽明白了。
李麻子不是麻子,這地方人說誰是麻子,就等于說誰是一個能人。李麻子也是一個淮陽人,一直在菜市場承包修路、搭棚工程什么的,怎么會搖身一變管理起菜市場呢?其實道理也簡單,管理菜市場關鍵是收取攤位的管理費。本地村民種菜、賣菜隨便地擺在路兩邊,不占攤位,不繳管理費。淮陽人販菜、賣菜,占一溜攤位,上兩三個人手,說是一家子,只繳一份管理費。實際上兩三個人是分開賣菜,各做各的生意。李麻子從村委會手里接過菜市場的管理權利,按月上繳給村委會管理費用,上繳得比村委會自己收得多,還節省一分心力,村干部何樂而不為呢?李麻子管理菜市場,把原先露天的地方修上水泥臺子,搭上玻璃鋼瓦頂棚。這么一做,本地村民賣菜不進菜棚沒地方賣菜,一進菜棚,李麻子理所當然地收取管理費用。再說淮陽菜販子與李麻子是一個地方的,誰跟誰是一家人,誰跟誰不是一家人,騙誰也不能騙李麻子呀。李麻子接過承包權利,整天在菜市場上轉悠,賣菜的與賣菜的、賣菜的與買菜的,真是少去好多是非呢。水英向別人問清菜市場的這些變化,明知李麻子不會幫助她說話,硬著頭皮還是去找一趟李麻子。
李麻子坐在辦公桌前面抽著煙,一只腳抬起來搭在桌面子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家伙。李麻子沒等水英把話說明白,就把話頭接過去。
李麻子說,俺管理菜市場跟村委會不一樣,誰進菜市場做買賣誰繳管理費,誰愿意在哪地方做生意俺也不去管,這叫自由買賣,合法收費。
淮陽人說話侉腔侉調的,愛說一個“俺”字。
水英說,這話是你說的,我把攤子擺在菜市場的東邊去。
李麻子說,要是你能把生意做下去,你想擺哪里擺哪里,俺還能管著你?
水英說,我手里握著一把殺雞刀,誰礙著我做生意我砍誰。
李麻子笑一笑說,真要是這樣的話,俺就更管不著你,怕就得打電話找110。
水英嘴上說一說大話、狠話,哪敢把賣雞
的攤子擺在菜市場的東邊,反倒是退回頭把賣雞的攤子設在更西邊的一片空地里。
水英眼里憋屈著淚沒有流出來。
水英死去男人,缺少人做幫手,生意就得分開做,一天回山南老家收購雞,一天來菜市場出攤子。兒子初中畢業沒能考上高中,想幫著水英一起做生意,水英不愿意。水英說,你跟我賣雞會有什么大出息。大龍說,你一個人又是買又是賣的怎么能忙過來?水英說,我把生意分開做,一天去山南集市上買雞,一天去山北菜市場上賣雞,我做不了多生意,我做少生意,我做不了快生意,我做慢生意。水英想兒子初中畢業能干什么呢?水英讓兒子進城里的烹飪學校學廚師,而后托熟人讓兒子進一家大酒樓。按照水英的想法,一個人要是能吃飽肚子,還能掙著錢,就是一個有大出息的人。水英的兒子進酒樓上班,跟水英一起住。水英的閨女單獨一個人留在山南老家繼續上初中。按照水英的想法,閨女初中畢業要是不愿意接著上高中,也不讓她跟著自己做賣雞的生意,一個女孩子家“賣雞、賣雞”的說出去就不是一件好聽的事情,只是眼下還沒想好閨女將來能做什么事。倒是小鳳自己有一個想法,說我初中畢業進城租一間門面房賣衣服。水英想,閨女真要是開一間賣服裝的店面也不錯。水英這么盤算好一兒一女的事情,覺得往后的日子會愈過愈見起色,愈過愈見紅火。
哪里想得到李麻子會上門找茬子。
水英往更西的西邊擺攤子,不去招惹淮陽人,不去找淮陽人的茬子,不代表淮陽人不找水英的茬子。李麻子現在成為淮陽人在這個菜市場上的代表。李麻子找水英的茬子,就是淮陽人找水英的茬子。李麻子找茬子的目的就是想把水英從菜市場上攆出去。
這一天,水英前腳收攤子往回走,李麻子后腳跟過來。水英一直忙著生意,根本就沒去注意李麻子從身后跟過來。水英走進院子,李麻子跟進院子;水英走進屋里,李麻子跟進屋里。水英猛然回頭看見李麻子站身后,無聲無息的像是一個鬼,嚇一跳。
水英驚訝地說一聲,哎喲我的媽媽喲。
李麻子說,俺不是你媽,俺是李書文。
李書文是李麻子的真實名字。
水英警覺地問,這是我的家,你來干什么?
李麻子滿臉不懷好意地笑著說,不干什么俺就不能來你家坐坐啦?
水英冷靜下來說,我一個寡婦女人家,你來我家坐坐不方便吧?
李麻子說,俺來看看你有沒有什么地方需要男人幫忙的。
水英堅決地說,沒有,你走吧!
李麻子不怕看水英的臉色,問,真的沒有什么要幫忙的嗎?候你想好了俺走也不遲。
水英不再答理李麻子的話茬子,自己往屋子外面走,往院子外面走。
水英說,你不走我就喊人了?
李麻子說,你看看你這個女人,俺好心還當作驢肝肺了呢。
——這是頭一回李麻子上門找水英的茬子。中間相隔一天,李麻子第二次找上門。
李麻子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死了老婆,水英聽說他跟好多個女人有關系。李麻子長相丑,抽煙抽出一嘴大黃牙,又加上頓頓喜歡喝二兩白酒,走在人面前,離好遠就能聞見一股刺鼻的煙酒味。這些女人跟他有關聯還不是看上他口袋里的一點錢?李麻子口袋里有錢,膽子就大,搞在菜市場里做生意的各種女人,當地的,外地的,甚至本村的。有一個算是他的親侄媳婦,三十多歲,長得有點姿色,在菜市場上擺攤賣花椒、大料等干貨。李麻子的親侄子,名叫李瘸子。李瘸子是個真瘸子,兩年前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斷一條腿,殘廢了,整天呆在家里靠著女人吃,靠著女人喝。自己的女人給自己戴綠帽子,還是自己親叔叔的綠帽子。李瘸子先是找到李麻子。
李瘸子問,你知不知道她是你的親侄媳婦?
李麻子說,俺眼里只有女人,沒有什么侄媳婦不侄媳婦。
李瘸子說,可她明明是俺的女人,你的親侄媳婦嘛!
李麻子說,她跟你睡覺是你的女人,她跟俺睡覺就是俺的女人。
李瘸子跟這樣的一個畜生叔叔說什么道理呢。
李瘸子說,你會遭老天報應的。
李麻子說,俺不怕。
李瘸子問自己的女人。
李瘸子問,你知不知道李麻子是你的親叔叔?
女人說,俺眼里只有男人,沒有什么親叔叔不親叔叔。
李麻子說,可他明明是你的親叔叔嘛!
女人說,俺跟你離婚,他還是俺親叔叔嗎?
李瘸子不敢多說話了,要是女人跟自己離婚,自己連一口飯都沒得吃。
女人實話說,莫看他那么丑那么老的一個男人,哪次從口袋掏出來的錢都是新嶄嶄的。女人說著話還把脖子上的一條白金項鏈露出來給男人看,說我跟你睡十幾年你給我買了什么?俺跟他睡半年人家就給俺買一根金鏈子。
李瘸子的腦袋一點一點耷拉進褲襠里。
水英第二次很警覺,看見李麻子蒼蠅一般聞著腥氣跟過來,自己連大門都沒開。大門外是一條路,人來人往,量李麻子也不敢怎么樣。
李麻子說,俺來跟你說一件正經事。
水英心里一陣好笑,李麻子這種人會有正經事?
水英說,你說吧?
李麻子說,你開門俺倆進屋里說。
水英說,站在大門外面不是一樣說?
李麻子說,你這個月的攤位管理費還沒繳呢!
攤位管理費是一個月一繳,每月月初繳,水英一馬虎,這個月忘記繳。
水英說,我現在就把錢給你。
水英從口袋里掏出錢。
李麻子說,俺現在身上沒帶收據,也沒帶公章。你現在給錢,俺現在不能收錢。
水英說,我不要收據。
李麻子一副公事公辦的口氣說,你要不要收據是你的事,俺給不給收據是俺的事,你不想說清楚,俺還想說清楚呢。
水英憋一肚子委屈,嘴上卻說不出一句話。
李麻子說,你明天去俺辦公室繳。
李麻子的身子一影一影地走離開。
李麻子口袋不缺錢,身邊就不缺女人。李麻子一回兩回來找水英的茬子,不是想跟水英有什么勾連。李麻子就是想騷擾水英,就是想讓水英過不上安生日子,就是想把水英攆出菜市場。水英真的要是跟李麻子勾連上,那又是另外一種說法了。水英不想跟李麻子有沾染,就得想法子,一是去別處的菜市場,其次是搬離菜市場遠一點。這么兩種法子水英都不愿意做,就得另外想法子。水英的婆家有不少村人在菜市場附近做著各種各樣的事;水英的娘家也有不少村人在菜市場附近做著各種各樣的事,水英聯系十幾個算是比較親近的村人,把這件事說清楚,準備找一個適當機會好好地教訓李麻子一頓。
一句話,水英不想把這種受氣的日子沒完沒了地過下去。
9
機會說來就來,來的有點突然,來的有點超出水英的料想。
這一天,菜市場東頭幾戶淮陽賣雞的人家也把攤子轉移到菜市場的西邊來。東邊的三戶人家加上西邊的一戶人家,正好前后左右把水英的攤子夾中間。俗話說,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水英看著淮陽人的一只只紅眼,忍氣吞聲地不說話。你做你的生意,我做我的生意。水英有意躲避著淮陽賣雞的,心里說我看你們今天能找著我的什么茬子?一個人存心想找另一個人的茬子怎么都能找著。水英嘴閉著,淮陽人
還是說水英張嘴罵人了。
水英說,我上下牙齒緊咬著一直沒松開,怎么會罵人呢?
說水英罵人的女人問另外三個女人,你們聽見沒聽見?
三個女人一齊說,俺們聽得清清楚楚的,怎么會沒聽見?
水英問,你們聽見我罵人,你們說我罵什么啦?
說水英罵人的女人說,這種話你能罵出口,俺都學不出口。
另外三個女人附和說,對,要多難聽有多難聽,要多惡毒有多惡毒。
四個淮陽女人的臉上一片笑瞇瞇的,水英的心里卻一陣陣抖起來。
四家賣雞的女人,一個長得比一個壯實,水英長得細胳膊細腿的,哪個女人上來打架,水英都不是人家的對手,更莫說四個女人一齊上了。水英說理說不過四個女人,打架更是打不過四個女人。
水英依舊一張嘴緊閉著不說話。
水英想罷休,四個淮陽女人不想罷休。四個女人相互對一下眼色,一步一步地朝著水英圍擁過來。水英心想四個女人要一齊上來打她,跑又跑不掉,跑掉也不適合。從某些方面來說,水英要的就是一頓結結實實的挨打,要的就是一個實實在在教訓淮陽人的機會。
水英一張臉仰得高高的,心里很害怕,嘴上卻連聲問,你們干什么?你們干嘛欺負人?
四個女人不說話。
四個女人怎樣整治水英是事先說好的,他們不動水英一根手指頭,七手八腳地把水英的雞籠子打開來,把雞全部放出來。一只只雞像逃出監獄大門的犯人,拼命地喊叫著,往菜市場的各個角落奔跑開。一時間,雞飛人叫,菜市場亂成一片。四個女人一齊站在水英空著的雞籠子面前,等候著水英跟她們爭吵,等候著水英跟她們廝打。
四個女人的等候落空了。
水英不去跟淮陽人爭吵,不去追捕逃跑的公雞,而是丟下一個空攤子,跑往菜市場的另一邊。四個女人使勁地眨動四雙大眼,一副不明就里的樣子。站在遠處的李麻子使勁地眨動一雙小眼,也一副不明就里的樣子。
這件事是李麻子一手策劃的。
李麻子只能策劃事件的上半場,卻不知道下半場怎么辦。也就是說,李麻子能當四個淮陽女人的家,卻當不了水英的家。
水英跑去菜市場的另一邊找一臺公用電話給兒子打電話。水英簡單地跟兒子說出菜市場發生的事情,指示兒子去找誰誰誰,還去找誰誰誰。水英嘴里說出的誰誰誰、誰誰誰,都是事先打過招呼的,說好有事過來幫忙的。水英嘴里說出的誰誰誰、誰誰誰的電話、手機等聯絡方式兒子手里都有,也是事先跟兒子說過的。水英電話里跟兒子說,你告訴他們不許空著兩手來,有刀的拿刀,有锨的扛锨,砍死這幫淮陽人,我去償命!
水英打過電話,一身輕松地回到攤子旁邊,望著一只空雞籠子,一臉笑瞇瞇的像是跑掉的是別人家的雞。菜市場圍觀看熱鬧的人糊涂了,四個賣雞的女人也糊涂了。她們打眼去找躲在菜市場拐角的李麻子,早不見他的影子。
其中三個過西頭賣雞的女人想把攤子撤回菜市場的東邊。
另一個賣雞的女人說,你們走俺也走。
水英說,你們四個誰也莫想走,過一會就有你們好看的。
四個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莫不是水英打110報了警。
四個女人交代說,是李麻子讓俺們這么做的,你報警也只能去找他。
水英說,我不管李麻子、張麻子、王麻子,我只知道你們都是一伙淮陽人。
大龍很快跑過來,沒帶一個手里拿刀的親戚朋友,也沒帶一個肩上扛锨的親戚朋友。水英大聲問兒子,我讓你喊的人呢?大龍長得高高條條的很帥氣,順手往身后一指說,我帶著小蘭子。小蘭子是個細胳膊細腿的小姑娘,看著沒有三兩力氣。水英不知道小蘭子是做什么的,四個賣雞的女人卻人人害怕她,一個個把頭低下來。
小蘭子說話也是淮陽腔調,說四個賣雞的女人,你們欺負人也睜眼看一看是欺負誰?
小蘭子是李麻子的親侄女,與大龍在同一家酒樓里打工。小蘭子看上了大龍的帥氣,大龍也看上了小蘭子的俊氣,兩人偷偷摸摸談起對象來。小蘭子陪著大龍把水英的空雞籠子搬回家。小蘭子跟水英說,俺大姨你在家里歇一歇,消消氣,她們放跑你好多雞,俺讓她們一分不少地賠給你。水英心里沒有底,不相信這個細胳膊細腿的小姑娘能辦成這么大的事。大龍心里有數,說娘,在酒店里小蘭子比我會混事,她想辦的事她肯定能辦成。
小蘭子不去找她的叔叔,跟前跟后地追著四個賣雞的女人要跑掉的雞錢。小蘭子說,誰放俺大姨的雞,俺就問誰要錢,你們一天不把錢拿出來,俺叫你們一天做不安生意。淮陽的男人、女人都厲害,小蘭子也是一個厲害的姑娘。四個淮陽女人自覺理虧,跟前跟后地追著李麻子要錢。四個賣雞的女人說,主意是你出的,這錢就該你賠。李麻子不害怕小蘭子,更不害怕四個淮陽女人,只是小蘭子這么一攪和,耽誤他在菜市場上收管理費,損失更多的錢,這才很不情愿地掏錢賠水英。
真的沒用水英出面,小蘭子就把這事辦妥當。
水英問兒子,你真的喜歡這個小蘭子?
大龍問,娘,難道你不喜歡她?
水英大笑起來說,這么有本事的小姑娘我能不喜歡?
大龍說,我還擔心娘不喜歡淮陽人呢?
水英說,有了小蘭子,看誰還敢欺負娘在菜市場上做生意。
10
轉眼,又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快到了。
這么多天來,水英一直在菜市場上賣雞。菜市場西邊,原先水英賣雞的地方被李麻子搭起賣菜的棚子,水英只得把賣雞的攤子擺在菜市場的東邊,混在幾家淮陽賣雞人的中間。有小蘭子在里邊牽扯著,水英跟幾戶淮陽賣雞的人家有了割舍不斷的親戚關系。幾家賣雞的女人臉上一片笑瞇瞇地主動騰出一片地方讓水英安插進來。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水英雞籠子里的草雞。一只只羽毛雜亂,瘟頭瘟腦,一看就知是從遠道運過來的淮陽草雞。買雞、賣雞,水英一個人確實忙不過來。雞販子能把一籠籠淮陽草雞送進水英的攤位跟前,更主要的是賣一只淮陽草雞不比賣一只山南草雞少賺錢,水英干嘛要一根死腦筋呢。倒是吃慣水英山南草雞的顧客不習慣,問水英怎么不賣山南草雞啦?水英連蒙帶騙地說,不是山南草雞是什么?顧客說,這山南草雞怎么跟從前的山南草雞不一樣?水英大包大攬地說,不是正宗的山南草雞,我一分錢不會要!水英睜著眼睛說瞎話,幾個賣雞的女人在一旁“哧、哧、哧”地偷著笑。水英怒眼對著幾個女人說,你們笑啥子,你們說俺賣的不是山南草雞是啥子雞?
淮陽人說話除去“俺、俺、俺”的,還說“啥、啥、啥”的。水英在淮陽人中間呆時間一長,不知不覺地說話帶上淮陽口音。
大龍、小蘭子還在那家酒家里。小鳳一個人在山南家里上學上夠了,初中二年級停下來不上了,也跟著過山北這一邊。小鳳小,先幫著別人家看一看服裝店。水英說,候你長大了,候你長能耐了,也候我手里有錢了,才能自己開服裝店。
現在兩個孩子一起跟著水英在山北過日子,沒有必要回山南,一個山南的家也就漸漸地陌生了。
水英一連幾個月沒回山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