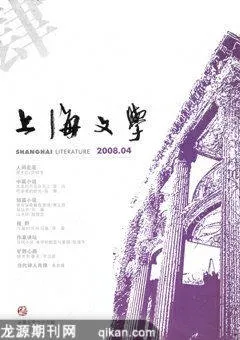飛越時間的鳥巢
1
那個周日下午,我在哄鹿歌睡覺時錯過了一個打給我手機的電話。孩子睡著后我回到小書房,急于回到午餐前中斷了的工作。但忍不住查了一下手機打入電話歷史欄里那個最新的號碼,非常陌生,好像是用電話卡打的,連從哪個州來的都無法判斷。換了平時我會置之不理,判斷要么是錯號要么是討厭的促銷廣告電話。我停頓了一下,隱約感覺到那個號碼后面潛伏著一種能量,那個撥號的手是否握著一把通向我過去或未來的鑰匙?
這與以往寂寞空曠中期待愛情甚或任何事件的發(fā)生很不一樣。這個多事之春延入一個難得不是海陸空時差中度過的夏季,一檔子一檔子發(fā)生了許多事,見了很多我笑稱為“牛鬼蛇神”的故人或新友(是的,新人也有感覺像故人的,相見恨晚或似曾相識)。本來生了孩子買了房子拿了資本主義“鐵飯碗”后似乎超穩(wěn)定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突然變得危機重重,卻又似乎充滿了變數(shù)和契機。很久以來我重新獲得強烈的夢境,感受到身心的饑渴,從中獲得種種微妙的啟示。我重新開始用中文寫一些東西,斷斷續(xù)續(xù)地不成篇章,跟心情夢境囈語一樣破碎,創(chuàng)作于我已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好像維持開銷后才能開始考慮儲蓄甚或投資一樣。有了孩子更是連睡覺看報的時間都沒有了。
是的,當母親好像是重新學會看鐘,重新認識時間這個神奇的,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的存在。沒日沒夜的嬰兒的混沌,混合著奶香,彌漫于每分每秒,似乎把我席卷而起,然后抖碎,像星辰一樣散落,不著邊際,突然覺得腳底要踏空的感覺。從1980年代初開始的那次為了自由和愛情背井離鄉(xiāng),好像既是被迫的又是奮不顧身的,借用當時的一個與晚期社會主義抑或“修正主義”有關的比喻,更接近人造衛(wèi)星脫離地面被射向星空的狀態(tài)。但不尋常的速度似乎使我早就脫軌,與任何指揮中心失去聯(lián)系。衛(wèi)星上天,紅旗真的落地嗎?我真的上了一條無歸路嗎?
在沒有游樂場穿山道飛車的時代,那種先是由幻想、小說、詩歌以及電影承載,后來干脆跳上長途汽車火車能去多遠便多遠的義無反顧,成為之后轟轟烈烈的出國大潮帶著光速的先聲。未完成的青春序曲和沒有讀完的學位,與之有關的年久失修的家鄉(xiāng)與國家都被遠遠地拋在身后,拋在破舊骯臟的大小站臺上。
為了大沼澤的呼喚
我駛出月臺/駛出深深的夜……
(《月臺》,1982)
2
我撥通了那個異樣號碼,謹慎地用英文說明我是誰,是回答一個不知來自何方的電話。一個輕揚的女聲用上海話驚喜地說她姓周,我中學同學,從朋友那里得到我的消息。聽不出像個中年婦女的聲音。她說沒能在紐約碰上頭,很遺憾。此刻她和家人在中西部的高速公路上,老公開車,兩個男孩自顧自玩,沒事試著給我打個電話。我從電話的時強時弱的聲頻中似乎聽到汽車輪在橫貫美國80號公路地面上的因高速產(chǎn)生的摩擦。那個快速行進中封閉的鐵盒載著一個與我1983年盛夏留在上海北站的過去多少有關的女人,還有她在美國創(chuàng)造的家庭。他們年前已隨“海歸”大潮回滬,這次是來度假。我很抱歉地說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也許見面會想起。她的聲音好像來自一部錄音書磁帶,清晰悅耳,卻勾勒不出任何我能記起的臉龐。就這樣,她用親切的鄉(xiāng)音帶我上路,開始了我完全沒準備的一次時間之旅。
看完好友唐穎從上海帶來的新作《初夜》,這比先前她關于上海70年代以降的諸種小說,更能使讀者強烈地感受那個年代,那個拉扯我們長大的城市在無可挽回地消逝。營養(yǎng)不良、缺乏血色的日子荒誕地澆灌了無數(shù)關于飛翔的夢。出國前唯一接近飛機的記憶,是隨中學的迎賓隊去西郊的虹橋機場,我那時跳舞不錯,但被認為長得不夠俊俏可愛,安排在隊伍后面,離飛機、跑道和外賓都很遠。好像壓根就沒看到一個外賓的高鼻子紅頭發(fā),只見同學們揮舞的手臂彩帶——周姓同學是否也在呢?太陽刺眼得很,機場上連塊陰影也沒有。我急盼一切快快結束,可以上廁所回家。我對這種讓女孩躍躍欲試,可借此化妝打扮“祖國的花朵”的迎賓活動很快就厭倦了。倒是夏夜乘涼時,仰望星空里偶爾掠過機器鳥一般的飛機,對黑夜毫無畏懼,不知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使我生出遐想。不知自己來生是否能坐上飛機或飛船,去哪里,倒不是最重要的。
唐穎到紐約上州Ithaca來看這個香格里拉似的大學城,來看今夏無法飛越美國國境的我,是說來就來了,從遙遠的上海飛來,有點不可思議。到紐約還沒倒完時差她就坐“短線公司”(Shortline)的長途車來到離紐約五個小時的“手指湖區(qū)”(Finger Lakes Region)。一周我們絮絮叨叨地用上海話談天說地,話東道西,沒完沒了的girl-talk交換為人母的喜悅與煩惱。唐穎飛回上海后,在我步入中年的一個重要時際,深夜讀完作為生日禮物的《初夜》,我好像被推上一條無形的軌道,射入時間的黑洞。三十年前的上海突然從失憶的迷霧里漸現(xiàn),如電影里的閃回一般。小說主人公蝶來三十多年后在寂寞寒冷的美國中西部小城通過迂回曲折的電話線,重新正視少女時代的創(chuàng)痛,本為了重續(xù)初戀舊情,卻引出另一段被長久壓抑的幽怨,名不正言不順,剪不斷理還亂。正是這個她生命里的“不速之客”及其不期而至的病逝,不僅給予蝶來的過往和現(xiàn)狀以新的意義,更使《初夜》進入了文化史的范疇。從冷戰(zhàn)到全球化,蝶來和她的青梅竹馬的友人和情人們,追求著物質(zhì)的自由,遠走高飛的自由,性和愛的自由,彌補青春實現(xiàn)自己的自由,卻無時不再地被那個叫做“自由”的多面怪獸驅(qū)趕著,疲于奔命。這已經(jīng)不只是一個關于上海的故事。
第二天我在筆記本里寫道:“小說里看到TY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的影子……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已成廢墟,埋葬了我們的青春。去年夏天回滬,與TY在淮海路見面逛街,她拐彎帶我去看了她家老房子弄堂,還在,仍充滿生活氣息。但對她已是‘鬼域’。……小說帶來的懷舊感,有點像追悼感。”十年前我回到市中心兒時的老房子,聽說快要拆了,我照了幾張相片,沒有勇氣去敲門找舊日玩伴就匆匆“逃走”了,好像一半是怕無人應門,人去樓空,一半是怕找到了人相見不相識,無言以對。“逃”路上經(jīng)過曾充滿歡笑與眼淚的幼兒園,一半已是斷墻殘壁,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以前接受愛國教育時必然提到的八國聯(lián)軍和頤和園。
我在電話里,對高速公路上的老同學大力推薦這部小說,她好像一邊在忙著從手提包里找紙筆記錄,好像一邊在點頭同意我說我們的“重逢”,很多是因為見證我們少年時代的老房子、學校、鄰居等等都蕩然無存了。我好像患了失憶癥,記不起她的名字和面容。她說身邊開車的老公也是老同學,我也無法回憶。但說起小時住處,南京路華僑商店后面,六合路中百公司對面弄堂,西藏路北京路口等等,那些市中心街區(qū)里弄三十年前的樣子,特別是“后面”、“對面”、“路口”這些浸透了人氣、體溫與故事的微觀地理與人文空間,雖然大都已從上海最新版的地圖上消失,突然在我眼前清晰具體到可以觸摸。
我們都是屬于閣樓的女孩子
我們的梯子的色澤和極數(shù)相差無幾
我們互相愛慕又互相嫉恨
時而是天使,時而又是女巫
我們?yōu)闊o從認清的情誼煩惱哭泣
我們是彼此心上的麥芽糖
永遠的傷痕
(《閣樓》,1983)
3
好像電源的正負兩極相通產(chǎn)生能量。這位老同學的出現(xiàn)與那些作為我們少年青春載體的時空化為烏有有關。我沒有提到其他的因素,比如人到中年感懷流年似水,流落他鄉(xiāng)的最好的年華與童年少年之間的橋梁要么早就斷裂,要么已成浮橋,沒有確定的方位。也沒有提到可能是唐穎這個我近幾年才獲得的鄉(xiāng)親摯友,用她的記憶和文學再現(xiàn)的魔力棒,將這個“老同學”變戲法似地引出場。不然怎么我剛看完小說,淚眼迷蒙地試圖追溯自己的少女時代,正為怎么也記不起而羞惱的時候,老同學(確切說,她的聲音)就出現(xiàn)了呢?
她的落落大方的上海話,是從沒間斷過使用和刷新,從小天地到大世界,出國又回滬,多次回爐后的那種,包涵量很大。語氣里絲毫沒有怪我“貴人多忘事”的意思。我開始安心下來,但仍緊握手機,神差鬼使似地任她的聲音帶我走向那些塵封的地域與形象。她先說到我們不是同班的,這讓我的愧疚稍稍減輕。不可思議的是,她竟然記得好多我們8班的事,而我連自己是8班都忘了!首當其沖提到我們的班主任,對,是姓吳。她說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那時孩子還很小,很可憐。這消息如晴天霹靂,怎么說我也沒料想到在這個時代比我父母還年輕的人,會這么快就走了。
讀《初夜》產(chǎn)生的濃重的追悼感忽然鋪天蓋地彌漫到我個人很具體的歷史里了。吳老師是那時知青回爐訓練后來當我們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比我們也就大十幾歲吧。他個子不高,精瘦,與其他老師不一樣,很有幽默感,背一個當時算時髦有風度的洗得發(fā)白的軍用書包。他跟我們這些發(fā)育中的小孩子有點沒大沒小,像我們的大哥或小叔似的。他教中國語文,卻用上海話授課,唯有朗讀正文時會用蹩腳的普通話,常常令我們發(fā)笑。他為了維持課堂紀律或保持那么一點“師道尊嚴”,故意板起臉裝嚴肅,卻“噗哧”自己先笑了。那些年的課本里充斥了不少泛政治化的內(nèi)容,但也有不少中國文學史上的佳作段落。吳老師對古文詩詞和20世紀初散文情有獨鐘,對我那時開始寫詩有影響。這個老師我當時并沒有看作自己的啟蒙者,以為自己從饑不擇食的大量課外閱讀中得到了足夠文學養(yǎng)分。更何況我們幾個“高材生”視他為兄長,還去他家玩(那時他還是單身,隨父母住),好像在八仙橋那邊。他家二樓對天井的客廳,寬敞明亮通風。這也許是后來剛上了大學后去他婚后住的北京路一帶一條弄堂里昏暗的小房間以后產(chǎn)生的對照印象。
他和顯得很和善的妻子坐在床邊的陰影中,突然給我一種時過境遷的荒涼感。我那時最怕的就是看見生機勃勃的青年人結婚后被捉襟見肘的日常生活吞噬掉,為此自己想好不要結婚成立家庭,不要為要命的房子問題、油米醬醋之類而過早衰老,放棄追求。他不經(jīng)心地問了我一些近況,一點也不談自己的事。好像我們都感覺到了距離,好像師生關系走到頭了。我去看他一方面是要取回寄他的一些文學習作,他說搬家后還沒找出來。我感覺是他弄丟了,就不好意思再提。他對我和隨同去的女友微笑著說,“看著吧,張真是很有野心的。”我當時一愣,不知這話的含義,是好是壞。多年后想起與他這次最后的見面,就會想起這句不著邊際的話,覺得不是滋味。這也可能是我再沒有拜訪他的原因之一。沒過幾年我就離開上海翻山越嶺,橫跨西伯利亞赴北歐了。那時出國沒錢有膽,有一種赴湯蹈火,好像飛向太空一去不復返的氣勢。
現(xiàn)在想來,吳老師怕是當時我從少年邁向成人階段最了解我的人了,我的強勢與弱點他似乎一目了然。他也從我父母那里了解到我作為長女大姐“母性”的能力,將在郊區(qū)學農(nóng)的全班的采購與伙食的重擔委任與我。在電話里,老同學提醒了這個細節(jié),說,“你們吳老師說讓你當家,‘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嘛。”吳老師沒有我認識的其他大人們的病態(tài)或虛偽。他似乎看透了那個才氣逼人的少女對一種莫名的東西(或者就叫自由)的向往遠勝過對知識或名利的渴望。我此刻才意識到,也許那正是他自己的“野心”!我離開上了兩年的初中去浦東上重點高中,后來考上復旦大學都沒有善始善終,對那些框框很多、束手束腳的機構很膩煩。住讀使我從家庭和弄堂的嘈雜中解放,但七八人上下鋪擠一室,軍隊化的集體生活讓我更壓抑,連個藏日記的角落都沒有。頂著當時“四個現(xiàn)代化”口號的壓力,不顧父母的反對,我設法脫離了那個集中營一樣的理科高中,將自己轉回市區(qū)人民廣場附近一個普通高中的文科班,滿腔熱情地補修地理歷史。每天穿過當時仍需門票或月票的人民公園,出西門經(jīng)過上海圖書館(現(xiàn)美術館),黃陂路上的花鳥市場,再轉入彎彎曲曲的窄巷。
那是些在普通地圖上找不到的城市秘徑,細微的神經(jīng)末梢。我每天獨自一絲不茍地穿梭來回,在那個多雨的春天,讀爛了很多書本,做了很多夢,迫不及待地走完了缺乏營養(yǎng)、發(fā)育不足的少女時代。那條七轉八彎的小巷里,有時我會從雨傘下瞥見另一個為別的原因從浦東高中轉來這邊理科班的男生,遠遠走在我的后面。他原來坐我后排,早我半年轉走的。現(xiàn)在好像我們從不認識似的。后來上了不同的大學后我們卻成為好友知己。最終他也像衛(wèi)星一樣彈飛出去了,在法國謀生,學建筑之余給《今天》編輯小說。周姓同學來電前不久,我剛收到他與法國女友生的女兒的照片。她比鹿歌小幾個月,但神情中那一絲憂愁與鹿歌的很像,似乎都與那些雨巷有關。說遠了,那該是另文詳述的一個故事。
我們是孤兒,是囚徒
是那車窗外即逝而永存的樹木
是那光團里湮滅而升騰的煙霧
(《潛行》,1983)
4
吳老師的死訊,差不多跨越了一個時代,越過了新世紀才抵達,我才真正體會到人去樓空了,更確切地說,是人亡樓廢了。吳老師隨著一個消失了的上海走了,化為灰燼與煙霧。但他的幽靈是否還常常嘗試沿著熟悉的馬路弄堂,去探訪1949年前曾是英國租界巡捕房的校舍和住在周邊“南京東路街道”的學生們?我突然很想回到西藏路已不復存在的老房子,回到初一的我,看到老師走近我們8號大門,趕緊進屋按家里招待來客的“儀式”,打開日光燈,沏上一杯茶,然后安靜地坐在一邊,聽老師與父母交談。
這個畫面讓我突然想起吳老師并不是我的青春回憶中第一個英年早逝的,雖然他是最早認識我的“野心”的一個有趣的成年人。從我上大學后,進入詩歌圈子,到出國前,來我家找我的人越來越多。處在市中心的我家,交通方便,雖然窄小,卻在那沒有茶館咖啡館之類公共空間的年代成了一個小聚會“沙龍”。每次來人,我照樣開日光燈,沏茶,有時也會用母親珍藏的咖啡器具煮上海咖啡,還必然拿上精致的玻璃煙缸。當時男人,尤其詩人大都抽煙,我也就跟著一起吞云吐霧,擺一個瀟灑入流的樣子。抽得最兇的是王小龍,比我們這些“校園詩人”大一撥,是個兄長角色。但其中一個不抽煙的,也不留長發(fā)的詩人是顧城。好像還是王小龍介紹帶來的。顧城不是上海人這一點也很突出,一口標準的北京話,加上他才氣過人,出口成章,又是“奇裝異服”(雪白的襯衣或淺色中山裝扣到脖頸),一切都不同凡響。顧城1993年秋在新西蘭小島上自殺,可能要比吳老師病逝走得更早更匆忙,更沒有后者死在家鄉(xiāng)的運氣。
當時顧城和他的詩歌已名揚四海,認識他我有點受寵若驚,好像見到天仙下凡,果然也食人間煙火。他是帶著新婚的妻子謝燁來的。聽他們說是在京滬火車上認識相愛,之后顧城就窮追到上海求婚。岳母不同意女兒嫁給窮詩人。因為謝燁也深愛顧城,兩人還是結成了婚。但上海住房緊張,顧城沒有戶口,又是無業(yè)游民,兩人無處安身,便在兩幢房屋之間的一塊方寸之地上自己動手蓋起一個小屋,也就是違章建筑吧。我當時聽著這現(xiàn)世童話,看著眼前黑眼睛閃亮的金童玉女,懷疑自己隨他們?nèi)チ嘶鹦牵⊥瑯拥兀麄兛粗煲獑⒊谈半x安徒生故鄉(xiāng)不遠的瑞典南方的我,扎著兩根辮子,形同灰姑娘躍躍欲試要去參加舞會,就差水晶鞋(或曰出國護照)沒到位了。跟他們在一起,與跟其他憂國憂民的詩人好友見面不同,更像玩家家的伙伴,蓋房做飯作詩,都是兒戲一般認真而脫俗。
我沒去過他們的那個小屋,現(xiàn)在看來,那個在過去未來任何版本的上海地圖上不存在的微型棚戶,其實是他們多年后在南太平洋激流島上白手起家蓋農(nóng)舍的排練。他們一生中唯一擁有過的這兩間房子,根本不像衛(wèi)星或宇宙飛船,而是風雨飄搖中的住家船,駛出蘇州河黃浦江,飄洋過海,闖過無數(shù)風浪,卻禁不起波及全球的海嘯。我每次送他們到弄堂口,老有心驚肉跳的不祥之感,怕他們就此從密密麻麻的人堆里無聲息地消失了。
我抱著白天媽媽曬過的枕頭
望著他們的位置
望著黑暗的幸福
(《梅雨季節(jié)到來》,1983)
跋
之后好像一直在披星戴月地趕路,在無邊際的太空中經(jīng)受失重帶來的快感與孤獨。很多人催我寫下自己的“傳奇”,作為對個人和歷史的一個交代。因為害怕直面往事,更怕傷害還活著的人們,我不敢貿(mào)然。而且,甜酸苦辣的日常生活將我磨煉成一個新人,演出各種社會角色,承擔很多責任,很少再有時間與力量回首過往。隨著時光流逝,大量日記書信在遷徙中的遺失,與一站又一站的同學、朋友、鄰居失去聯(lián)系,感覺像交通事故后動過多次大手術,換上的死者捐獻的角膜和新裝的義肢沒有與我的大腦和心臟同步的記憶,所以無法找到回歸的方向與軌道。
老同學從高速公路上的來電突然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拉開了西藏路老房子里的日光燈。在黑暗中塵封了二十多年的屋子,家具擺設,還有方桌上殘留的茶煙具一下子被照得通明。但我的眼睛卻不能適應這突如其來的記憶黑洞里射出的強光。我握話筒太緊,手心出汗,似乎怕我剛開始進入情景,突然光又滅了,一切都會化為煙靄。我的眼睛牢牢地聚焦在書房窄窗外,樹冠上方慢慢浮動的夏日白云上,好像從那里可以瞥見往西疾駛載著老同學的車子,還有吳老師在西天騰云駕霧的身影。我突然很感激這個老同學好像從光年之外傳來的信息,吳老師的死使我明白回歸之路真的已經(jīng)斷裂了,那些人事地貌歲月,從這一刻起已經(jīng)進入了傳說的世界。
電話剛掛斷,鹿歌午睡醒了,揉著眼睛,光著腳輕輕地來到我身邊。我猛然意識到這溪水叮咚,奇花異草飄香的Ithaca并非虛構卻也不是真實的。我好像進入了Tarkovski的電影《鏡子》,和Kubrick的《2001:空間奧德賽》片尾新舊交替、時空翻轉的場景。我用手指梳順兒子睡亂了的頭發(fā),突然十分思念從未見過的吳老師和顧城夫婦分別留在上海和激流島毛里人家中的孩子。他們的命運與上一個世紀的上海有關而截然不同,我從心底為他們一樣深深祝福。
……
我的一生中失去的發(fā)辮
懸著永不停息的秋千
我們的孩子坐在上邊
我們的孩子坐在上邊
一只貓頭鷹唱出他的語言
他轉過臉看熟睡的父母
那臉是一片無邊的風景
他捧著的那本大書
只限于被打開的一頁
森林的漿汁從他指縫中流出
……
他撿起一只橘子放在耳邊
聽到我們絮絮情話和心臟
他忽然感到無比羞愧
為這一切所暗示的久遠的山水
他轉回臉重新面向那一邊
我們無力看到的世界
他的背上映出一條縱深的道路……
你
是否還有力量與我一起
去夢見我們孩子手中的書
我們美麗的孩子
(《在岸和岸之外……》,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