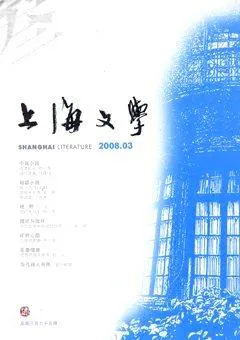靈感來自靈隱寺
美是無處不在的。世上缺的不是美,而是發現美的眼睛。
在我老家浙江永康的方巖山上,有座胡公祠。胡公名胡則,是宋代的一位好官。毛澤東1959年從廬山下來,途徑金華時,曾贊美過他。如今,毛澤東的手跡就刻在山頂的一面灰色的巨墻上,“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為了紀念他,建廟祭祀,香火一直很旺。我從小就跟大人上方巖拜胡公,那根根點燃的紅燭,是祈求胡公保佑的圖騰——神秘的圖騰。
我每到一個寺廟,總有旺盛的香燭相迎。人們每插上一根蠟燭,便寄托了一個美好的心愿。
每當舊歷大年三十,家家戶戶都點燃大紅燭。那燃燒到天明的燭火,寓寄著人們吉祥、喜慶的祈望。
我從小就喜歡紅燭和那跳動的明亮燭光。念書之后,“蠟炬成灰淚始干”印進了我的腦海。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是對教師的贊美。此時,紅燭是一種高尚人格的寫照。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大概是1993年春天,杭州選美,我有幸與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演員陳述、向梅、外交部的部長夫人和女大使們一起被聘為評委。選美,可以養眼,是一樁美差。美女選出來之后,我們到杭州古剎靈隱寺游覽朝拜。其時,靈隱寺的香火特別旺盛。那一排排紅燭,燃燒得紅紅火火。盡管有山風襲來,但匯成燭海的火焰卻頑強地飄動著,不息不滅。美女們站立在燭火的空當中,我舉機取景,攝下了一幅幅奇美而動人的照片。
離開西子湖,那些美女已漸漸淡去,甚至忘卻,而那些燃燒的紅燭,卻占據了我的腦海,揮之不去,驅之不走。
靈隱寺的燭火,觸動了我的創作靈感,點燃了我的藝術之火。此時,也只有此時,那些久已儲存在我內心深處的一根根紅燭,燃燒成一片,匯成了一個燭火的海洋,洶涌澎湃地撞擊著我的心靈。我時時處于強烈的創作沖動之中。
中國水墨畫是最講究筆墨技法的。線是中國畫筆墨的靈魂。構圖、著色也都有嚴格的規矩程式。我想畫的是一排排,一層層,重重疊疊,排山倒海似的燭火。只有這種氣勢的畫面,才能抒發我內心的激情和我追尋的意念。從傳統筆墨中,我一時無法找到合用的技法。于是,我異想天開,突破陳規舊習,無法無天了一回。就用了排筆,將中國畫顏料的大紅、深紅和入日本櫻花廣告色摻和適量丙烯,使畫面變得深沉、厚重。
四川有位畫油畫的朋友得知消息后,來電邀請我去成都創作此畫。我抵達成都時,這位熱心腸的老弟己畫了十多張紅燭。他想為我分憂,為我的新作提供一個草圖。他以為畫油畫的更懂得色彩,畫起燭火來更在行。面對著一地的“紅燭”,我只好直言相告:“你畫的紅燭全是死的。”原因在于他沒有我的那種親身感受。其實,我不是真的在畫靈隱寺的紅燭,而是在畫我自己心中的紅燭,畫第二自然。
回北京后,我到圓明園邊上一家河南人開的裱畫店,借用他們的大裱畫桌。畫友楊再春送來已存放了十七年的丈二匹紅星宣紙。裱畫師端著我調好的大半臉盆顏料,我凝神揮毫,一鼓作氣往潔白的宣紙上潑彩潑墨,先畫一排排紅燭,接著畫黃色的燭光,并用蘸著濃墨的筆寫出燭心…宣泄了大半天時間,畫成一幅題為《生命》的巨幅紅燭。
在題跋中,我贊美了蠟燭結成一個群體,燃燒起來更具生命力。燃燒發出了光,發出了熱。熊熊燃燒的燭光便是生命之火。
1996年10月9日,我在中國畫研究院舉辦畫展時,面對著一面墻的紅紅火火的燭火,人們不禁嘩然,驚訝它的氣勢和藝膽。女畫家鄧林說:“魯光,你好大膽呀!”人們紛紛以這幅大畫為背景,拍照留念。
在畫展座談會上,畫界名家和評論家們稱此畫為“魯光的專利”。一位畫家說:“我畫二十年了,還沒有自己的專利產品,魯光畫十年就有自己的專利產品了。”一位資深美術評論家說:“我最欣賞的是魯光作畫時的無法無天。中國畫的十八般武藝,他雖然沒有全掌握,但他揚長避短,只用了七八般就氣勢奪人。”中國畫研究院院長劉勃舒在總結發言時,說:“魯光一下子在美術圈里冒出來了。”
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中國總部經理,看了這個畫展,立即與我簽訂“一次性版權合同。”他購買了我十五幅畫的版權,出版了1997年魯光的《大寫意》掛歷。還出版了紅燭《生命》和牛畫《三人行》的單幅掛歷。印了數萬本,分送給他們的用戶。
榮寶齋副總經理米景陽向我索要紅燭畫。他說“掛一副到我們店里去吧!”
“在退休之前,我不賣畫。”這是我的原則。
“人家想擠都擠不進來,我們求你進你還不進…”米景陽詰問我。
我們商定只掛不賣。一幅4平方尺紅燭,掛進了以出售高檔傳統中國畫的榮寶齋店堂。它與店堂里的名家大作都不同,風格獨特,一片紅色,很跳。
不到半個月,頭一幅紅燭便從榮寶齋“走掉”了。
從1997年起,我的畫幅便陸續掛進了這個中國書畫的最高殿堂。至今已有十余年,常有畫幅從這里“走掉”。
2003年我應邀去新加坡藝溯廊辦了一個畫展。我回國的頭一天晚上,都十點鐘了。藝溯廊藝術總監余欣小姐問我:“累不累?”我說:“不累。”她說:“我和我的先生想請您去家里做客。”那是一座帶游泳池花園的大宅。客廳很寬大。進了客廳,我的眼前一亮,只見墻上掛著我的一幅紅燭畫。射燈發出柔和的光,把紅燭照得很亮。畫廊女老板告訴過我,她的丈夫,是一位商界人士,不喜歡藝術。但他卻從太太畫廊里買下我的一幅紅燭畫。我對余欣的先生說:“你不喜歡藝術,怎么會鐘情我的這幅紅燭畫呢?”他說:“這幅紅燭畫,我很喜歡。我也說不清為什么喜歡。我每天清早和夜晚,都會坐在遠處,久久觀賞它。看上五分鐘,那燭光便會晃動起來。”其實,看久了,那錯落的燭光,便讓他看眼花。不過,我也不愿點破這一層。在藝術作品前,產生任何想像都是合情合理的。這就是所謂的藝術魅力。
義烏一位年輕的老板,到我浙江山居里來走訪。被我掛在客廳里的一幅《紅燭》吸引住了。他想買走這幅畫。
“這是我用來鎮宅的,非賣品。”我說。
他從上午九時,一直到晚上八時還不走,非讓我把此畫讓給他。
后來,我去過他的工廠,沒有見到那幅紅燭畫。他領我走進他的臥室,說:“我最喜歡這幅畫,掛在臥室了。掛在外面,怕哪位領導看中了向我要……”
紅燭畫在日本也引起了強烈反響。2002年夏天,《現代中國水墨畫展》在富山舉辦時,紅燭畫是這次畫展的主打廣告,天天在日本電視上出現。推近拉遠,那飄動的燭火就變得更神奇、更壯麗、更迷人了。平時觀眾每天四五百人,閉幕那天來了一千二百多人。富山縣水墨美術館館長在送別酒宴上,對我說:“你的紅色征服了日本觀眾。許多觀眾是沖著你的紅燭來的。”
倫敦一家畫廊的女老板,在劉勃舒家見到掛歷上的那副紅燭時,說:“這幅畫很性感,在西方會有很好的市場。”起先,我吃了一驚,紅燭怎么與性感扯到一起去了呢?后來,朋友們告訴我,西方人的“性感”,與我們東方人的“性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她的意思是,紅燭畫有魅力,很吸引人。啊,原來如此!
為了頌揚周恩來總理的偉大人品,我畫過一幅《紅燭》。毛澤東主席紀念堂收藏了它。
我畫紅燭時,只是出于一種神奇的沖動。但一旦我的紅燭畫問世之后,它便越來越走紅。年輕人喜歡它,喜歡它的蓬勃生機。老板喜歡它,喜歡它紅紅火火帶來財運。革命前輩喜歡它,喜歡它雨淋不熄、風吹不滅的強大生命力。中國人喜歡它,是因為吉祥喜慶。外國人喜歡它,是因為新奇神秘。人們賦予它的想像,遠遠超越了我想表達的本意和內涵。假若有一百個人閱讀紅燭畫,那肯定會有一百種解讀與感受,藝術就這么神奇。
李苦禪大師曾說:“無法之法乃為至法。”此畫是否應了苦禪老的這句名言?
2005年秋,我應澳門基金會之邀去澳門舉辦畫展前,著名畫家、評論家周韶華先生見到了我的紅燭畫《生命》,他連夜著文作了獨到的評論,“他畫的不再是自然狀態的紅燭,而是與心靈相對應的熊熊燃燒的火把,意念中的鐵壁紅墻,與命運抗爭的生命。藝術手段不期然而然地是表現主義與象征主義的表現,完全從文人畫脫胎換骨而成為現代中國畫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可以說,這一作品是魯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作。彰顯的是現代人的壯志情懷,是不折不扣的現代中國畫。”周韶華還從藝術技法上作了點評,“他的‘大寫意’中國畫,得益于李苦禪、崔子范兩位恩師的熏陶。但是他不克隆老師,能沖破陳舊陋習,跳出老一套的框框,完全用自己的眼光去感受世界,用自己的思想去尋找新的藝術方位,用自己的表現手段解決自己的繪畫語言形式,不但與老師們拉開了距離,而且打造出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現代中國畫形式。”
我把周韶華的評點,當作一種激勵。在藝術創新上,我從不自覺走向自覺。
紅燭畫受寵愛,有市場,我當然高興。它說明我的創新追求得到了觀眾和市場的肯定。但我更看重的是透過這個現象看到我的美好藝術前程。
畫界有個戒律: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我常常以此告誡自己。
2008年1月19日
寫于珠海怡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