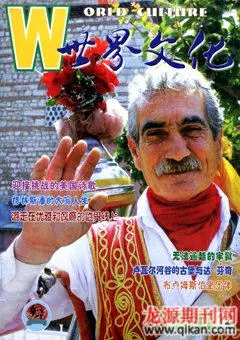盲人的純凈目光
“上帝給了我書籍/同時也給了我黑夜/這一巧妙的嘲弄令人叫絕。”
“上帝讓一雙黯然無光的眼睛/成為這座書城的主人/不管他如何努力/只能在影影綽綽的書架上/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篇章。”
——《天稟》
阿根廷小說家、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是拉美文壇乃至世界文化之林中一位充滿傳奇色彩和戲劇性的作家。他曾經獲得過“富門托”文學獎,“布克”文學獎和西班牙“塞萬提斯”獎等多種國際文學大獎,是繼聶魯達,卡彭鐵爾等大師之后拉美文學史上又一位獨具魅力的文學宗師。
★少 年★
博爾赫斯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名門望族家庭,受著英國式的童年教育。由于從小的體弱多病和父親的大量藏書使得小小的博爾赫斯終日流連在父親的書齋之中。漫長的童年時光使他閱讀了很多國家的巨著:《一千零一夜》、《熙德之歌》、甚至于有阿根廷民族文學的高峰之作《馬丁·菲耶羅》。這些東西提前叩擊了他幼小的心靈之門,讓他感到了在永恒時光中人類那短暫而又不可預測的命運是多么的無奈。以至于7歲時的他就用英語寫了第一篇關于古希臘神話的短文,又用西班牙語寫出他的第一個文學故事《致命的護眼罩》。而那些享譽文壇的孤獨的文學天才們:吉卜林,愛倫·坡,史蒂文森,切斯透頓,蕭伯納,喬伊斯……也幻化成無數靈光直透這位早熟的少年的心靈,鋪就了他日后輝煌而燦爛的文學人生。
1914年因要治療父親眼疾,博爾赫斯隨家人前往歐洲。在那里他掌握了法語,拉丁語,德語多種語言,使他可以直接通過原文來了解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及歐洲的文學藝術成就,得以飽覽人類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的異常豐富的精神典籍。使從小就熱愛寫作的他于文學創作技藝更是突飛猛進,同時也確定了其終其一生不悔不變的事業。在《詩的藝術》中他這樣表現自己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傳說飽經艱險奇遇的尤利西斯/見到蔥郁質樸的伊大卡竟深情慟哭/藝術就是伊大卡,永恒蔥郁/不是艱險奇遇。”“詩還像河流,無窮無盡/是赫拉克利特常變的水晶/是它本身,可又不是/宛如奔騰不息的河流,終古常新。”
★超 越★
在博爾赫斯五六十歲的時候,他逐漸變成了一位盲人。但對這位智者而言在這喧擾的世界失去其浮華的外表前,他早已深得其中的奧秘。他早已不需要再茫然地睜大眼睛去看那蠅營狗茍的凡塵瑣事。對他而言這個堆積繁復表象的世界是否消失在眼前,也許已不再那么重要。他用其更高的智慧,更明凈的心靈去創造一個更為純潔和更打動人心的詩意的世界,愜意得能夠住在那里,享受心靈的寧靜。從那位唱著“世代如落葉”的人類第一詩人荷馬,到那被稱為是來自幻想的黑暗的音樂的《失樂園》和《復樂園》的著者的彌爾頓,再到以擅長制造迷宮以高超技藝將美學的表現手法與拉美的本土經驗完美結合的大師博爾赫斯。他們都用盲人獨有的心鏡和自己無窮的想象力給世人帶來了關于豪邁、激昂、沉思的瑰麗畫面和深刻、永恒的思想魅力。
之后的日子,他一直從事圖書館工作,那里成了他終生棲息之地。雖然光明已不復見,但上帝還是仁慈的使他和書結下了永遠的不解之緣。大量涉獵的哲學、文學、歷史、神話使他對人類的文明進程了然于心,當它們緩緩流過心中之時,寫作的靈感也破殼而出,其作品中顯露出的奇思妙想和機智靈悟引起了拉美乃至世界的驚訝和關注。其間他也曾多次出國演講和講學獲得了各種榮譽和勛章。但無論多么精美,曾拉出過多么動聽旋律的名琴也終會被時間之弓無情的拉斷。1985年博爾赫斯因患癌癥并對阿根廷激進派政府的政策的極其不滿使得他永遠的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漂洋過海再度來到他少年時長久流連駐足的日內瓦,以和自己青春的時光作最后一次約會的方式作為與這個塵世的最后訣別。
★無 限★
博爾赫斯留下了他精湛的絕響,這天籟來自智慧,更來自無與倫比的才華。他最善長的題材——短篇小說,除了法國的梅里美、莫伯桑,俄國的契訶夫和美國的歐·亨利以外能與之相比的大概是寥若晨星了。而其深刻性在于它總能將迷宮、時間、死亡、虛無這些永恒的主題玩弄于股掌之間。
他的代表作之一《小徑分叉的花園》正是這些主題的最好注解。故事情節很簡單,他講述了一個名叫俞琛的中國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充當間諜。他偵察到英軍一處炮兵陣地,卻被發現而不得不倉皇出逃。乘火車來到一個小鎮,躲入一位叫史蒂芬·阿爾貝的博士家中。作者從這里引出了小徑分叉的花園。英軍趕到逮捕了俞琛,可軍事機密早已泄漏并傳到了柏林。其方法是:俞琛殺死了阿爾貝,消息立刻見報,德國情報機關因而馬上猜出阿爾貝是英軍炮兵陣地的名稱。德軍立刻派飛機轟炸了這個陣地。
但小說的主旨是介紹小徑分叉的花園,它的主體是時間,在此地時間是一座循環往復的迷宮,它充滿了變數與重復。是一張正在擴張、變化、分散、集中、平行的網。它的網線互相接近、交織、隔斷,這張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人徒勞地尋找出口,卻又正不斷浪費生命使之消逝在這樣一座迷宮中。同時人類創造了種種不朽的形式來戰勝死亡,用精神,用幻想,也用肉體來展示生活的秘密。而這些形式最后又不得不被最終的時間所消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時間借以顯示自己的明證。因而我們既是自己的起點也是自己的終點。而這部小說也因此成為了一部循環的書,它的第一頁和最后一頁沒有差別,使我們有了無限閱讀下去的可能性。
《阿萊夫》博爾赫斯的另一部代表作。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我”有一個女友,在她在世時曾去她們家拜訪,認識了她的詩人哥哥阿根蒂諾,當時他正在創作一首叫《大地》的長詩。很多年過去了,姑娘不幸去世,而他哥哥仍在年復一年的創作著這首長詩。一天他哥哥給“我”打電話說有人要拆房,但他絕不能容忍,因為那會毀了房間地下室的阿萊夫。他還解釋阿萊夫就是包含著一切點的空間的一個點。從而開始了對阿萊夫的描述:一個小光球……飽含著天地萬物……令“我”感到無限的憧憬,無限的凄涼。那么阿萊夫到底是什么呢?每一個讀者看完后大概都會有不同的結論。但作者的用意在于以其作為一與多,有限與無限,一瞬與永恒的復雜哲理象征物。它既是單一的又是復雜的,既是空間上的一個有限的點又可以將無限的宇宙不縮小的放在里面,既可以在某個瞬間看到它,又可以使這一瞬間成為無窮無盡的永恒。而這一切的過程又忽真忽假,或以假亂真。但經過認真地思考,最終你會理解到作者的宇宙人生觀,對博爾赫斯面對大千世界的悲哀與無奈的感受感同身受。
看完博爾赫斯的作品你大概會覺得他是故意建造一座通天塔迷宮,故意不想讓人讀懂其中任何一本書或一封信的含義,正如博爾赫斯所崇拜的愛倫·坡說過的,那“失卻的信件”最好的藏匿地是在偵探的鼻子底下。其實當你明了了他的邏輯與藝術思想來源后就不會有這樣的惶惑了。博爾赫斯對古老的文明有著無限地敬仰與崇拜使他骨子里是個懷舊主義者,但同時又接受了貝克萊的神秘主義,休謨的懷疑主義,叔本華的唯意志論使他具備了徹底的反叛精神。兩相碰撞,使他有能力站在超脫的高處以純凈的目光與心靈來審視人世的茫然、孤獨與虛無。從而也使他的作品擺脫了一般文人平庸的多愁善感,顯示出一種經過洗煉的達到巔峰狀態的透徹與超越平凡人生深入人類精神領域的無限妙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