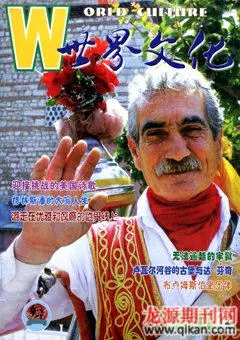墨西哥看海
七月,“流火”的日子,不是天上,是在心里。南美的熱浪四溢,讓人無處可逃。先生說:“去墨西哥看海吧。”
海的誘惑在我如“葉公”與“龍”,洶涌澎湃的情感多來自文字的激蕩和畫面的想象,真的去看它,倒有些怯意的萎縮。看家里的兩個男人已全副武裝,躊躇的我在最后一刻把自己也當作一件隨機的行李送上了云空。
墨西哥,近在咫尺卻如此陌生,就一直不能明白那拉丁音樂的歡快究竟是源于心靈的何方。但我認識不少墨西哥人,或在中餐館,或在馬路上割草,他們說自己是偷渡的,我就趕緊揮手:“德州本來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有世界上最浪漫的詩人帕斯,有世界上最痛苦的畫家芙烈達,但那都是個體生命的獨特表達,與整個民族的心理距離尚遠。去墨西哥的游人多喜歡在黃昏時分坐在早年瑪雅人的廢墟上,懷想那最后一道即將消逝的光芒。今天的墨西哥,眩惑的是色彩的熱鬧,張揚的是快樂的簡單,當然還有酒的及時行樂。
印象中加勒比海儼然是美國大戶人家的后花園。飛機落地,果然,一隊隊穿著花襯衫的美國人被綠色制服的墨西哥小伙子輕車熟路地引領著奔赴各家酒店。巴士車上,先發啤酒,然后收錢,濃郁的酒香立刻散在空氣里,讓人欣欣然。
我們的目的地坎昆,其實是在濱海深處的狹島。行駛間,看見有破陋的房屋對應著城堡式的酒店,一街之隔,卻是天壤。走進我們的洞天別墅,柜臺旁又看見酒,喝了兩杯,那酒力似乎要將人麻醉。
城堡靠著海,如詩如畫,來這里的人都是客居,只求盡情上天入海。翌晨,我隨人流攀上一艘駁船,海上的陽光亮得人瞇起眼。喜歡那桅桿,像是電影里的《鴿子號》,臆想著自己跟著老水手遠航。可惜那水手太年輕,航了不遠就揮手拋錨,叫大家下海去看珊瑚,這才感覺自己是見了“真龍”。坐在船舷邊看著波動的海水怔832a0237a115a1a4a221e30ef3c40c33eca333f3f735b5de6a9c8d0b38db4a80怔地發顫,是“跳”還是“不跳”?終于選擇了前者,結果發現此處的加勒比海原來是這樣的清淺,完全不如《泰坦尼克號》的那般深沉壯烈。
七月的海水依然是清冽冽,且直灌喉嚨,我浮在水面上,同情地看著海底的那些美麗魚兒,敢情它們喝著咸苦的水,卻游得如此自在。珊瑚雖美,但經不住鼻子嗆水、胃液倒流,體力開始不支,趕緊呼救,這才發現水手還是年輕些好,仰天長嘆的我,迅即被拉回到船上,人不是魚,所以不能享受魚的快樂。
下海過后,船上的水手忽然扯起了風帆,那彩色的帆在風中招展,竟如一面威武的戰旗,原來是讓船上的人隨著風帆的繩索冉冉升起。我等恐高絕不敢為,就悠然地看那一個個的身影在彩色的帆里搖曳著升騰再忽然墜下,歡騰與沮喪交錯,黝黑的墨西哥小伙兒掌控著每個人的高度,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竟看見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特別的快意。
海上歸來,小試牛刀的先生與小兒決計向海的深處進軍。他們扛起家伙,登上更大的船,開始了深海潛水的壯懷行動。那里的海據說有四十多尺深,幽暗神秘的海底實在讓他們很向往。后來看到錄像,一大一小兩個背著巨大氧氣罐的身影竟然漫步在大海之底的沙土上,成群的魚兒在身旁手舞足蹈,也著實叫我激動了一番。
愛海且懼海的我,終于發現真正迷戀的還是人的世界。于是,那個艷陽的午后,甩甩手坐上了去坎昆市區的長途汽車,以為是一場瀟灑的云游,誰知這一甩手,竟差點兒有去無回。
坎昆城的鬧市中央,街道交錯,完全看不出南北,我的“云游”就頗有些隨意地流竄。驀然就找到最愛的跳蚤市場,墨西哥人性情歡快,物品多艷色,裙衣多夸張,古樸的工藝品尤其讓人悅目,笨笨的陶罐、粗粗的木雕,大紅大綠卻不俗。喜歡墨西哥人的刺繡包,雖不是針腳精到,但毫無匠氣。因為天氣熱,不敢嘗墨西哥人露天做的夾肉玉米餅,看那路邊的小攤販將水果切成花瓣一樣的圖案,終于還是忍不住想吃的口水。
總忘記自己是在“外國”,每每聽熱情的墨西哥女人殷殷地用西班牙語為我指路,常常猜到相反的方向去。干脆乘島上的巴士走到路的盡頭,下車一望竟是童話里的海,那水綠得讓人傷感,天色藍得讓人流淚,腳下的沙子柔軟到心醉,絕色的加勒比海啊,難道正是你的美麗永遠地滿足了墨西哥人的心?
天色將暗,我駐足在十字交錯的街口,因為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歸路。尋覓到巴士的總站,面對售票的窗口卻怎么也說不出自己所來的那個靠海的小鎮。掏出城堡的門卡,上面既無地址也無電話,各方交涉了半天幾近絕望,情急之中,忽然翻出了來時的那張未及丟棄的單程車票,只聽售票的女子“啊”的一聲喊道:“Playa Del Carmen!”我得救了!
容易迷路的我不再出行,做童話里的漁夫,躺在城堡酒店的水畔讀書遐想。打開餐廳朝海的一扇窗,海風就吹進來,幫我翻閱著桌上的書頁,浸潤著手邊的木瓜果香。書讀累了,再去泳池的吧臺要酒,花花綠綠的看不懂,就由著侍者把酒調成最漂亮的雞尾顏色。墨西哥的酒多烈,一杯下去就暈暈然渴望長眠不醒,只能躺在長椅上,用毛巾蓋了頭睡去,直到黃昏的海風把自己吹到酒醒。
浮生偷閑,南柯一夢,才想起拜倫的詩:“我不是不愛人,但我更愛大自然。”原來自然竟是比人高貴的,因為它比人更純凈更永恒,所謂海枯石爛,人早就灰飛煙滅了。
飛機上回望加勒比海,想那早年的殖民者,除了掠奪,給這片土地留下的僅僅是異國的語言和血脈,卻沒有留下出征大海的野心和夢想,究竟是幸還是不幸?絕世的美景,滯后的文明,究竟是夢想還是惆悵?過客如我,迷思在永遠也看不清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