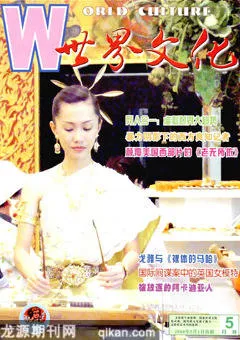奧古斯丁:基督教史學的先行者

羅馬帝國晚期動蕩不安,蠻族入侵勢不可擋,生于亂世之中的蕓蕓眾生渴望獲得精神家園。于是,早已在帝國境內(nèi)根深葉茂的基督教會借此天賜良機,在宗教領(lǐng)域和現(xiàn)世生活占據(jù)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帝國晚期涌現(xiàn)出來的基督教精神領(lǐng)袖,不再是跡近傳說的不辭辛勞傳教的圣使徒,而是一批著書立說、言傳身教的教會神學家。
這些人包括拉克坦提烏斯、安布羅斯、圣杰羅姆和奧古斯丁等人,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奧古斯丁。奧古斯丁的地位,從13世紀圣多明我修會會長約爾丹書信的結(jié)語可見一斑:“請您向您的那些姐妹致意,愿她們遵照我們圣徒教父奧古斯丁的教誨……”奧古斯丁究竟何許人也?到底有什么卓爾不凡的貢獻?
奧古斯丁于公元354年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今阿爾及利亞境內(nèi))。父親是一位小官吏,信奉多神教。此人一生雖略有積蓄但為人懶惰,貪圖世俗享受,直到臨終時才勉強信主受洗。而奧古斯丁的母親則是一位堅定而忠誠的基督教徒。她很關(guān)心兒子的前程,每天為他在神的面前禱告并經(jīng)常淚流滿面,同時她也身體力行的實踐著對上帝的虔誠。也許是受到父母雙方這些極具反差品性的雙重影響,奧古斯丁從小就兼具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性情,一種是在欲望之中追求放縱,另一種則是對真理不懈的矢志不渝。奧古斯丁的心靈深處也必然成了善與惡斗爭的戰(zhàn)場。
奧古斯丁17歲時,母親為磨煉他的意志品質(zhì)而送他外出求學。他幾經(jīng)輾轉(zhuǎn)來到北非名城迦太基,在那里悉心學習修辭學。奧古斯丁的最初理想是成為一名雄辯家,但他不久結(jié)識當?shù)匾幻倥⒀杆傧萑霟釕伲瑥拇藘扇碎_始長達14年的同居生活。19歲那年,他接觸到西塞羅的著作,從此樹立終生追求真理的信念。此時他開始轉(zhuǎn)向以思想混合二元主義為基本理念的摩尼教,追求心靈的安慰與解脫。奧古斯丁信奉摩尼教長達9年,在這期間他一面治學一面教書。但平淡的生活使善于思辨的他漸漸的開始懷疑這個教門理智上的效能。于是他前去拜見摩尼教的首領(lǐng)并提出了很多關(guān)于真理與人生的困惑。但教首在教理上的多處自相矛盾使得很多以前看似圓滿的理論變得難以自圓其說,這使得奧古斯丁在真理的追求上大失所望。公元384年,帶著對真理與人生的重重困惑,他遷居羅馬帝國西部的大都市——米蘭,并在當?shù)亟淌谛揶o學。在米蘭的日子里,奧古斯丁雖然聆聽了安波羅修大主教的布道,但真正吸引他的僅僅是主教雄辯的口才。而此時也是他一生之中道德水準最低的時期。奧古斯丁的母親為他訂了一門親事,于是他便與從前的情人脫離了關(guān)系,甚至拋棄了自己的親生骨肉。但由于訂婚的女子年紀尚輕而一時不能完婚,奧古斯丁再次過上放蕩生活,不久他就和米蘭當?shù)匾粋€有夫之婦攪在一起。
后來,他讀到新柏拉圖派的威克多林傳記,看見他在老年時如何皈依基督,不禁為之動容。因為他聽安波羅修的講道多了,所以對教會的權(quán)威也有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實之源。加上又聽到埃及的修道士之高尚圣潔的生活,奧古斯丁自慚形穢。因為他雖然立志追求真理,卻始終為情欲所俘虜。在悲痛自責之余,他奔向花園中去,伏在樹下痛哭。忽然之間大風驟起,花葉滿地,他仿佛聽到天空中的一個聲音說:“快拿起來讀吧!”奧古斯丁的面色大變,抑制著眼淚,拿起一本他所讀過的書信急忙翻開,視線隨即落在這段經(jīng)文之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自此以后,奧古斯丁內(nèi)心有了寧靜,他感覺有從上帝而來的力量戰(zhàn)勝了邪念,內(nèi)心發(fā)生了極大轉(zhuǎn)變。這些變化也最終落實到了奧古斯丁的行動之上。公元386年夏末,奧古斯丁離開情婦,辭去教職,退居到一所山莊,與其他修士共同研習哲學。公元387年的復活節(jié),奧古斯丁在米蘭受洗于大主教安波羅修,皈依了基督教。391年,他前往希波受職為神父,4年后又繼承主教一職。奧古斯丁在希波創(chuàng)建非洲第一所修道院,為教會培養(yǎng)了大批領(lǐng)袖人才。而他的余生則全部致力于牧養(yǎng)教會、宣講福音、救濟貧弱等事業(yè)上。為解決北非教會的各種爭端,他更不辭勞苦,幾度召開宗教會議。
在致力于傳播基督教之余,奧古斯丁筆耕不綴,撰寫大量書稿,全面闡述他對基督教的認識與理解。《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對中世紀神學史觀產(chǎn)生空前絕后的影響。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認為天地之間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即在天上的上帝之城與在人間的地上之城。上帝之城是由上帝主宰的天國與極樂世界,而地上之城則是由亞當?shù)膬鹤釉撾[所創(chuàng)造的凡塵之地。前者是至善的象征而后者則是極惡的代表。教會是上帝所一手創(chuàng)造,因此教會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了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它也就在兩城之間起到了名副其實的橋梁作用。教會的終極目標也就是竭盡全力的促使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而使上帝之城在人間實現(xiàn)。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之間就會不斷的發(fā)生斗爭,直到地上之城徹底消失為止。在這種背景下,整部人類歷史和整個世界歷史其實也就是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不斷斗爭的歷史,即善與惡之間持續(xù)斗爭的歷史。奧古斯丁在創(chuàng)作《上帝之城》之時,始終懷著與異教徒辯論的目的,假想與對方進行一對一爭論。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與宗教文化原因。公元410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領(lǐng)部眾一舉攻入羅馬城。雖然蠻族占領(lǐng)城市不到三日,但此事卻在羅馬的精神世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震動。盡管羅馬當時早已不再是皇帝常駐的首都,但它卻仍始終是羅馬文明的重要象征。在當時人看來,“永恒之城”的陷落難以置信,這件事情甚至意味著世界末日的臨近。而對于當時已經(jīng)在帝國之中取得特權(quán)地位的基督教來說,都城的陷落也意味深長。此時的羅馬帝國正走在基督教化的道路之上,十字架對多神教的節(jié)節(jié)勝利也使樂觀情緒彌漫在基督教徒中間。多數(shù)人都認為,正是基督教在造化著偉大的羅馬,羅馬將因基督教而更加昌盛。然而,“永恒之城”卻在公元410年遭到了這場劫難。抵制基督教的異教徒正好借此將羅馬的陷落視為基督教化的惡果。在他們看來,正是基督的到來取代了長久以來保護羅馬城的諸路神祗才造成了災難的降臨。因此,《上帝之城》正是奧古斯丁對這些責難的回答,同時也是其對羅馬危機進行理解的結(jié)果。在推演了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關(guān)系之后,奧古斯丁提出這個答案:羅馬城的陷落正是其建國以來種種罪惡的結(jié)果而非基督教的過錯。相反,基督教還減緩了入侵者那些殘暴的性格。
除《上帝之城》以外,《懺悔錄》、《論三位一體》等著作也集中的展現(xiàn)了奧古斯丁的神學觀和歷史觀。雖然奧古斯丁從未自覺地系統(tǒng)闡釋歷史思想,但中世紀基督教史學中宗教與歷史的嚴密捆綁也使我們必須承認,在為中世紀神學史觀定調(diào)方面奧古斯丁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奧古斯丁發(fā)展了歷史時間觀念,而歷史時間觀念的定型則決定了中世紀歷史寫作的基本形式。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史學家那里,時間沒有方向性,一直處于循環(huán)之中。而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則認為上帝“在一切時間之前,是一切時間的永恒創(chuàng)造者”。這就意味著在奧古斯丁的神學體系里,時間再也不是永恒的物質(zhì)。上帝在創(chuàng)世紀之時賦予世界以生命,同時也賦予生命以時間,時間初始于人類世界的誕生。在末日審判之后,世界即將消失,依存于物質(zhì)世界而存在的一切也都會在那一瞬間灰飛煙滅,因此被賦予在生命之上的時間也會隨之消逝。在后來的阿非利加那與尤希比烏斯那里,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其歷史的記載就始于創(chuàng)世紀。可以說奧古斯丁對于人類歷史時間的闡釋已經(jīng)為中世紀的神學歷史編織出了一個基本的時間框架。
在《上帝之城》中我們也看到,奧古斯丁將人類歷史的起點定為該隱創(chuàng)造地上之城之時,這一時期則充滿惡與暗。而人類歷史的終結(jié)也就是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之時,那時則必將充滿著善與明。同時,在他的另一著作《論三位一體》中,奧古斯丁還將兩城的斗爭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前律法階段、律法階段與上帝的天國階段。在這之中,奧古斯丁為后世的史家奠定了神學的進步史觀與歷史分期觀念的基礎(chǔ)。而在此之前,古希臘羅馬歷史學家的史觀都是悲觀的歷史循環(huán)論。比如,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就提出過典型的歷史循環(huán)倒退論,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周而復始。直至近代,在歷史學家的意識之中,奧古斯丁所確立的那種歷史進步思想仍然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
奧古斯丁寫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就是為基督教與神學辯護,其整個解釋系統(tǒng)都是為了論證上帝與基督教的合理性,帶有強烈的宿命論與目的論色彩。但這種寫作范式與價值取向卻為之后中世紀的其他神學史家所繼承并發(fā)展,成為這些史家撰寫歷史的根本目的。雖然中世紀的神學史觀在當代飽受批判,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作為其重要奠基人的奧古斯丁對歷史學的影響延續(xù)了千年。
奧古斯丁以其一生的思想變化生動演繹了他對上帝的虔誠,為整個中世紀的基督教會樹立了行為的楷模。同時,他的神學思想也為中世紀的神學歷史觀奠定了主要的基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