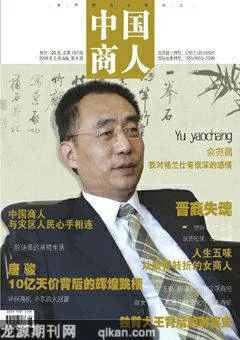淑女學堂:教授傳統文化中創造商機

這是一個每天都在變化的世界,著裝在變,建筑在變,城市在變,觀念也在變。蘇州有個叫南林苑的地方,在外人看來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居民區,可這里卻發生著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這個小區里生活著一群古代裝束的女子,乍一看比拍古裝劇還有范兒,這些女孩舉止溫婉,每天的學習任務就是練習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她們奇怪的舉動和小區里的正常生活顯得格格不入,讓生活在這里的居民摸不著頭腦。
穿著漢服上課的女子
原來,小區里開辦了一所私人學校,這些打扮成古代女子的女孩都是這里的學生。這個學校自創辦以來生源漸增,這與它獨特的優勢分不開:到這里來,人們浮躁的心容易變得很平靜;到這里來,行為舉止會變得溫柔一點,優雅一點;到這里來,可以學習道德經、論語和唐詩、宋詞等古典文學;到這里來,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古代才女在現代社會同樣有很大市場。很多學生被這所學校的魅力所折服。
學生所穿的漢服本身質地飄逸,穿上以后就有點飄飄欲仙回到古代的那種感覺,所以為了更加真實地生活在“古代”,學校還規定:不準大步走路啊、不準高聲說話、不準握手等,最奇怪的就是不準收年輕的男子當學生。
說出這個奇怪規定的人本身就是個小伙子,不過他不是學生,而是這所私塾的創辦人,名叫傅奇,字正之,號鳴鹿。他為私塾起了個特別的名字——“淑女學堂”。
至于為什么不招年輕的男學生時,傅奇解釋為:“這些女孩形象氣質都比較好,可經過媒體報道的夸張渲染,很多人就誤以為淑女學堂的女生全部都是美女,我們擔心一些男孩來學習目的不純,打著學習傳統文化的旗號,實則想交女朋友談戀愛。”
傅奇自稱是淑女學堂的堂主,他拒收男學生是不想破壞了這片清靜之地,“在里面學習時,心情一定要很安靜,詩情畫意的,如果有一個男士闖進了她們的生活,打亂了她們內心的安定,學習效率就會大大折扣。”
這是一所奇怪的學校,一群奇怪的女子,還有一個思想怪異的堂主。說來有趣,傅奇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帶有一些傳奇色彩。
孩子不愛學傳統文化
傅奇是河南商丘人,大學讀了三個月就退學了。由于他非常喜歡傳統文化,2001年就在開封開了個“子曰”書店,專門賣中國歷史文學的經典著作。
蘇州一直是傅奇魂牽夢繞的地方,2004年傅奇第一次來到蘇州,就深深地愛上了這片土地,“那次是來蘇州旅游,第一次看到寒山寺,腦子里立刻蹦出張繼的《楓橋夜泊》那首詩,詩里面描寫的場景好像就在眼前,那一刻,我想這個城市是屬于我的。”
傅奇下決心要留在這個城市,然后就從開封義無反顧地到了蘇州。在蘇州生活的每時每刻,傅奇就像穿越了時空,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文學作品一一出現在他的腦海里,書中描繪的小橋、流水、人家的美景,非常清晰地矗立在傅奇的眼前。
傅奇留在了蘇州打工,但是工作一直不盡如人意。突然有一天,傅奇在網上看到了一則新聞,正是這則消息改變了傅奇的命運。
傅奇回憶道:“媒體報道說中國的私塾經過2500年的跨度退出了歷史舞臺。當時心里特別遺憾,莫名其妙的難受。”
這則網絡新聞點燃了傅奇的斗志,他向朋友借了幾萬塊錢,幾天的工夫就辦起了一個自己的私人學校。可傅奇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蘇州創業的第一步就栽了個大跟頭。
傅奇的私塾一開始只是招收小孩子,可是來報名的寥寥無幾。現在的孩子都被家長送去學習舞蹈、外語等課程,傳統文化沒能引起他們太大的興趣。
費盡力氣,傅奇的班上只有十幾個孩子上課。眼看他借來的幾萬塊錢都要賠了進去,此時的傅奇找不到出路。突然有一天,有一個女孩子來學堂買少兒讀本的四書五經,看到學堂整個的環境和學習氣氛十分喜愛,便極力要求和五六歲的孩子一同上課,學習傳統文化。她的做法一下子觸碰到了傅奇的心。
傅奇觀察到,這么虔誠的、想學知識的女孩不是一兩個,市場的需求人群得重新定位。有了這樣一個念頭,傅奇心里開始盤算,既然有這么多的女孩想來聽課,何不辦一個淑女學堂來教她們?
淑女學堂找淑女
雖說這是傅奇的突發奇想,但這個想法還是有現實基礎的。蘇州是個經濟發達、生活富足的城市,又是吳文化的發源地,很多外國人都來這里投資、生活,當中西文化在蘇州交匯的時候,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化和藝術再一次彰顯了它的魅力。通過傳統文化的學習來提高自己的修養成為了蘇州乃至周邊地區人們所追求的一種新風尚。

“女孩子的內心里面還是很向往淑女狀態的,堂主能用淑女學堂這個名字作為一個商機的切入點,我認為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有個學生翹起大拇指說道。
現如今,私立教育五花八門,但把淑女們集中到一起進行培訓的,傅奇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淑女學堂該怎么辦,他也是摸著石頭過河,腳底下沒譜。
一開始,傅奇每天都在網上瘋狂地尋找所有和淑女、漢文化有關的信息。找著找著,他突然想到,既然是辦淑女學堂,他就應該知道淑女該是什么樣?怎么才能變成一個淑女?所以辦學之前,必須先找淑女。
思路明確之后,目標也很快出現,“我經常上漢網,正好看到了傅奇發的一個關于他辦學的帖子,我就在后面跟了一個帖子說我正在找他。過了兩天他就給我打來電話,他說他也正在找我,彼此都覺得很有緣分。” 這個女孩子就是傅奇要找的淑女,她叫方芳,網名叫做天涯在小樓,是一個非常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的女孩。
第一次見面時,方芳穿了一套漢服,這讓從來沒有真正見過漢服的傅奇大開眼界,“衣服很漂亮、很好看,能給人以力量和感動,這種衣服就是我要的傳統。”
從方芳那里,傅奇了解到,在很多地方都有像她一樣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更有了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把自己要辦淑女學堂的想法告訴了方芳。
“因為她是一個女孩子,一個我認為已經很標準的淑女形象了,我就把起草的任務交給她,她果真很正確地表達出什么是淑女。”傅奇笑笑,慶幸自己沒看錯人。
為淑女開設古琴課
于是,方芳就按照自己的體會,給傅奇寫了一個淑女學堂的宣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載以來,美麗高雅、知書達理、善良恭謙的女子是男人心中一個無法釋懷的情結。想成為現代版的淑女嗎?來淑女學堂吧。”
一夜之間,傅奇的淑女學堂成了各大媒體的焦點,來私塾學習的女孩絡繹不絕。一開始傅奇只是給這些女孩子上一些古代典籍的學習課,可淑女們并不滿足只是讀讀詩,念念詞,她們要求開設琴棋書畫課。
學生提出這個要求是有一個原因,蘇州是古琴的故鄉,古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的地位很高,秀才四藝,琴棋書畫,琴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古代的文化人里,琴是他們必修的一樣東西。
可傅奇要想開設古琴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古琴雖然好,但是一個琴動輒要好幾萬,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練習琴也要七八千,如果要買琴投入就會很大,但沒有琴學生又不來學。”傅奇陷入兩難境地。
一把琴憋倒英雄漢,淑女學堂的第一門課就把雄心勃勃的傅奇難倒了。如果這第一門課開不起來,傅奇算是前功盡棄了。
全世界會做古琴的人不超過100個,所以古琴的價格十分昂貴。為了能夠開古琴課留住學生,傅奇單槍匹馬跑到廈門去找做琴的名家借琴。
一開始,傅奇把話題放在自己的淑女學堂上,壓根就不談借琴的事情。等對方所有的興趣都放到這個學堂的時候,再開口說借琴的事,并且向對方保證借用的同時還幫助代賣。一聽說傅奇辦了一個這么有創意的學堂,來學習的人正是自己的消費對象,于是對方很痛快地答應了傅奇的請求。
發聘書聘請民間古琴專家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古琴有了,可老師在哪兒?傅奇對古琴一點也不了解,學習古琴的人也都隱藏在民間。突然有一天,傅奇聽說有一位工廠退下來的技術廠長精通古琴,他眼前一亮趕緊和朋友一起去請老師。
“這個老師來源于古琴世家,我特意發了個聘書誠心聘請他來我們私塾傳授琴道,然后他很開心地同意了。”傅奇興奮地說道。
“我彈琴是家傳的,自己彈著玩,要教琴基本上也都是在家里教,在外面基本上沒教過。” 古琴老師吳同光坦言。
傅奇的淑女學堂,讓這位從來沒有出過山的老先生欣然接受了邀請,也受到很多感動,“我是5月份過去的,后來天氣慢慢變熱,那時候學堂還沒裝空調,可大家還是汗流浹背地堅持學習。另外,彈古琴的過程中手會很疼,特別是左手的大拇指,有幾個女孩彈到最后手上都起泡了,可她們還在堅持學習,確實不簡單。”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聽到老師彈陽關三疊,有一個學生就唱著陽關三疊,畫面非常美,那一刻真的就像回到了古代,就像看到了我們傳統中的詩情畫意,很感動,這才是真正的曲子,真正的音樂。”傅奇陶醉地說道。
由于古琴的價格昂貴,而且精通古琴的老師非常少,所以淑女學堂開設的古琴課,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第一批學員。慢慢地,傅奇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自助式的經營模式,每節課的學費是50塊錢,學員只要交夠一門課的學費就可以免費學習其他科目。學堂提供相應的學習工具,這樣傅奇通過小小的優惠政策一下子盤活了淑女學堂的所有教學科目。
淑女學堂的男弟子
古琴課成了淑女學堂的招牌,只要是來這里學琴都可以免費用琴,還有專人輔導。所以來學堂學琴的淑女源源不斷。突然有一天,一個叫狄碧云的學生找到傅奇,希望能到淑女學堂來學習,光聽名字狄碧云,傅奇以為是個女孩,見面后才知道是名字誤導了,其實是個男孩,淑女學堂從來都沒有收過男弟子,所以傅奇沒有同意接收這名男子。
狄碧云也不放棄,找了傅奇好幾次,堅持要到淑女學堂來學習古琴。最后,傅奇心軟了。
原來傅奇雖然把話說得很明白,淑女學堂是不會收男學生的。但是,狄碧云卻是撞了南墻也不回頭,非來學不可。一來二去,兩個人竟然成了好朋友。
傅奇想明白了,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中國人的東西,不光是淑女才可以學習,眼前的這個小伙子忠厚老實,又是這么地熱愛古琴,傅奇決定收下這個男學生。
狄碧云異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因為我那兒沒有直達的公交車過來,必須走過200米到另一個站去坐車,三四十分鐘后才能到學堂。過來。剛開始是晚上的課,常常趕不上那趟車,我就會倒車回家。”
有了一個狄碧云,傅奇的淑女學堂又接二連三地收了好幾個男弟子。他們也和淑女們一樣,認真地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歷經了幾千年的洗禮,有些人認為其中的一些東西已經不合時宜,應該退出歷史舞臺,可就在這個時候,傅奇卻把它們變成了新的時尚。一個淑女學堂,讓中國的傳統文化再次煥發了新的光彩。正是他的一個創意讓這么多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的人聚到一起,與此同時也收獲了一份自己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