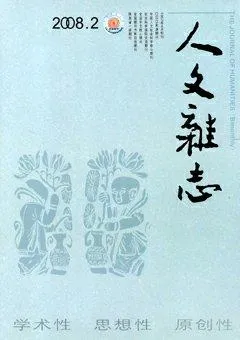子思學派仁義內外說辨析
內容提要:郭店楚簡中有大量儒家簡,其中的“仁內義外”之說引起了理解分歧。本文結合《中庸》及郭店《五行》篇的相關內容,闡述了子思學派仁義內外說的獨特內涵與哲學意義,認為仁義從根源上說是天命于人的內在本性,為人性之內涵與本質;但從人倫的角度講,仁義則是“教”之內容,是表現(xiàn)于外的道德行為與規(guī)范。
關鍵詞 子思學派 仁 義 《中庸》 《五行》
〔中圖分類號〕B2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8)02-0028-05
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簡中有大量儒家簡,其中多有仁義之論,且多次出現(xiàn)“仁內義外”的記載,例如:
“仁,內也。義,外也。禮樂,共也。內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門內之治仁掩義,門外之治義斬仁。”(注:本文所引郭店楚簡內容均依據(jù)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以下不再作注。)(《六德》)
仁生于人,義生于道。或生于內,或生于外。(《語叢一》)
仁形于內謂之德之行,不形于內謂之行。義形于內謂之德之行,不形于內謂之行。(《五行》)
這些“仁內義外”的說法出現(xiàn)在不同的篇章中,其意義也不盡相同。王博在《論“仁內義外” 》一文(注:王博:《論“仁內義外”》,《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中,把戰(zhàn)國時期思想家們所討論的“仁內義外”說分為三種意義不同的觀點,并對各自的內涵做了分析。筆者贊同王博先生這一分別討論的方法,因為仁義內外的討論實質上是關于人性善惡問題的爭論,其指向則是建立自律道德還是他律道德的倫理實踐問題。所以,只有對不同文本中出現(xiàn)的仁義內外之說做具體的分析,才能明確其立論的目的和根本哲學主張。如前所述,郭店簡中關于仁義內外眾說紛紜的現(xiàn)象,給學者們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但筆者認為不加分析地直接把子思學派的仁義之說等同于告子的“仁內義外”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認為《中庸》系子思學派的著作(注: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02頁。),郭店《五行》篇也被視為與子思學派相關(注:
參見郭齊勇:《郭店楚簡<五行>的身心觀與道德論》,收入郭齊勇著《儒學與儒學史新論》,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本文以《中庸》與《五行》篇為代表,試對子思學派仁義內外之說作一辨析,以明確它不同于告子“仁內義外”思想的獨特內涵與意義。
一、“性”與“天道”的契接
儒家早期“仁義”思想到孟子時才得以真正形成,其內涵及相互關系也得到了明確與統(tǒng)一。那么在與孟子思想有承繼關系的子思學派那里,仁義的內涵與關系是如何的呢?部分學者吸收分析了郭店楚簡中的仁義思想,認為儒家在孟子以前有告子所持的“仁內義外”說。這種觀點認為,孔子仁禮并舉,已有了“仁內義外”的思想傾向,子思學派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仁內義外”說,此說發(fā)展到告子時以極端的形式將其內在矛盾揭示出來,到孟子,仁義之間的內外關系才完全消融,二者皆根于心,形成了“仁義”思想(注:見梁濤:《孟子的“仁義內在”說》,《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4期;劉豐:《從郭店楚簡看儒家的“仁內義外”說》,《湖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2期。)。
針對上述觀點,筆者認為,儒家仁義思想的確經歷了從內到外的發(fā)展歷程,由仁與義的分別走向二者的結合與統(tǒng)一。然考察仁義思想的形成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從孔子仁學思想的提出,到子思學派性與天道的契接,再到孟子“仁義”思想的形成,其中有一以貫之的理論線索與發(fā)展脈絡。立足于儒學發(fā)展的脈絡,我們可以明確分別出子思學派仁義內外討論與告子仁內義外說的實質不同。儒家“仁義內外”的討論實質上關涉到了“性與天道”的問題,它體現(xiàn)了孔子之后儒家為道德倫理尋找根據(jù)的努力。因此,筆者認為在研究子思學派仁義思想之前,對其性與天道思想作一研究是必需的。
“性與天道”的問題,實即概括了孔孟之學從內到外的全部內容(注:李景林:《教養(yǎng)的本原——哲學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頁。)。在繼承傳統(tǒng)的“天”、“天道”與“天命”等觀念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仁”的學說,認為“為仁由己”(《論語?顏淵》)(注:本文所引《論語》《中庸》等內容,均以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版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據(jù)。),“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孔子把人之為人的道德性扎根于人自身,高揚人的主體性,認為內在于人的“仁”是道德實踐的根據(jù)與動力,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內在條件。而在孔子的觀念中,“天”、“天道” 或“天命” 還是一高高在上的道德存在,是最高的道德裁判者。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R26;雍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在孔子看來,人的行為總是逃不脫無形無象的道德之“天”的評判與賞罰,人要對“天”持有戒慎虔謹?shù)木次芬庾R。在這種戒慎虔謹?shù)木次芬庾R中,人展開了無限的“下學上達”之路,以期獲得天的認同與肯定。通過無限地“下學上達”的求仁功夫,人最終能夠實現(xiàn)對天道的認識,與天道同一。同樣人也就是在這樣的“下學上達”中,最終體認到“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人的道德來源乃在于“天”,人與“天”本是一體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所知的,也許只是其個體生命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中庸》第三十二章)的默識、契接中,體證了“天道”的內涵、“人性”與“天道”的同一。然而,正如子貢所感嘆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孔子很少談及“性”與“天道”的關系。“天”雖與我同體,但還是超越于我,高高在上,人只能“遙契之”,“默識之”,“敬畏之” (注: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41頁。)。
《中庸》從性命天道的高度繼承發(fā)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明確以“天命”規(guī)定“人性”,從理論上實現(xiàn)了性與天道的統(tǒng)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中庸》全篇的總綱與宗旨。“天命之謂性”,是繼承、發(fā)展孔子仁學思想的直接表達。《中庸》把孔子景仰的超越之天與人性等同了,天命就是人性。講“性”,即是著重于“天命”、“天道”落實、內在于血氣心知的自然生命中;講“天命”、“天道”,則是指自然血氣生命中超越的道德存在。講“性”,即是以“人性”詮釋“天命”;講“天命”,則是以客觀“天道”規(guī)定“人性”,“性”與“天道”其實是二而一。性與天道的合一,表達了“人性”的基本特征:人性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既具有客觀性,又具有主體性,是超越性與內在性、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tǒng)一。
“率性之謂道”就是天命之性的進一步落實與展開。朱子曰:“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注:〔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人遵循內在的天命之性,使之展現(xiàn)在具體生活的各方面,就形成了人道,“人道”即是“天命之性”的充分擴展與實現(xiàn)。“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作為“天之道”的“誠”,不僅是天道之實然的表征,同時亦為人道之應然的最本真的體現(xiàn)②③
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xiàn)代詮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1、83、54-56頁。)。《中庸》首章還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與開篇以天命規(guī)定人性比較,這里是落在人喜怒哀悲的具體生命中來談天道和人性的。
《中庸》從形上層面論證了性與天道一體的思想,彰顯了人道的內涵,指出人道根源于人性,是人性的擴展與實現(xiàn),其意旨在于表明天道之實然與人道之應然。但從實然層面看,人的天命之性是扎根于人的自然生命中的,這樣就必然受人與生俱來的血氣心知與喜怒哀悲之氣的局限與影響。由于自然氣稟的不同,人的天命之性也就有不同程度的彰顯,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中庸》第二十章)。性雖為人命自于天的本然之善,內在于人的喜怒哀悲之情氣中,但卻是潛在而有待實現(xiàn)的,這就需要“教”來使其得以培養(yǎng)與實現(xiàn)。“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中庸》第二十章) 教亦即是“誠之”,是一動態(tài)的無限之過程,實質上教也就是人之道的真正內涵。“修道之謂教”(《中庸》第一章),人道的實現(xiàn)是一動態(tài)的無限過程,要通過外在的“教”與“習”來完成。通過教習,使德真正內在于心,由心而發(fā)。教所包含的正是人性的自我實現(xiàn),即將天所命于人的純然之性在具體的日常事務中得到實現(xiàn)
②。“教”的內容即是“禮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中庸》第二十章)通過外在的“禮樂刑政”之學習與規(guī)范,即使是愚弱之人,只要“擇善而固執(zhí)之”,最終都可以實現(xiàn)人道,回歸人的道德本性。“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峻極于天。優(yōu)優(yōu)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第二十六章)。圣人能洞察天地萬物之理,把命自于天的人性徹底展現(xiàn)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都是其天命之性的展現(xiàn),與天合一。因此追求人道的君子不僅要對其內在德性持有敬慎虔謹?shù)膽B(tài)度,而且更要博學而審問,溫故而知新,乾乾終日。只有在這樣的歷煉與學習中,才能實現(xiàn)人道,展現(xiàn)人的道德本性。《中庸》認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主張以人道來修身,修身即是修道,而修道則是以人之為人的“仁性”為其內容。因此“教”雖由外作,人身與人道的修為雖由外在的禮儀教化、道德實踐來實現(xiàn),但具體的仁義禮樂都是符合人性的,是順人性之仁而發(fā)的。這正說明了“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第十三章)。
綜上所述,《中庸》的人性理論是:從本體論的層面講,“天命”就是“人性”,二者是統(tǒng)一的。“天命”與“人性”的貫通與統(tǒng)一,即是人道的落實與實現(xiàn)。“人道”即是天道之實然與人性之應然,是人性與自然生命的結合,并在自然生命中的全面展開與實現(xiàn)。從現(xiàn)實道德實踐的層面講,人性是潛在而有待實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