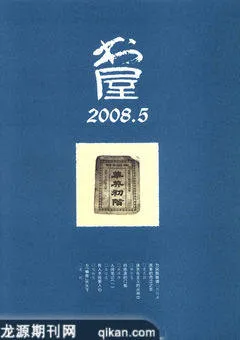與“偏房”共天下
《清稗類鈔》記錄了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一則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我們看郭氏所列舉的歷朝與君主“共天下”之人,絕大部分竟可以歸入隱權力者的行列,如西漢之外戚、東漢之太監、唐之后妃、元之番僧、明之宰相(實為內閣大學士)與太監,還有清之胥吏。在名分上,這些人并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只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系,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于正式的官僚系統而言,他們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
我們現在都說“皇權專制”,作為對歷史的宏觀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體情形而言,自漢代以降,除了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統攬朝政、乾綱獨斷的獨裁局面其實不多見,確如郭嵩燾所言:“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問題在于權力被誰所“分寄”。如果與宰相共治天下,則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因為從道理上說,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者與象征,“攬權不必親細務”,而宰相作為政府首腦,理當“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所謂“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是也。宰相的執政大權由制度賦予,為正統承認。如果君主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則被目為違制,“不由鳳閣鸞臺(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因此,對于“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權力分治格局,我認為是名正而言順的,正式的權力制度就是這么安排的;不正常的是“與外戚共天下”,因為外戚只是皇帝的私親,身份雖尊貴,但并無“總百官、平庶政”的正式權力,憑什么把持朝政?
在以宰相為首的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另立一個由隱權力者組成的“副權力系統”,始作俑者為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猜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系統,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的“外朝”撇在一邊。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并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
然而,或許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坐大之后,時間長了,可能會獲得名分的承認,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如常為外戚把據的大司馬,原來只是一個虛銜,并無印綬官屬,但至漢末已列為三公之首,位極人臣、權傾朝野。劉徹在世時盡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后,西漢終于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也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后,鑒于之前大司馬篡權之亂象,設“尚書臺”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臺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我們從字面上來理解,尚書不過是皇室秘書,協助皇帝整理文書而已,秩卑權微;但在西漢劉徹時代,因為皇帝倚重內朝,尚書權柄趨重;及至東漢劉秀時代,尚書發展為尚書臺,成為連接人主與臣下的唯一媒介,權勢更盛;到后來,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儼然已演變成半正式的權力中樞。
劉秀改組尚書臺與劉徹創建內朝,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而實現朝綱獨斷。后人評價“兩漢政出于二”,換成我們的話來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復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劉秀另設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又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劉秀留下來的權力結構未能阻止外戚對政權的篡奪,恰恰相反,到了東漢后期,外戚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臺,壟斷了朝政。而君主要奪回權柄,手法還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一個副權力系統,只不過扶植的對象換成了宦官。宦官得勢之后,又復擅權亂政。東漢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專政。所以郭嵩燾說,“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
郭氏提到的“名士”,還需要作簡略說明。這是指門閥世族,在東漢后期,門閥世族具有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世居高位,把據著權力系統的要害,包括尚書臺——此時的尚書臺,已不好說是副權力系統,尚書臺的首領“錄尚書事”也不好稱為隱權力者,相當于是“偏房”扶為“正室”了。而且,他們門生、故吏遍于天下,隱權力資源非常深厚。東漢皇帝之所以倚重宦官,目的也是想打擊這些樹大招風的門閥世族。
但最后的勝利方是后者,東漢天下被門閥世族瓜分、顛覆,中國從此進入近四百年之久的群氓時代,直至李淵建立大唐政權,才迎來一個較長時段的承平之世。郭嵩燾所指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大致可以安史之亂為界,戰亂前頻繁發生后妃預政,武則天還干脆做了女皇帝;戰亂后則出現藩鎮割據,最終導致大唐朝四分五裂。不過后妃預政與藩鎮割據,倒不是人主另立副權力系統取代正式權力系統的結果。因為后妃臨朝,雖是“牝雞司晨”,于名分不合,但只能說明皇權旁落,正式的官僚系統大體上還是如常運轉(當然,后妃因是政治“偏房”,難免有更器重“偏房”系統的傾向);至于藩鎮,本就是正式權力系統的一部分,只是后來尾大不掉。
但是,我們不能說唐代沒有出現“正室-偏房”的畸形權力結構。唐代的君主為限正式官僚系統之權,也另立“偏房”參預朝政——這個“偏房”就是宦官集團。宦官在李世民時代只是“門閣守御,廷內掃除,廩食而已”,但安史之亂后,君主因猜疑武將而寵信宦官,宦官不僅掌握內廷機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統,擔任政府要職。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個副權力系統來牽制正式權力系統,防止權柄下移,但是這個副權力系統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不僅架空正式權力系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其手中。因此,郭嵩燾的名句還需要補正:“唐與宦官共天下”。
相對而言,宋代的中央權力結構是歷代最合理的,國家權力的運轉也是最制度化的,沒有出現“偏房”得勢而“正室”失權的局面。許多學者都認為,與漢唐相比,宋代相權低落了,理由是宰相的權力被多個機構分割。這個看法其實不是很準確,就宰相個人而言,權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領的正式權力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其權力遠比前朝穩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與“偏房”的浸漁。
宋代是歷史上少見的沒有形成副權力系統的朝代,女寵、宦官、外戚、皇室秘書、幸臣等隱權力集團大體上都受到遏制。盡管當時也有太后垂簾聽政,那只是特殊情況下攝行皇權,并沒有出現一個鉗制外朝的內朝;對外戚則“養之以豐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對宦官也是規定“不典兵、不預政”。即使是貴為天下主權者的君主,對于政事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時人評價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雖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虛飾之言。我們可以舉一例證:內廷國手趙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職非皇室私器,隨便予人是有違政制的,因此趙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開恩。宋孝宗答復:“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讓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并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孝宗唯有一聲浩嘆:“書生難與他說話!”趙鄂因陪皇帝下棋,與孝宗關系極好,按說是頗有隱權力的,但宋代比較健康的權力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隱權力,連皇帝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破壞這個權力結構。我們看過漢唐的私臣亂政,會覺得宋代對正式權力系統的尊重,實為難能可貴。
郭嵩燾認為兩宋與奸臣、外國共天下。其實“奸臣”論比較勉強,哪個朝代沒有奸臣呢?更何況平心而論,北宋的奸臣比之前之后的朝代都要少得多。至于“外國”論,宋朝積弱,強敵環伺,的確不能不與西夏、遼、金、蒙古等政權共天下,不過這不屬本文所欲分析的權力結構范圍,不必細述。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說,宋代君主與何人共治天下,當時的政治精英已有精辟說法。宋熙寧四年三月,意欲變法的宋神宗召大臣議事,樞密使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需更張,以失人心。”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歷來是官僚系統的基石,“與士大夫治天下”之判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正式權力系統的穩固地位。
遺憾的是,趙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對正式權力系統保持尊重的權力格局不再出現。宋之后的元代是一個具有神權傾向的政權,喇嘛教被定為國教,皇帝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帝師體制造就了一個驕橫跋扈的隱權力集團——僧侶階層,他們不僅干預政事,連皇室成員也敢欺負。所以郭嵩燾才有“元與番僧共天下”的斷語。
把蒙古鐵騎逐回大漠的朱明政權,將國家權力結構改造得更加畸重畸輕——朱元璋為了實現大權獨攬,干脆廢掉了宰相,并詔令子孫:“以后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漢、唐的皇帝出于獨裁之目的,只是另立一個以隱權力集團為班底的副權力系統,借以掣肘、架空正式權力系統,形成“正室-偏房”的復式權力結構。朱元璋的做法更絕,相當于將“正室”廢了,皇帝躬攬庶政,國家主權者兼任政府首腦。然而政事繁重,又豈是皇帝一人所能對付?連精力過人的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明代君主選拔“輔臣”的做法還是效法前朝——借重隱權力集團,建立一個副權力系統。
明代的副權力系統由內閣學士與內廷太監組成。內閣學士與從前的“尚書”相似,本是皇帝的秘書,充“侍從左右,以備顧問”之職,秩五品,官階低,亦無甚正式權力。廢宰相之后,內閣成了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入值的大學士得以參預機務,為皇帝起草詔令、批復奏章,時稱“票擬”。嚴格來說,“票擬”只是一種隱權力,因為它并無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參考的意見,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筆抄正,時稱“朱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盡管如此,由于內閣學士是皇帝近寵,“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禮眷,殊于百辟”,這樣的隱權力是極容易轉換成炙手可熱的實際權勢的。所以后人說入閣辦事的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明代內閣也先后產生了幾名位極人臣的權臣,如嘉靖朝的嚴嵩、萬歷朝的張居正,史書說他們“赫然為真宰相”。
然而,內閣學士權柄再重,也終究是政治上的“偏房”,在名分上,他們并無制詔令、統朝政、領百僚的正式權力,與過去的宰相絕不可同日而語。清代皇帝乾隆就很不高興臣工將內閣學士稱為“相國”,特別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后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嚴嵩、張居正得勢時權傾朝野,但還是被后人批評為“怙寵行私,上竊朝廷之權,下侵六曹之職”,也就是說,內閣的“相權”是不被名分承認的,即使權焰熏天,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就如盜竊來的財產,別想獲得合法性。而大凡得勢的“偏房”,也總是比“正室”更擅長于權術,因為“偏房”們能夠掌握多大的權力,并不是取決于制度的規劃,而是高度依賴于私人的隱權力資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寵幸、太監的配合、羽黨的擁戴。嚴嵩要在朝廷上呼風喚雨,唯有絞盡腦汁為嘉靖皇帝寫“青詞”;后來徐階取代了嚴嵩地位,也是因為“青詞”寫得比嚴嵩好;張居正欲把持朝政,也不能不勾結司禮監太監馮保。
太監之所以成為權臣巴結的對象,是因為在明代的權力結構中太監處于要害位置。雖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靖難”事變之后,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統,任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遂成廢話。明中葉以后,皇帝又讓司禮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之權——這是因為明代廢了宰相,皇帝卻越來越不成器,沉迷于聲色犬馬,不理國政,只好將“朱批”的辛苦活計交給身邊的太監代勞,于是在明代的權力鏈條中,太監成了內閣學士的上線,“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即太監)”。繼東漢、晚唐之后,太監亂政集團這一沉睡多年的怪獸,又被明代的獨裁君王所喚醒,在失衡的權力系統中再一次張牙舞爪、咬牙切齒。但我們從名分上來看,不管是“赫然為真宰相”的閣臣,還是被諛為“九千歲”的太監,都屬于典型的“偏房”得寵,權力難以獲得正統的認可。對他們而言,人品與政聲如何姑且不論,權力本身就構成他們的“原罪”,權力越大,罪名也越大,終有一天要身敗名裂。
朱明政權滅亡后,其基本權力結構為清代所承習。清廷沒有再置宰相,繼續保留內閣體制,同時將內閣大學士的官階提至一品,并正式授予大學士“掌鈞國政,贊詔命,厘憲典,議大禮”的職責。換言之,明代的“偏房”如今已扶為“正室”,從前的副權力系統演化成正式權力系統了。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內閣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清代的君主在為內閣大學士追認名分的同時,又另外置立了一套副權力系統——先是康熙皇帝設“南書房”,隨后雍正皇帝在“南書房”基礎上創建“軍機處”。嚴格地說,“軍機處”只是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門,不配置府衙,也不設正式職官,臣工只是以“值日”、“兼職”的形式供皇帝顧問。也就是說,軍機處大臣盡管參預機務,權柄極重,但皇帝并不打算賦予其正式的宰輔之權,他們的預政大權只能說是一種沒有名分的隱權力。我們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現:借重隱權力來鉗制和取代正式權力系統,正是歷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為了使官僚集團更便于控制,明清兩季的皇帝在選拔與任用官僚上還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比如對“八股文”的強制推行,對文牘形式主義的高度講究。獨裁的君主不希望出現一個自作聰明的官僚系統,所以用僵化的標準不斷銼去官員的靈性與智力。反智政策的長期效應在晚清明顯地顯示了出來——官僚集團越來越昏庸無能、權力運行越來越程式化。《清稗類鈔》記載,清代的中央各部,“每辦一案,堂官(行政長官)委之司官(屬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看,并不需要太發達的大腦,就可以完成政務的流水線作業。只是如此一來,處于權力鏈條最低端的書吏卻得到了竊柄自重、挾律行私的可乘之機。書吏,又稱胥吏,指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處理文書的辦事員,不屬于正式的國家干部,流品極卑,但是僵化的權力系統給了他們上下其手之便,于是書吏也能作威作福,使人不能不畏,以致“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卿貳督撫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甚至“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所以晚清封疆大吏胡林翼干脆說:“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此言恰好拿來作郭氏“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論的注腳。
現在我們回頭來看,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制約的當然不可能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復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系統,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范性、程序性的規制,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制也越大。如果我們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權欲旺盛的雄猜之主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于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系統,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縱。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復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了獨裁權力。后來的君主為了“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復另設一個易于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歷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復發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著“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復雜管道的權力盡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布,但也顛覆性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線,并且受到程序性與規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看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后來內朝的大司馬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閑置,借重尚書臺,但尚書臺的領袖最后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制也培養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只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么歷代一再發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只是他們缺乏歷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后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