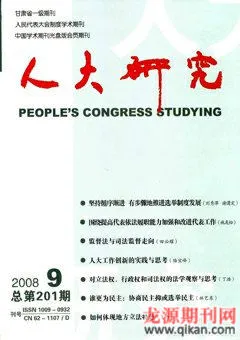內地與香港管轄權沖突協議應經過人大表決程序
內地和香港雖然屬于同一主權國家,但卻分屬于不同的法域。隨著兩地民商事交往日漸增多,民事訴訟管轄權的沖突及其解決問題開始引起法學界的廣泛關注。由于兩地在民商事法領域沒有共同的立法機關和最高司法機關,所以無法直接通過統一沖突法或統一實體法的方式解決管轄權沖突[1]。內地和香港相繼簽署的《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的安排》(1998年12月)、《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1999年6月)和《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2006年7月)三項司法協助安排的有效實施充分說明,運用區際協議的方法解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管轄權沖突應該是在現行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一種可行又可取的方法。上述三項司法協助安排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內地與港方進行協商,并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發布后在內地實施的。今后在簽訂和實施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是否也可以采取這一方式?是否需要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介入?如果需要,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應該如何分工?本文就從法律依據、效力等級和實施方式三個方面對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簽訂和實施中的這幾個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一、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的法律依據
與現行的三項司法協助安排的法律依據相同,內地與香港為民事訴訟管轄權沖突簽訂區際協議也應該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系和相互提供協助”這一規定作為法律依據。該法律條文中的內地“其他地區”應指內地省級地區,但是如果由省級地區的高級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分別進行協商和簽署協議,一方面會使協商較為繁瑣,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出現內地各省級地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協商的結果不一致,仍然難有統一的效果[2]。所以應該采取簽署三項司法協助安排時的做法,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擔任內地的代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協商并簽訂協議。
二、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的效力等級
在內地,國際條約和國際協定在國內適用時是有效力等級的。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準的,均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力——低于憲法和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凡由國務院締結的,而不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準的,均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低于憲法、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3]。但迄今為止,我國法律尚沒有明文規定區際協議在國內的適用問題,亦未作出參照國際條約適用的準用性規定。從法律淵源來看,在目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體系中,區際協議還沒有其應有的位置,本質上還不是任何形式的法律,因而在這兩個法域的內部沒有直接適用的效力,無法對抗內地法與香港法規定[4]。
三、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的實施方式
區際協議只有在通過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分別被內地和香港的法律接受后才能在各法域產生對內效力。那么,未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簽署了解決管轄權沖突的區際協議后,應該以怎樣的程序和方式在內地實施?
1. 能否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公布?
有學者認為,跟現行三項司法協助安排一樣,民事管轄權沖突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內地與特別行政區政府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發布,在內地實施;香港特區由立法機關修改或制定相關的法例的方式得以實施[5]。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未來兩地關于管轄權沖突的區際協議在內地的實施方式不可以套用現行三項司法協助安排的做法,因為兩者的性質明顯不同。司法協助,除去國家主權因素之外,主要是法院之間代對方為一定的行為,只涉及法院自身的活動,對當事人并無不利影響,因而最高法院將這種司法協助安排作為對《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并無太大問題。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就民事管轄權問題達成協議,必將與內地現行法律的規定有很大不同,以至于超出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所能涵蓋的范圍,所以不宜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公布。而且區際民事管轄權沖突協議屬于對民事主體權利義務關系有很大影響的事項,同時也屬于我國《立法法》第八條所明確規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有關訴訟和仲裁制度的事項,所以理所當然應該經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表決程序。
2. 是作為法律而通過,還是作為準條約來批準?
國際條約在國內的適用,我國傾向于直接納入的做法[6],在國內直接適用,無需再通過國內立法使之轉變為國內法。但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與國際條約不同,必須經過立法程序轉化為內地的法律才能在內地法域范圍內發生效力。也就是說為了使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得以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應該通過立法程序將其作為法律通過,而不是作為準條約來批準。如果只是以批準條約的方式批準了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它的性質仍然是未經轉化的區際協議,仍然無法對抗內地的各種位階的法律。區際管轄權沖突協議在適用上必須經過立法程序的轉化,這并不是出于壟斷立法權的需要,而是由區際協議本身固有的缺陷所決定的。
注釋:
[1][2][5] 胡宜奎:《內地與香港民事訴訟管轄權的沖突及解決方法》,載《江淮論壇》2004 年第1期。
[3] 張乃根:《重視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的研究》,載《政治與法律》1999年第3期。
[4] 慕亞平、林昊:《防范“溢出效應”——探析CEPA中“香港公司”定義難題》,載《國際貿易》2003年第11期。
[6] 王鐵崖:《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頁。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