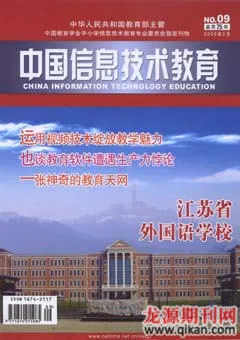圖靈測試能證實人工智能的存在嗎
圖靈測試是機器是否具有智能的重要標志之一,它最早被英國科學家、人工智能主要奠基人圖靈(1912~1954)提出。在信息技術必修教材中的人工智能部分不但被提及,而且給出了一些可以對話的機器人,讓學生通過與計算機的對話并尋找其中的破綻來感受人工智能的存在,例如機器人ELIZA等(http://www-ai.ijs.si/eliza.html)。人工智能是20世紀的新興學科,也是當今的前沿學科,關于“機器能否思維”以及“機器能否具有智能”這樣的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作為機器是否具有智能的重要標準——圖靈測試自然承載了人們更多的期望與質疑。下面,就讓我們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重溫人們對圖靈測試以及人工智能探尋的經典歷程。
■ 圖靈測試的提出:機器能思維
1950年,圖靈在《思維》雜志發表了奠定了人工智能理論基礎的著名論文《計算機與智能》,文章中提出了“圖靈測試”,認為判斷一臺計算機是否具有智能可以通過圖靈測試來檢驗。所謂圖靈測試,簡單說來,就是讓一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分別與一個人和一臺計算機進行問答,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如5分鐘內),他無法分辨與他交流的對象是人還是計算機,那么這臺計算機就可以被認為是能思維的,即具有智能的。圖靈并且預言,在20世紀末,將會有30%以上的計算機通過圖靈測試,人與計算機可以自由交談。
■ 維特根斯坦:機器不能思維

最早對“機器能思維”這一觀點持堅決反對態度的是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的維特根斯坦(1889~1951)。雖然他的大部分生命歷程是在計算機問世之前,但維特根斯坦對機器思維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深刻的思考。在他用自己生命最后16年時間完成的空前杰作《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就明確指出:機器不能思維。他的理由是:思維是生命現象,說“機器在思維”是無意義的,雖然計算機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它無法理解這些行為的意義,這不屬于思維的范疇,他舉例說,當機器停機時,可以說它在思考或者沉思嗎?
■ 塞爾:中文屋子

1980年,當代美國哲學家塞爾提出了著名的中文屋子假想實驗,以回應圖靈測試。他假定了如下情節:一個名叫丹瑪的人被關在一間只有一個窗戶的屋子里,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而看守她的人則只懂中文,不懂英文。丹瑪面前有一張桌子和各式各樣的紙條,以及一本英文寫的規則書,規則書告訴她如何為中文字符配對。如看守遞進的紙條上寫有“甲”時,她應當送出“乙”。對于丹瑪來說,“甲”和“乙”都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圖形,而對于看守,“甲”與“乙”都有其自身的含義,并且對于從窗口遞進的問題,丹瑪都已經將答案遞出。因此,看守認為屋子里的丹瑪是懂中文的,而丹瑪則對中文一無所知,她所做的只不過是按照規則書進行圖形匹配而已。
塞爾的中文屋子比喻了通過圖靈測試的計算機。丹瑪相當于計算機中的CPU,那本英文寫的規則書則相當于程序,紙條是存儲器,窗口則是輸入輸出裝置。丹瑪雖然給出了正確答案(通過了圖靈測試),但是她對那些問題卻毫無理解。中文屋子假想實驗表明,用圖靈測試來定義人工智能的存在是遠遠不夠的。
■ 彭羅斯:皇帝新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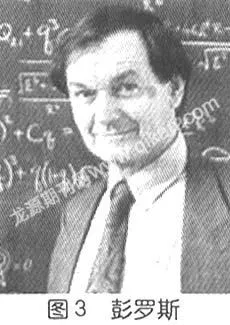
羅杰·彭羅斯,這位被譽為當代“最博學、最有創見”的科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于1989年推出了《皇帝新腦》一書。該書立刻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上榜并達數周之久,并獲得了1991年科學書籍獎,作為一部經典的科普著作給人們帶來了長久的影響。在書中,彭羅斯借用童話故事“皇帝新衣”來隱喻計算機,正如皇帝沒有穿衣服一樣,電腦并沒有頭腦。他認為,要制造出能滿意地通過圖靈測試的計算機還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即使真有計算機通過了圖靈測試,我們還是不能斷定它真的具備了智能。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彭羅斯以一個故事的形式不失幽默地攻擊了圖靈測試與人工智能。
大會堂里有一個盛大的集會,標志著新的“超子”電腦的誕生。總統波羅剛剛結束了他的開幕詞。現在,總設計師正在進行他的發言:“有1017以上的邏輯單元,這比組成我們國家中任何人的大腦神經的數目還要多!它的智慧將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馬上就有幸親眼看到這種智慧。讓我們的超子電腦開動運行!”
總統夫人向前走去,有點緊張,也有點笨拙,不過她還是轉動了開關。“噓”的一聲,這1017邏輯單元進入運轉時有一絲難以察覺的暗淡的光,每個人都在等待。“現在有沒有觀眾想提出第一個問題來讓我們的超子電腦開始工作?”總設計師問道。每個人都感到羞怯,生怕在眾人面前出丑——尤其是在這個新的上帝面前。一片寂靜。“可是必須得有一個人來提問呀?”總設計師請求大家。可是大家都害怕了,似乎感到了一個新的權威的威懾。
這時,坐在第三排的一個孩子舉起了手,總設計師說道:“這位小朋友,你要向我們的新朋友提個問題,是嗎?”孩子戰戰兢兢走到超子電腦面前,“是的,我想問的是,超子先生,您現在感覺如何?”“嗯,一個最有趣的問題,我的小朋友,我自己也想知道答案。”這位總設計師說道,“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朋友對這問題怎么說……真奇怪……呃……超子電腦說它不知道……它甚至不能理解你想問的是什么!”壓抑的會堂里終于爆發出大笑……
■ 對詰難的反駁
正如《劍橋五重奏》的作者、美國著名科普作家約翰·卡斯蒂所說,塞爾和彭羅斯在20世紀80年代對人工智能的兩輪“討伐”引發的爭論至今未息,他們的詰難也激起了人工智能界的反駁,同時促使人工智能學術界嚴肅地反思構成他們研究基礎的一些哲學問題。

“人工智能”術語的提出者、1971年圖靈獎得主、有“人工智能之父”之稱的約翰·麥卡錫回應塞爾“中文屋子”假想實驗時說:“雖然屋子里的人不理解中文,但屋子這個系統已經具備了理解能力,這就夠了。我們就可以說這間屋子具有智能。”也就是說,判斷一個問題是否得到了理解,依據的并不是我們是否能夠洞察這個問題在人腦或計算機中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而是看人或計算機在其特定的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行為。在“中文屋子”中,我們所依據的只能是屋子整體所表現出來的實際結果,而這個實際結果就是看守判定里面的丹瑪是懂中文的。對于看守而言,屋子內部完全是一個“黑箱”,他無法直接和屋子中的丹瑪溝通,就像我們不可能觀察到在他人頭腦中發生的思維過程一樣。
正如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不停追問,“圖靈測試能否證實人工智能存在”這個問題竟然涉及了人類與計算機的思維、語言、情感等諸多方面的爭論。而針對這些問題的深入討論已經使其由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演變為一個哲學問題,時至今日,這一問題尚未有完全令人滿意的答復。或許我們應該重溫圖靈在《計算機與智力》文中的最后一句話:“我們只能向前看到很短的距離,但是,我們能夠看到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試問,假如圖靈活到今天,他對當今人工智能的發展會感到滿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