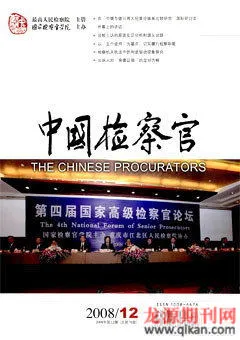盲目高速駕車撞人致傷行為如何定性
1 基本案情
王某,A縣人,有多年駕駛經驗。2006年10月3日15時許,王某駕駛面包車,在往A縣長途汽車站進出口方向的公共道路上,未注意觀察路面交通情況,盲目高速行駛,在距離長途汽車站進出口64米處,車頭碰撞相對方向駛來人力三輪車后,車輛繼續前進,在距進出口39米處,車頭又碰撞相對方向駛來的人力三輪車,相繼導致三輪車夫林某輕傷、朱某重傷。
交警部門認定王某負該起交通事故全部責任。經查,王某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交通解釋》)第2條第2款規定的“酒后、吸食毒品……”等六種情形的任意一種情形。
本案,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定性方面,存在爭議。
2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無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 評析意見
(一)《交通解釋》第8條第1款不能曲解為“在公共道路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只能按交通肇事罪定性處罰”。
首先,應從《交通解釋》全文把握其精神實質。《交通解釋》第1條:“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再結合第8條規定,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圍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規定定性處罰。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條件,“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圍內”是交通肇事罪的空間條件,“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是交通肇事罪的結果條件,只有這三個條件都具備了,才以交通肇事罪定性。而不能理解為:凡是公共交通道路內的重大交通事故,惟獨考慮交通肇事罪,除此之外,不構成其他任何犯罪。
其次,《交通解釋》并沒有排除刑法其他罪名的適用。理論上,在公共道路內駕駛機動車輛觸犯刑法分則其他規定的,仍應定其他犯罪。如果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在公共道路上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應定交通肇事罪;如果行為人為了殺人、傷人,采取駕車撞擊的方式,即使是在公共道路內,也應定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如果行為人出于報復社會的動機,采取駕車撞向公共道路中的車輛或人群的方式,則應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再次,按照犯罪構成理論,行為人在公共道路內駕車,只要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就應以相應罪名定罪處罰;如果不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則不以犯罪論處。在此,應該具體分析公共道路內駕駛機動車致人重傷的情況:如果行為人有《交通解釋》第2條第2款規定的“酒后、吸食毒品……”等六種情形之一的,造成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以交通肇事罪論處:如果行為人沒有六種情形之一的,而是出于過失,造成事故致人重傷的,可以按照過失致人重傷罪論處:如果行為人沒有六種情形之一的,在公共道路內盲目高速行駛,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以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反之,如果行為人在公共道路內,未違反交通運輸法規,也不存在主觀過失,而是因被害人過錯發生碰撞導致重傷的,行為人不負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在禁止行人行走的封閉的道路如高速公路內,未違反交通運輸法規,碰撞在高速公路內意外出現的行人的,不負刑事責任。
最后,在理論探討和司法實踐中,對于發生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圍內的重大交通事故,也不乏被定性為其他犯罪的理論觀點與審判實例。如《人民司法》2003年第10期刊載吳繼生、唐艷《交通事故中過失致人重傷定性的法理研究》一文,就提出過失致人重傷罪的定性意見;再如,2007年1月2日《人民法院報》刊發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院陳黎筍、鄭朝芳《車內人員爭奪高速行駛車輛致路人死亡——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文,則介紹了江蘇省鹽城市中級法院終審裁定王純龍、于抉、孫學軍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審判實例。
(二)法條競合與區別近似行為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筆者認為,無罪意見中的法條競合觀點。是把法條競合與區別近似行為這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混為一談,導致了分析判斷的錯誤。
首先,法條競合是不同法條在內涵或外延的相互關系問題,法條競合是立法中的客觀形態上的存在。我們知道,因刑法分則法條的錯綜規定,出現數個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具有從屬或者交叉關系的情形時,理論上稱之為法條競合。而且,法條競合的本質并不因為具體行為的出現才引起競合,而是不同法條本身之間的內涵或外延形態上就存在著必然的邏輯關系,如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本身就是存在著競合關系。當一個行為,完全符合整體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時,必然也符合部分法規定的構成要件,這種情況是法條競合中的包容競合關系。必須注意的是,這一行為要完全符合整體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才存在法條競合問題。本案,王某并無《交通解釋》的六種情形之一,因此,王某之行為不能用交通肇事罪加以評價。就不存在什么整體法與部分法的問題,也就沒有法條包容競合及其適用原則。
其次,區別近似行為是針對近似但又不同的行為進行由現象到本質的分析問題,分析近似行為在本質上的差異,是司法裁判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重要方法。本案,王某駕駛車輛、在公共道路內行駛,過失撞人,該行為確實與交通肇事罪所規定的客觀行為極為近似。但是,交通肇事罪在造成重傷結果時,要求有《交通解釋》的“六種情形”之一作為法定條件,由于王某之行為不具備這一法定條件,就不屬于交通肇事行為。繼而按照犯罪構成要件分析,我們發現,王某之行為可能符合過失致人重傷罪、也可能符合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規定的客觀方面要件。
(三)犯罪對象的特定與不特定之間可共存、轉化
理論上,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特定與不特定可以相互轉化。不特定因素會因行為的方法、時間、地點等環境條件的改變而增多,從數量上超過特定因素,促使特定性向不特定性發展。不特定性在發展過程中也會因方法、時間、地點等環境條件的改變而逐漸減少或消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對特定性。例如,《交通解釋》就為犯罪對象由不特定到特定轉化開了個口子。《交通解釋》第8條第2款:“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134條、第135條、第233條等規定定罪處罰。”該解釋將同樣是駕車過失撞人這種針對不特定對象的行為,僅因發生在公共道路以外,而規定為犯罪對象相對特定的過失致人死亡罪或過失致人重傷罪等。實踐中,天津市紅橋區檢察院對“小區內駕車撞人致人重傷”案件,則以涉嫌過失致人重傷罪提起公訴。
(四)其他危險方法的認定問題
《刑法》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規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5條第2款規定了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謂危險方法,通說認為是指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的危險性相當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認定具有“相當性”的其他危險方法,還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
1、依據當時的刑法規定。在《刑法修正案(三)》之前,1997《刑法》第114條采取正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其他危險方法行為的“對象要素”為“工廠、礦場、油田、港口、河流、水源、倉庫、住宅、森林、農場、谷場、牧場、重要管道、公共建筑或者其他公私財產”等,由于當時所列舉的“對象要素”并不包括“人”,那么駕車撞人、私設電網傷人、向人群開槍等方式就不宜認定為其他危險方法。而《刑法修正案(三)》刪除了這些“對象要素”,且結果要素又包括“致人重傷、死亡”,那么駕車撞人、私設電網傷人、向人群開槍等方式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其他危險方法。
2、依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0條規定:“邪教組織人員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3、從行為本質上確定“相當性”。“其他危險方法”既然與放火、爆炸、決水、投毒等行為并列規定,自然應具有與其“相當性”。但是,“相當性”無法從行為方式上去類推比照,放火可以是點燃易燃物的方式,爆炸可以是啟動引爆裝置的方式,決水可以是挖掘攔水壩的方式,投毒可以是向河流、水井中投放,也可以是向空氣中投放,就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毒罪這四種基本犯,都無法用統一的行為方式加以界定,其他危險方法當然也不能以界定行為方式而加以認定。既然從行為方式上無法確定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的“相當性”,那么從本質上確定其“相當性”就是可行的路徑。只要行為在本質上足以危及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安全,就可以認定為具有本質上的“相當性”,
4、刑法分則另有規定的,按照相關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114條、115條的“兜底”規定,而非刑法其他罪名的“兜底”規定。刑法分則另有規定的,如:破壞交通設施罪,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就只能按該條處理,不能為了從重處罰而解釋此種行為同時也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五)盲目高速駕車撞人致傷行為中的想象競合問題
王某實施了盲目高速駕車撞人致傷的一個行為,這一行為的結果導致一人重傷、一人輕傷,一行為既觸犯了過失致人重傷罪,也觸犯了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理原則,應擇一重罪處罰,即,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
有觀點認為,似王某這樣盲目高速駕車撞人的行為,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為犯罪,要想把它作為犯罪來處理,可以采取舉輕明重的方法。就是說一個輕的行為(過失致人重傷)在刑法當中都規定為犯罪,你這個行為(一人重傷、一人輕傷)比它重,即使刑法沒有規定,也應當作為犯罪來處理,據此,應依照過失致人重傷罪論處。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本身的前提是不妥當的。“舉輕以明重”可以用于1979刑法,因為當時刑法規定了類推制度。我國現行刑法確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罪刑法定原則,“舉輕以明重”的類推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如果認為刑法并沒有明確規定這類行為為犯罪。就不能以犯罪論處。
需要強調的是,在司法實踐中,一個案件事實,總是具有多重屬性,常常牽涉多項法律,以不同的法律規范為指導,歸納、評價案件事實,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在遇到案件事實可能觸犯刑事犯罪時,司法工作人員應當在刑法規范的觀點下進行分析,目光要不斷往返于罪刑規范和案件事實之間,而不能簡單地以案件事實屬于民事范疇為由,認為案件事實不構成犯罪。我們堅持以行為的犯罪構成符合性來判斷是否犯罪,前述評析意見已經多次闡述了本案王某行為既符合過失致人重傷罪,也符合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鑒于兩者之間存在想象競合,應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