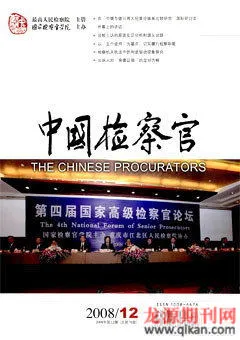綁架期間奪取財物行為的認定
1 基本案情
2005年2月13日12時許,被告人康某糾集宋某、王某(另案處理)采取毆打手段逼迫被害人劉某承認與康某之妻發生性關系,并將被害人劉某挾持到一招待所407房間。在招待所里,康某等人把被害人身上隨身攜帶的一部波導手機和800元現金奪走,之后向其勒錢,迫使被害人打電話讓其家里人匯來了5000元錢,康某等人把5000元錢取出后,又讓被害人給其女友打電話,要求送2500元錢到指定地點,康某等人在約定地點接錢時被當場抓獲。
2 分歧意見
在審理中,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康某的行為僅構成綁架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康某的行為不僅構成綁架罪,而且由于其在綁架期間,又公然奪取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財物,其行為也構成搶奪罪。對其應散罪并罰。
3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本案主要有兩個疑難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被告人康某在綁架被害人期間奪取被害人隨身所帶財物的行為如何認定,是構成搶劫罪還是構成搶奪罪;二是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在綁架過程中以暴力、脅迫等手段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
(一)被告人康某在綁架被害人期間奪取其財物的行為的認定
在綁架期間,被告人康某奪走被害人劉某隨身攜帶的一部手機及800元現金的行為不構成搶劫罪。
搶劫罪是一種復合行為犯罪。行為人一方面必須對被害人采取了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另一方面必須實施了劫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在綁架過程中,行為人當場劫取被害人攜帶的財物,盡管滿足了搶劫罪客觀方面的第二個行為——劫取財物的行為。但行為人并沒有對其實施搶劫罪所要求的第一個行為——暴力行為。行為人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從被綁架人身上奪取財物,是基于其先前所實施的綁架行為,即采取了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使被綁架人處于自己的實力控制下,這時,行為人成立綁架罪。在成立綁架罪后,行為人發現被綁架人身上還攜帶著其他財物,并將其奪走,這一行為的實施是基于綁架行為實施完畢后產生的不法狀態,沒有前面的綁架行為,行為人不可能順利地從綁架人身上奪取其財物。因此,行為人在綁架期間當場奪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客觀方面不符合搶劫罪所必需的實行行為,不能成立搶劫罪。
被告人康某在綁架期間奪取被綁架人劉某隨身攜帶的手機和800元現金的行為構成搶奪罪。其理由如下:
1、符合搶奪罪侵害的客體。搶奪罪侵害的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被告人在綁架劉某期間奪取其手機和800元現金,侵害了被害人對其財產的所有權。
2、符合搶奪罪客觀方面的實行行為。搶奪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公然奪取財物所有人或財物保管人的財物。(1)何謂“公然奪取”?著名刑法學者趙秉志認為,“公然奪取”是指“財產所有人或保管人在場的情況下。行為人當著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的面或者采取可以使其立即發覺的方法奪取財物”。康某在綁架期間當場奪取被綁架人劉某隨身攜帶的財物,是在劉某不能反抗的狀態下當著劉某的面實施的,該行為符合搶劫罪“公然奪取”的特征。(2)“乘人不備”是否為搶奪罪的構成要件?著名刑法學者王作富認為,“大多數搶奪行為雖是乘人不備時實施的,但在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備的情況下搶奪財物的也并非少見”。因此,被告人康某當場奪取被綁架人的財產,不論是在被綁架人有所警覺的情況下實施還是乘人不備時實施,都不影響其行為構成搶奪罪。(3)被告人康某的行為符合搶奪罪的行為指向。搶奪罪的行為指向是財物,而非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的人身。被告人康某當場奪取被綁架人的800元現金和手機時。并沒有采用暴力、脅迫等危害人身安全的手段,其奪取財物的行為直接指向被綁架人的800元現金和手機。而非指向被綁架人的人身,因此,該行為符合搶奪罪的行為指向。
3、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符合搶奪罪的構成特征。行為人主觀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被告人康某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在綁架既遂后產生的,屬于“另起犯意”,康某在實施綁架行為前不存在該犯意。因此,非法占有被綁架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目的不能被綁架目的所包容,被告人康某奪取財物的行為應當單獨進行評價,而不應當作為綁架罪的量刑情節考慮。
(二)正確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答復》的適用范圍
根據2001年11月8日《答復》的規定:行為人在綁架過程中,又以暴力、脅迫等手段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構成犯罪的,擇一重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復解決了司法實施中出現的這樣一類情形:行為人出于綁架意圖,對被綁架人采取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使被綁架人處于自己的實施控制下后,再一次采取暴力、脅迫等手段,當場劫取被害人的財物,后一次實施的采取暴力手段劫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在綁架罪和搶劫罪中擇一重罪處罰。
上述情形不同于行為人在綁架期間當場奪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行為人在綁架過程中當場奪取被害人的財物,是行為人控制了被綁架人的人身自由后,從其身上奪走財物。行為人奪走財物前,并沒有再一次對被綁架人實施暴力行為,而是利用了被害人被綁架后處于不能反抗的情形奪取其財物,奪取財物的行為并不能構成搶劫罪。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答復的適用范圍僅限于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既構成綁架罪,同時還構成搶劫罪的情況,而不能適用于行為人在綁架期間奪取被害人的財物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