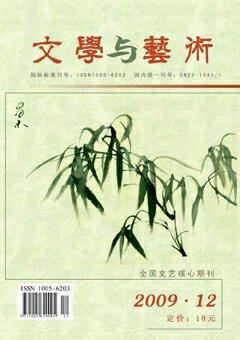簡析1924-1926年間魯迅的“復仇游戲”
王 宏
【摘要】1924—1926年間,由于感知定勢和思維偏執的影響,魯迅不得不對社會進行“以抗爭來適應”。不僅抱著“偏不精神”進行著嚴肅的現實游戲,而且在文本中進行著深刻的復仇實驗。可惜的是,此期間整個社會沒有給魯迅喘息的機會,他既執著于復仇又質疑于復仇,一直徘徊在無法消除的迷惑中。
【關鍵詞】復仇游戲 ;“偏不”精神;文本試驗;執著與質疑
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各種誅心之律的非人間,魯迅要起而反抗,要向社會復仇,為自己亦為別人。“復仇”作為魯迅思維的基本命題,貫穿于一生。從閱讀《工人綏惠略夫》開始,他就開始思索復仇。當看到綏惠略夫所采取的瘋狂報復行為,“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魯迅敏銳地感覺到復仇具有可怕的“殺傷力”,發出“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的希望。1并且在1924—1926年間,他選擇了“游戲”戰,既游戲現實又游戲文本,對復仇展開更深入的思考。
現實游戲:“偏不”精神
1926年編輯《華蓋集續編》時,魯迅沉痛地寫下,“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么大舉。”2看似平靜實則憤慨。“偏不”意味著另類,意味著冒險,意味著不可避免的遭迫害……但魯迅還是執拗地選擇了“偏不”。這種“偏不”精神與他思維的偏執性不謀而合。
據長期幫傭的阮和森回憶,魯迅在紹興師范學堂教書時,王金發欲加害負責《越鐸》的魯迅。家人朋友都替他擔心,再三叮囑他晚上不要單獨出門。“魯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飯一定要回到學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兩只手各拿一個燈籠,燈籠上紅紅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從學校回家,又總是說:‘怎么樣?又回來了。”3越是加害,越要主動出擊,越要挑戰你的權威,使你無從下手,不敢下手。在廈門時,“樓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鐵絲攔著,我因為要看它有怎樣的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 4 以身試“刺”冒險“跳鐵絲網”的事情雖小,但魯迅不堪約束、“偏不”遵從的性格卻可見一斑。而且嘗試的結果,也證實了魯迅的最初設想:這些“刺”不過如此罷了。由此不難理解,魯迅為什么會對陶元慶的畫作《大紅袍》那樣著迷,兩次到場兩次均長時間逗留于它的面前,5 過后并對許欽文發出,“握劍的姿態很醒目”的感慨。6
孫伏園曾經在《往事》中這樣說,“幼年被人蔑視與欺壓,精神上銘刻著傷痕,發展而為復仇的觀念”,直接將魯迅復仇觀念的養成推回到幼年時期遭受的歧視和欺凌。確實,小時候魯迅就經歷過一次“復仇”體驗:鄰居小孩沈八斤非常蠻橫,經常拿著自己做的竹槍,喊著“戳伊殺,戳伊殺!”,跳進跳出的亂戳。魯迅不得不采用了畫畫這種隱晦的方式來進行復仇。父親看到后,雖“叫了魯迅去問,可是并不嚴厲……只是把這頁撕去了。”7父親的寬容和理解,使魯迅的心性更加朝著“嫉惡如仇”“睚眥必報”的方向發展。隨著日后身受的災難和不幸的加重,以及別人的嘲弄和謾罵的加深,魯迅這種原始的復仇萌芽,經過“偏不”精神的催發,終于成熟。
1924年的西安之行是魯迅一生除杭州之行以外,唯一的一次旅行。與別人忙著購買各種紀念品不同,他選擇了“弩”這一古代的兵器。“此為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性十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故頗收藏了好幾具(自北京古董鋪購得),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8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武器,而是一個解讀魯迅復仇思想的“符碼”,它暗示了太多的東西:對尚武精神的憧憬、對俠客風范的向往、對復仇內蘊的領悟……
這些現實行為,既是他對黑暗的蔑視,也是他對世界的游戲:無視敵人,盡情地揮舞著復仇之劍。
文本試驗:游戲“復仇”
1924—1926年間,在進行了一系列抗爭之后,魯迅決定“自己裁判,自己執行”, 開始了文本復仇試驗。以“復仇”為命題,共創作了二首散文詩《復仇》、《復仇(其二)》,兩篇小說《孤獨者》、《鑄劍》。(《鑄劍》實作于1927年4月3日,整理成集時署為1926年10月。這一誤記,暗示了潛意識中魯迅一直認為它創作于1926年,故把它作為1924—1926年間的復仇文本分析。)
在《復仇》里,整個文本分裂成“雙重復仇”的層次結構。一是復仇者與仇人之間的復仇,以實際的殺人來收場。復仇者一轉而為“殺戮者”,自身并沒有獲得復仇的快樂,反而陷入“人性茫然”,倒是仇人(被殺者)“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二是復仇者與仇人兩人構成一個整體對看客的復仇,以無所作為來報復,使看客們無戲可看。結果,不但仇未報,而且雙方都“圓活的身體,已將干枯”。魯迅初步質疑了復仇的實際可行性。
既然實際的殺人與無所作為都不能達到復仇的目的,那么,以西方文化的大悲憫態度來原諒仇人忘卻復仇又會怎樣呢?在《復仇(其二)》里,魯迅借以色列人釘殺基督的故事,給出了答案:“神之子”遭上帝遺棄成為“人之子”,難逃被屠殺的命運!
一年后的《孤獨者》,復仇者選擇了以毒攻毒的方式,昔日的敵人開始紛紛向他磕頭打拱。他似乎勝利了,然而卻失敗了。因為這一切都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犧牲愛我者的生命為代價。也就是說,復仇的實現是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毀滅為前提,并且以實體生命的滅亡為結局。《鑄劍》,復仇是憑借先犧牲自己再借他人之力來完成的。只是,他人也被卷進復仇漩渦,生命盡失。在這里,魯迅只能戲謔:復仇演化為巨大的引力場,吸引著,也摧毀著每一個人。
就在魯迅對文本內容作游戲的同時,他還對文本的形式做著“戲仿”實驗。如作于1925年2月28日的《長明燈》,在內容上幾乎是《狂人日記》的翻版,但文章末尾對駱賓王《鵝》的戲謔化處理,使其有了全新的內涵:不但確立了“疑而走”的抗爭路線,消解了以“孩童為中心”的進化論,而且使戲謔化的寫作模式初具雛形。
就這樣,1924—1926年間,魯迅抱著嚴肅的人生態度,不但借“偏不”精神對人世間展開復仇游戲,而且以戲謔的筆墨進行文本復仇實驗。既執著于復仇又質疑于復仇。直到臨去世前的《女吊》,他不再游戲,借這個美麗凄婉的復仇者形象直接肯定了復仇。
【參考文獻】
[1]魯迅. 記談話. 魯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357
[2]魯迅. 華蓋集續編·小引. 魯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83
[3]阮和森. 魯迅故居和藏書. 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6
[4]魯迅. 兩地書·六二. 魯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77
[5]魯迅年譜(修訂本),第二卷.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1999:187
[6]許欽文. <魯迅日記>中的我. 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93
[7]周遐壽. 魯迅的故家.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33
[8]張辛南. 追憶魯迅先生在西安. 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01
作者簡介:王宏(1976--),女,漢族,山西太原人,太原大學外語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