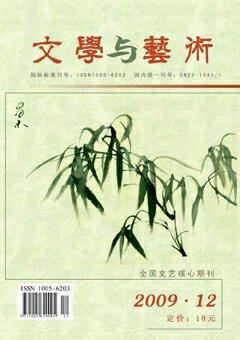失敗的碰壁者——論池莉筆下的知識男性
鄭 璞
【摘要】在社會變革和經濟轉型中,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文化受到了日益增長的市民文化的沖擊和抵御。面對現實,池莉作品中的男性知識分子大多顯得迂腐,虛偽和不適應。知識分子的先鋒性、精英性被世俗化消解。
【關鍵詞】池莉;知識分子;男性
人生三部曲階段,池莉小說描寫的多是計劃經濟下幾近停滯的人生景觀。三部曲時期男主人公面對人生困頓,體現出安分守紀、堅忍寬慰的生活態度,他們是困守的一群。隨著時代變遷,池莉作品中的男人對現實有了或是自覺的、或是被迫的突圍意識。在突圍的男性中,有一群特殊的人,那就是知識分子。之所以說知識男性是特殊的一群,是因為他們在承受著諸如女性的期望,物質生活的壓迫的同時,還承受著九十年代的社會變革和經濟轉型對他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操守的檢驗。眾所周知,池莉的作品褒揚市民文化,否定知識分子文化。因此,她筆下的知識男性在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環境下,大多顯得迂腐,虛偽和不適應。他們是突圍的男人中落魄的失敗者。
知識分子是文化的載體,以一種改造社會,推動歷史的先驅的角色凌駕于一般庸眾之上。知識分子不屑于某種具體目標的達成,他們熱衷于對精神世界進行關照和反思,面對現實,他們往往會表現出比如心高氣傲、眼高手低、過于自矜自潔等等自身的弱點,甚至導致某些沮喪、彷徨、虛無情緒的產生。
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感官享受、物質刺激、利益追逐沖擊著知識分子艱苦而高深的精神跋涉。原有的價值體系迅速瓦解,以經濟為本位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商品化成為肯定性價值占據著理想的地位,伴隨經濟地位的急劇下滑,知識分子不再以精神導師的角色出現。巨大的心理落差帶來的是精神荒漠和信仰無序。這種不平衡的心態使知識分子的弱點暴露無遺。池莉曾批評知識分子:“他重在精神,自感是名士是精英,雙腳離地向上升騰,所思所慮直指人類永恒的歸宿,現實感常常錯位。”[1]王朔就曾評判知識分子那種“無孔不入的優越感”,稱“他們控制著社會全部的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2]
《口紅》中的寧岸原本是一個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在他身上彌漫著溫情主義和理想主義。寧岸在改革開放之前是一位人民教師,后任廠長,生活還不錯。但改革開放之后廠子倒閉了,教師也當不成了,物質上的日愈貧困導致心態發生裂變:一方面為自己清貧為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而驕傲;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的想大把掙錢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特別是文化比他低個層次的趙耀根的暴富極大的刺激了寧岸,他毅然下海。但下海之后他卻事事不如意。市場這個瞬息萬變耳虞我詐的大環境讓他這個知識分子無所適從。最后一個孤傲的知識分子因無法面對失敗而墜入吸毒、走私、賭博的深淵。寧岸的心路歷程和生存觀念的改變表現出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經被我們感知卻無從體驗的社會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認的政治”。查爾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個群體或個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就會遭受傷害或歪曲,就會成為一種壓迫形式,他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扭曲的承認不僅給對象造成可怕的創傷,并且會使受害者背負著致命的自我仇恨。[3]拒絕“承認”的現象在任何社會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寧岸就是這樣一個被拒絕者。不被承認就沒有尊嚴可言。現代社會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嚴,具有了可以分享社會平等關注的可能。就像泰勒舉出的例證那樣,每個人都可以被稱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稱為老爺、太太。[4]但是這種虛假的平等從來也沒有成為生活的現實,等級的劃分或根據社會身份獲得的尊嚴感,幾乎是未做宣告卻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觀念或不成文的習慣法。寧岸試圖突圍就是渴望自己被世人認可。
寧岸的失敗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對世俗社會的不適應。現實生活使知識分子面臨許許多多的困境和難題,無法規避,只有勇敢的面對。但令人遺憾的是,寧岸卻選擇了回避。將回避作為自己現實生存策略的寧岸,并非是對尚未認識到的現代商業社會的一種主動拒絕,相反卻是精神上或物質上被現代商業社會撞得頭破血流的一種被迫選擇,于是這樣的回避,帶給他的是更大的精神危機——物質與精神自信的雙重失落。正如陳平原先生所說:“此后,文化精英所要面對的,已經由政治權威轉為市場規律。對他們來說,或許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感覺到金錢的巨大壓力,也從沒像今天這樣意識到自身的無足輕重。此前那種先知先覺的導師心態,真理在手的優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產生的悲壯情懷,在商品流通中變的一錢不值。于是,現代中國的唐·吉可德們,最可悲的結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離經叛道而遭受政治權威的處罰,而是因其‘道德、‘理想與‘激情而被市場所遺棄。”[5]
在世俗化欲望的沖擊下,如果說寧岸的突圍經歷著心靈掙扎和靈魂爭戰,體驗著靈肉沖突和痛苦,那么《你以為你是誰》中另一個知識男性湖北大學的李教授就是完全自覺的被世俗文化同化。
小說中的李老師被刻畫的窮酸迂腐可笑。他總是為自己的世俗生活尋找崇高的借口,打著形而上的幌子過著形而下的生活。居住在漢口洞庭里小市民圈子中的他多方論證自己與市民居住一起的理由 :一是他們都是革命工人的后代,而他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二是他不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在這里,而是為了“體驗生活”。在這里“由于有了高級的精神生活,李老師的內心獲得了平衡。他安心安意的居住在洞庭里16號,既學跳舞也學打牌,既敢喝高度白酒也敢唱它一嗓子卡拉ok,既憤世嫉俗也同流合污,比如不時接受陸武橋的邀請,去參加一些公款吃喝的飯局。……我不去我怎么深入了解社會生活及流行語言?怎么會認識海參和鮑魚?魚翅和燕窩?”他既得陸武橋的好處,又從精神上瞧不起陸武橋。“如果恰巧這時候陸武橋抖擻的經過他家窗前,他就會鄙視的低沉的說:‘不就是為了幾個臭錢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嗎?除此之外,小子,你還有什么?”
對知識分子如此嘲諷實際上在大聲呼告知識分子已經“死亡”,他們喪失了按超越自我堅守真理的現實批判精神。按照路易斯·科塞的說法,知識分子不僅是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并且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還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6]知識分子的要義是具有超越自我及其所屬專業的公共關懷和為真理而獨立不倚的現實批判精神。中國古代以士大夫為代表的知識精英有道統作為精神上的支撐,有學統提供知識和學理上的資源。他們有自我犧牲精神及使命感和責任感,即使身處逆境,也能泰然處之。而大眾的確對這兩大傳統敬畏不已,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物化時代、欲望膨脹、消費人生,說的重一點無異于沒有硝煙的戰爭,它在時時撩動你的“本我”欲望,使你向人的自然本能、生命原欲滑落,甚至是一落千丈。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種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動聲色的強制性,逼迫每一個人就范,使他們失去身份,變成一個個僅僅活著的個體。”[7]
【參考文獻】
[1]池莉.《寫作的意義》[J].池莉文集(四).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243—244
[2]王朔.《王朔自白》[c].文藝爭鳴.1983(4)
[3][4]孟繁華.《21世紀初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J].萬方數據
[5]陳平原.《近百年中國文化精英的失落》[J].21世紀.1993(6)
[6]許紀霖.《另一種啟蒙·自序》[M]花城出版社.1999.8
[7]閻真.《做人和當作家》[J].文學漫談—名家專訪.奧博教育網
作者簡介:鄭璞(1978-- ),湖南長沙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