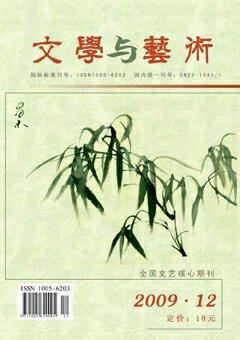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副面孔
柳沙沙 劉嬌蕾
【摘要】在汪曾祺的小說《受戒》中有兩副面孔,即傳統主義的和現代主義的,兩副面孔在汪曾祺的小說是以一種交融而非間離的面目出現的。本文分別從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副面孔來研究汪曾祺,傳統主義的面孔主要是從內容方面即日常生活的溫暖著手,現代主義的面孔主要是從形式上的意識流上來探討。
【關鍵詞】傳統主義; 現代主義; 民族情結
一、 前言
1980年,汪曾祺的小說《受戒》一發表就引起了大家的密切關注,評論家紛紛發表文章對他的小說進行評論,對汪曾祺的研究也因此慢慢開展起來。本文試圖從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副面孔來研究汪曾祺的小說《受戒》。
二、 傳統主義的面孔
幼年的汪曾祺生長在一個亦商亦士、開明而不庸俗的書香門第,其父親給了他極大的影響。父親通曉琴棋書畫、喜愛花鳥蟲魚,具有典型的士大夫修養和情趣,其“仁”者的“救世意識”給幼年汪曾棋及其深刻的影響。因此,汪曾棋從小就對人情風俗和自然萬物充滿好奇和樂趣,童年的經驗將各種人情美景映入了作家的記憶。本文將從日常生活的溫暖和這個方面來論述《受戒》中的傳統主義的面孔。在《受戒》中,汪曾祺是通過對過去熟悉的事物、事情和生活的細節來展示日常生活的可愛與溫暖的。
首先,我們看到了過去很熟悉的事物如桑葚、桑樹、蘆花蕩子、圍裙飄帶、荸薺等,熟悉的事情,這些事物就是一首首童謠,總能激起人內心的漣漪。大家能夠清晰的回憶起小時候用水車車高田水,車水的時候看見水被一級一級的傳遞上去,這對小孩子來說似乎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在當時一直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但卻別有一番生活趣味。而象“不把錢、雞婆子”這些口語色彩很濃重的詞語,不僅讓人覺得親切,更能激起人們對過去的美好回憶,在現代社會中,往往是這些過去的事物更能夠激起人們對生活溫暖的感覺。
再次,作者通過對一些細節的簡單描述,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溫馨的美妙的世界。如兩個小孩天真無邪玩銅蜻蜓那段,“小英子跑過來:‘給我!給我!”。我們讀到這里立馬就能看見兩個對世界充滿好奇感的小孩子,其中一個小孩對某種新事物很了解,會玩會操作了,必然會引起另一個小孩極大的興趣,而且一開始,另一個小孩子會因為對新事物陌生而產生害怕而遠遠的站著,當他發現如此好玩的時候便會興高采烈的跑過去嚷著:給我,給我。而一直被大家所稱道的明海和小英子的充滿情趣的愛情,更是透露出了生活的美好。作者寫到“明海看看她的腳印,傻了。……他覺得心里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搗亂了”,作者用搗亂、心癢癢很貼切地傳達了這樣的感覺,而有了這樣的感覺,劃進無人的蘆花蕩子就必然會因為有了心事后害羞而覺得心里面莫名的緊張,于是想拼命的劃槳逃離這個緊張又有點窒息的二人世界,只要出了蘆花蕩子,緊張的心就會緩口氣松弛下來,如釋重負。之后那大聲的要之后又小聲的要,是兩個人吐露心聲之后小小的歡喜,小聲的說更是兩個人對愛情的一種小心翼翼的呵護;兩只漿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則是兩個人知道彼此的心之后的心情的輕快了,所以兩只漿一定是劃得飛快的。文章中的傳統主義面孔實際上是一種認同,對傳統倫理道德規范的認同,這種認同以一種潛意識里的懷舊和對過去年代的人和事的懷念的形式出現。
三、 現代主義的面孔
汪曾祺創作起步于20世紀40年代,他就讀的西南聯大正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汪曾祺很自然地接受了現代主義洗禮,并參與創辦《文聚》,不斷磨礪現代主義技法。但是汪曾祺說,“我不贊成把現代派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① 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是喜歡現代派的,但是不主張全盤照抄西方的理論,而是主張將西方的理論本土化。現代主義不僅是一種文學思潮,更是對于社會、文化、人性的探索和拷問。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界定充滿爭議,本文把汪曾祺涉及的現代主義文學主要界定在意識流這個方面。
在作品《受戒》中,汪曾祺開篇就以現在的時間作為中心,作品寫到“明海出家已經四年”。然后接下去講述他十三歲來荸薺庵之前為出家做的一系列事情,接下來又講現在小和尚清閑的日子及庵里面的基本情況尤其是庵里面沒有所謂的清規戒律,在講到和尚們打牌的時候,敘述的筆觸又自然的伸到了收雞毛的和打兔子兼偷雞的兩個正經人身上,由偷雞又講到小英子和明海兩個人玩偷雞的家什——銅蜻蜓。然后又繼續轉回到到打牌,打牌還沒有寫幾句又突然轉到了和尚們在大殿上殺豬的事情上了,講完殺豬,又無端的轉到了寫明海和小英子的交往上去了。作者隨自己的思緒在各個場景之間不斷的轉化,有時交叉,有時又重疊起來了,純粹是通過自己的自由聯想來組織故事,情節在《受戒》中淡化了。所以,作者在對人物的激烈反應的心理也往往表現出節制,沖淡與平靜,沒有波瀾起伏,更沒有什么矛盾沖突、因果關系。
由于汪曾祺對社會現實審美感受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對用連貫有序的故事性和恩怨相報的倫理圈子是否表現現實生活的真實表示懷疑,于是,便用“抒情的東西”來擠破固有的故事結構,在情節松動的地方,詩意、哲理、諷刺、幽默、政論、風俗、時尚、意識流一齊涌了進來,使小說獲得了對生活的最大的創造能動性。另外,汪曾祺的不愿被小說的規范所約束,執意追求自由的創作行為,也影響了“先鋒派”小說的游戲性質。
結 語
雖然兩副面孔的交融使小說在整體上很和諧和優美,但是背后卻涂上了一層淡淡的悲涼的底色,因為小說的最后寫到:兩人劃進了蘆花蕩,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嚕嚕嚕飛遠了。鳥兒被外界驚起而倉皇的飛走了,帶給人無限的憂思和落寞。可喜的是,面對日益強大的現代化潮流,汪曾祺并沒有表現出過多的悲哀和絕望,最多也就是一點淡淡的哀愁。不悲哀,不絕望的背后一定有東西在支撐著,它就是五四新文學傳統和民族主義情結。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種精神情結深深的系在了20世紀每一個文人的心靈里。汪曾祺的作品雖然沒有直接反應水深火熱的現實,但是從另一個側面實現著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反思和超越。汪曾祺從創作的初期就力圖發現民族優秀的文化精神。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民族文化又面臨著如何順應現代化的考驗,他認為沒有融入到優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參考文獻】
[1]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陸建華·汪曾祺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3]洪子誠·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作者簡介:柳沙沙(1984--),女,湖南人,現就讀于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碩士
劉嬌蕾(1984--),女,江蘇人,現就讀于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