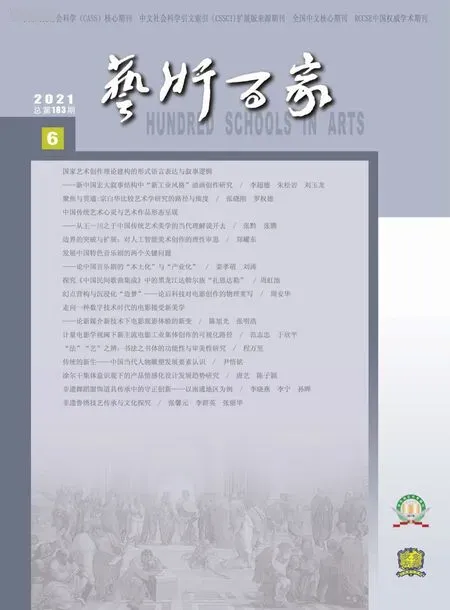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但丁讀后感》品析
方 旻



摘 要:《但丁讀后感——幻想奏鳴曲》是李斯特重要的鋼琴作品之一,音樂中所表現的精神內涵與但丁文學主題有著本質上的聯系。在整首鋼琴作品中,李斯特將象征黑暗的主導動機貫穿全曲,為音樂奠定了一個“不協和”基調,塑造了“魔性”音樂形象。同時,又把象征光明的D大調調式色彩與大三和弦反復運用,構成了“神性”音樂主題。“魔性”與“神性”兩個音樂主題既相為矛盾,又互為滲透,并在“人性主題”的轉化中達到和諧統一,最終體現了李斯特“在魔性中爭斗,在神性中統一”的精神內涵。
關鍵詞:李斯特;音樂作品;《但丁讀后感》;精神內涵;地獄主題;人性主題;上帝主題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
Appreciating Dante Sonat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Liszt's music and Dante's Literary Themes
FANG Min
李斯特《旅行歲月——意大利卷》中的每首作品,都附有一個文學性和描繪性的標題,作曲家透過這些精致細膩的標題,從不同角度向我們展現了它的音樂與意大利文學、繪畫等藝術千絲萬縷的聯系。李斯特向來主張“標題音樂”,他堅信音樂與文學可以相互闡釋,并融為一體。這為我們試圖了解他的音樂精神內涵與傳奇一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但丁讀后感——幻想奏鳴曲》作為此卷中最具規模的一首作品,完成于1849年,為單一樂章的奏鳴曲形式。標題取自雨果作于1836年的詩集《內在的聲音》,內容為李斯特自己讀但丁《神曲》的印象。
此作品從最初創作(19世紀30年代末),至最后定名(1953年)歷經十多年,這不禁使我們欲想深入地去了解,在那段被作曲家自稱為漫游歲月、朝圣歲月的日子里,他的生活究竟有著怎樣的特殊經歷?他的思想又經歷了怎樣的階段?這部作品的創作以“但丁”命名,那么李斯特音樂中表現的精神內涵,與但丁的不朽之作《神曲》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系呢?
《神曲》原名為《喜劇》,是一部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也是意大利文學史中最偉大的詩篇。分為《地獄》、《煉獄》、《天國》三部,是但丁在政治失意后,為擺脫內心苦悶,表達強烈的救國救民的熾熱心情寫照。作品中處處透露著作者思想上的雙重性甚至多重性。其一表現為:人文主義情懷帶著濃烈的宗教主義色彩雙重性;其二表現為:狹隘的宗教信仰與開明的政治理想相統一的雙重性。這種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形成的思想多重性,恰恰反映了時代矛盾對但丁的深遠影響。
這種思想上的多重性,同樣也存在于李斯特的性格中。他一生游歷歐洲各國,人生閱歷豐富,情史無數,并樂于助人。上有上帝的昭示,下有魔鬼的誘惑,可以說他是魔性與神性的統一體。這樣雙重乃至多重的個性特征,形成了一個矛盾的綜合體貫穿于他傳奇的一生,而李斯特音樂中所表現的精神內涵,正是這樣矛盾性深入于他靈魂與血液中的最佳寫照。
但丁與李斯特性格上的共性,是構建兩者間聯系的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但丁的文學主題,與李斯特透過《但丁奏鳴曲》表現的音樂精神內涵有著本質上的相通性。文學作品《神曲》以《地獄》篇象征黑暗與苦難,以《天國》篇象征光明與幸福,形成了對立的兩面,而將《煉獄》置于中間,表現從黑暗苦難向美好光明過渡時所必經的艱辛歷程。《地獄》與《天國》對立的兩面,通過《煉獄》的轉化,最終達到和諧統一,這樣的“轉化統一”即是《神曲》作為一部理想“喜劇”的最本質的表現意義,也是李斯特《但丁奏鳴曲》表現的音樂精神實質,即為“魔—人—神”這個永恒的主題。
一、地獄主題——“魔”
《神曲》中扣人心弦的《地獄》篇,向我們講述著那些在黑暗與絕望中掙扎的靈魂,仍然被人世間的感情和欲望所迷惑,眷戀著以往的生活。成群的罪惡靈魂和魔鬼,古典神話中的人物,奇形怪狀、混亂、凄涼、艱險可怕的景物,相互交織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渲染了地獄的恐怖氣氛的同時,使人聯想到人生的悲慘。
《但丁奏鳴曲》中的地獄主題,出現于全曲的引子部分,在這里李斯特已向我們展示了貫穿整部作品的主導動機。在這個極度渲染恐怖氣氛的簡短樂句中,包含了若干個貫穿整曲的核心材料,每個材料都以其獨有的表現意義與衍生方式,形成了一個“網狀”脈絡,構建起全曲的“黑暗”與“不協和”的音樂基調。
主導動機的主要核心材料包括:
1.增四度音程
樂譜第1-2小節為全曲的開端處,“三全音”以其“魔鬼”般猙獰的形象,拉開了全曲的序幕。向下進行的八度音程像是邁向地獄的腳步聲。這一魔鬼形象的動機展現貫穿全曲,“三全音”在其本身的“不協和”音響的表達中還具有兩種“轉化”性的用法,在作品中被衍生使用。
1)“三全音”的轉化
“三全音”可以通過屬七和弦等音轉化的方式,作為半音調性關系的轉接中心點,把最遠端的兩個調性關系轉化成最為毗鄰的兩者。不僅如此,它轉化的本身還具有“增和弦”的色彩亮度。
我們知道,在李斯特的作品中,“增和弦”具有獨立的色彩性表現,經常作為暫時性模糊調性手段,被多處運用,有時甚至用于終止式。
在樂譜第23-24小節中李斯特用半音進行的方式,構成g小調的III級增和弦替代屬七和弦,運用于終止式,這樣的結尾方式同樣也出現于b小調奏鳴曲中,可見其普遍性。
2)“三全音”的疊置
另一方面,這個音程也可通過疊置的方式,構成一個減七和弦。
在第7-8小節里把第1-2小節A-Eb與第7-8小節C-F#兩個音程進行疊加,那么就可得到A-Eb-C-F#(=gb),呈現出“減和弦”的色彩亮度。作品中多處出現的減七和弦,是音樂“黑暗”與“不協和”表現的又一種表現手法,同樣以其陰森、恐怖的象征性意義貫穿全曲。
2.半音化的線條
在樂譜第3-5小節里主導動機3-5小節低音聲部出現的Eb-Fb-Eb助音式的半音進行,仿佛是靈魂在黑暗中痛苦的呻吟,這個半音動機,之后衍生形成“半音化線條”,覆蓋了全曲大部分的篇章。“半音化線條”作為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的典型創作手法,被作曲家們普遍運用。在李斯特的音樂中,“半音”這個最為不協和音程,以不同的方式衍生發展,其印記隨處可見。然而,這個“不協和”因素作為李斯特獨有的色彩性思維,對20世紀的音樂影響深遠。它的獨特性表現于:
1)半音化旋律的和聲性表現
樂譜第35小節開始的呈示部主部主題是由上下聲部平行并交替兩個半音化線條構成。這個“旋律”與“和聲”并駕齊驅的雙重性半音化線條,是李斯特對半音線條的典型運用手法,在低聲部D音的持續中,一個半音化的和聲音響在不停地涌動,為人們描述出一幅罪惡靈魂在地獄中飽受煎熬、拼命掙扎又不知所措的悲慘畫面。
2)重復中變化的色彩性表現
樂譜第35-43小節是李斯特又一個典型的半音化寫作手法。在結構相同的樂句重復出現時,增高或降低一個半音,使其具有不同的色彩表現.如同譜例中第35小節旋律中的Bb音與第40小節的B音,升高半音的變化,不僅使同樣的樂句,在重復陳述時具有不一樣的色彩亮度。同時,這個半音變化也清晰地表明了句法結構,因為,在大多數的樂句進行時,李斯特通過半音和聲性的進行來模糊調性,其中不運用明確的功能和聲。
3.重復音節奏
在樂譜第1-2小節中帶裝飾音的二分音符與四分音符構成的重復音節奏,作為核心節奏貫穿于全曲。每一個鏗鏘有力的八度重復音表現出地獄中那些哭泣靈魂在黑暗與絕望中的痛苦掙扎,也是樂曲音樂內涵表達的核心。這個節奏動機,以“一點”——“雙線”——“多層面”的衍生方式發展并覆蓋于整曲的節奏表現。
1)“一點”意為:核心節奏
樂譜第1小節里這個核心節奏由一個短時值的裝飾音與長時值的二分音符構成。長音與短音之間的對比與沖突,成為全曲矛盾性表現的開端。下行音程好像是進入地獄的層層階梯,每一個八度的重復音如同邁向地獄的腳步聲,營造著極度的恐懼感。
2)“雙線”意為:由核心節奏直接或間接衍生的兩個“基本奏網絡”
由于不同的節奏分割,形成音樂的矛盾與對比。作品中的基本節奏網絡主要分為兩類節奏語匯:
核心節奏的直接衍生——形成以“2”為基礎分割的主導性節奏語匯;核心節奏的間接衍生——形成以“3”為基礎分割的對比性節奏語匯。
A.在樂譜第1小節核心節奏基本等同于第20小節中出現的節奏。
B.樂譜第2小節是核心節奏的加快形式。
C.樂譜第21小節八分休止符表現了有聲與無聲間的對比,使音樂情緒在加劇的恐慌與緊張中略帶著顫抖感。
D.在樂譜第194小節與帶有八分音符休止符的節奏C相比,在有緊張感的同時,則更具有持續性與推動力。
E.在樂譜第30小節里節奏以交錯密集出現的十六分音符組合,是此節奏網絡的最短時值的語匯。
對比性節奏語匯基本網絡節奏圖:
A.樂譜第90小節出現的三連音,是節奏由松至緊、由穩定至不穩定,是音樂形象加劇收緊的表現。這樣的節奏密集性的表現,更生動地表現出地獄那陰暗、凄慘的黑暗世界,以及在魔鬼誘惑與折磨中人的悲慘。
B.樂譜第124小節出現了兩個三連音的變化節奏,不同拍位的八分音符休止,在橫向上形成了兩個欲停又走、欲走又停的三連音節奏;在縱向上,又通過節奏的交錯填補形成了強烈的不穩定性,表現了人內心糾纏著的痛苦。
C.樂譜第84小節高聲部出現的六連音節奏具有雙重性。3+3或2+2+2,不同的節拍組合表達著不同的音樂表現需要。
3)“多層面”意為:兩個或多個節奏語匯所形成的節奏對置
兩個或多個節奏語匯結合使用,形成多層面的復合性節奏。在一個空間里,每個層面的節奏以不同的節奏特征獨立存在,通過交替、疊加等方式結合形成一個多層次的節奏空間,更為鮮明地刻畫出音樂的含義。
A.樂譜第95小節處出現了兩個節奏語匯組的首次碰撞的:對比性節奏語匯A與主導性節奏語匯B,各為分離,又互為結合,三連音節奏的不穩定性,加上帶休止符的符點節奏所傳遞出的恐懼感,形成了強烈的沖突感。這樣的節奏對置,在樂曲的多處出現。
B.樂譜第157-158小節是極柔美的樂句,由縱向的四個節奏層面構成。其中旋律節奏與低音支架節奏,形成一個外部的框架,低音正拍進入的節奏推動著后六分之一拍進入的旋律線條,此外,中間的兩個背景節奏以六連音與四連音的節奏律動,形成了一個內部的緊密交錯,“三等分”與“二等分”的不同節奏分割語匯組合運用,有著強烈的不穩定性,是一種痛苦、彷徨、不安的最深層的表現。
C.在樂譜第339-342小節同樣是縱向四個節奏層面,它們在相對的獨立中,又分別組合,構成節奏的多織體、復合性的表現。由不同形態的三連音節奏構成了一個錯落有致與交替性的節奏組合,其間八分音符的休止形成了節奏橫向進行的“疏密有致',與縱向進行的“犬齒相交”,具有極強的立體感。
二、人性主題——“人”
在《煉獄》篇的文學思想表達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愛、溫順和寬恕。因此與《地獄》篇可怕的、使人壓抑的氣氛不同是,這里有著一份溫和、平靜之感。盡管地獄中的懲戒是極為嚴厲的,但人們知道,經過痛苦的凈化之后,等待他們的是上天美好的安排。然而,這個從苦難到幸福的歷程依然是艱辛無比,軟弱而易動搖的人始終會處于天堂與地獄的掙扎與彷徨之中,時而會聽從上帝的昭示;時而也會經受不住魔鬼的誘惑。
在《但丁奏鳴曲》的第二部分音樂中,李斯特所呈現的仿佛是那些人世間情感的紛繁復雜,糾纏交織。我們有理由相信,《但丁奏鳴曲》作為一部被人們長期注意的李斯特的重要作品,其創作意義不僅僅是作曲家在閱讀完《神曲》后單純地表達但丁所描述的“悲嘆、倨傲、淫亂、憎惡、饑餓”的地獄景象。而更是因為在這位作曲家的內心深處,存有著一種與文學作品表達的強烈共鳴,這種共鳴正是其音樂表現的精神內涵。樂曲中每一種情感不僅表達著人與生俱來的復雜性,更是作曲家多面性的個性特征與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也許在其本身性格中所存有的“掙扎性”、“魔性”、“神性”正是李斯特一生行為的總結。
1.音樂中“掙扎之人”的表現
《煉獄》描寫的是懺悔罪過的靈魂在接受凈化后將得到寬恕并獲得重生。但這個“洗禮”的過程卻是極為艱辛的。人的靈魂需要經歷深刻悔悟——洗刷罪孽——等待審判——重獲新生。在這個過程中“人”將始終于上帝與魔鬼兩者的掙扎中,在《但丁奏鳴曲》的第二部分音樂中,這樣的情感表達占據主導地位,它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情感的“掙扎性”。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1)深刻懺悔時的內心彷徨
在樂譜第124-135小節中由高聲部八度音歌唱出的半音旋律,仿佛向我們講述著在地獄中保羅和弗朗齊絲卡這對癡情戀人的悲劇性的遭遇。三個遞進式的樂句,通過半音線條的進行,情感表達得格外的凄楚動人。131小節與133小節兩次出現的同音反復D#音,如泣如訴地表達著這對情人追求愛情自由的無限向往,但因為受到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禮教習俗的制約,他們必須受到懲罰,內心的悔悟與向往愛情自由之間的矛盾,使他們彷徨,形成了一種無奈的掙扎感。而在李斯特的現實生活中,同樣也有著如此經歷。當時年輕的他,深愛瑪麗?德?阿古,與這位伯爵夫人的結合,顯然不受社會道德的認同。向往自由愛情的同時受到道德倫理的制約,這樣的矛盾與掙扎同樣糾纏著這位年輕的作曲家,內心的彷徨之感是他的音樂表現與文學作品之間的一種共鳴的體現。這部分的材料在之后出現的273-289小節再次出現,既是一種呼應,又是一種強調。
2)欲求解脫時的“重生”希望
在樂譜第167-180小節中三次重復出現,并逐步加快、加強的旋律線條,伴隨著有著強烈交織性的節奏,像是描述著尋求從痛苦中解脫的人們,內心的“欲望之火”不斷地燃燒與升高,但這種“欲望”并非來自于魔鬼的誘惑,而是人自身所希望的理智解放與美好向往,這同樣也符合于但丁的文學思想。在這里,音樂中所表現出人的“掙扎性”不再是痛苦的彷徨,取而代之的是人對擺脫苦難,祈求獲得“新生”的急切追求。人將永遠處于欲想得到解脫,又不敢相信可以完全解脫的矛盾掙扎中。音樂術語“accelerando”、“sempre accelerando”、“rinforzando”、“appassionato assai”的標識正是這種人在掙扎中欲求“重生”的最佳證明。音樂上這種“遞進式”的表達手法,同樣也出現于211-223小節中,三次上行小三度關系的轉調“Ab大調—B大調—D大調”,表現出人擺脫黑暗,爭取光明的強烈愿望。
2.音樂中“魔性之人”的表現
在樂譜第181-188小節中作為地獄主題音樂形象的再次出現,此處的音樂已不再是對地獄恐怖環境的表達,而是揭示出人性中所存有的“魔性”面。以“三全音”塑造出的“魔鬼”形象,在“pp”極弱的音響中出現。整段音樂“sotto voce”低聲的奏出,更突出了“魔”的神秘性與隱蔽性。因為對于人而言,“魔性”的一面往往是隱藏于內心最深處的,它與其它的情感不同,人在受到魔鬼誘惑后,那些不被宗教教義所允許的欲望在內心不斷膨脹,189-198小節中出現的“tremolando”奏法的十六分音符表達的正是人處于一種極度的不安與焦躁之中,而在此句低聲部間隔出現的三連音節奏的上下行樂句,表現的是人的內心被強烈地撕扯,但卻找不到正確的方向。這一切的感受與表現,這個存在于人們最內在世界里的“魔”是始作俑者。
3.音樂中“神性之人”的表現
在樂譜第136-144小節中F#大調上出現的這個樂段像是一首祝福的贊美詩,這里表現了人在接受了上帝昭示后,內心所獲得的溫和與平靜之感,以及對上帝的無比崇敬之情。表達了人對永恒幸福的美好向往。這個F#大調的調性色彩也同樣被運用于李斯特的同時期的其它作品中,如:詩與宗教的和諧中的部分曲目,以及《旅行歲月第三卷》之“艾斯特莊的噴泉”。在此處的音樂中,人用一種高尚的情感表達著他們的愛,正如同但丁對貝雅特里齊的愛一樣。但丁終其一生都在寫詩獻給這位他所心愛的女子,因為詩人認為她是上帝派到人間,啟迪他靈魂的天使。同樣,在當時李斯特的心目中瑪麗?德?阿古具有這樣的地位,在1834年喬治桑的小說中提及李斯特本人曾經狂喜地表達道:“天堂是兩個靈魂在愛中的融合,無論在那里都可以感覺到,不管是圣徒或是罪人。”顯然,李斯特在這位伯爵夫人身上找到了但丁文學中的原型,以同樣的情感表達著他對瑪麗?德?阿古灼熱的愛。把美好的向往寄托于平和的情感表達中,作曲家用人的理性感情構建出音樂中高尚的和諧之美。
三、上帝主題——“神”
《天國》篇文學表達的主要目的是宣揚天國的整體和諧和眾圣人所享受的神奇的安寧。在這里,沒有苦難、沒有邪惡,在九重天居住著的靈魂,按照他們在人間所建立的功德,分成各個等級,不同程度地接受上帝的光輝,享受瞻仰上帝圣容的幸福。“光明的天國”是文學中含有象征性的隱喻手法,詩人但丁以此隱喻來啟迪人們的思想,這樣隱喻性的表現同樣也存在于李斯特《但丁奏鳴曲》的音樂中。
1.音樂中文學隱喻性的表現
《神曲》之所以稱其為“喜劇”,一則是因為它采用中等體裁,是為有一般文化水平的普通人而寫作的作品。而更深層的意義是在于,“天國”是真理與至善的象征,《地獄》、《煉獄》、《天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一部對未來充滿“美好理想”的作品。在整部文學巨作中,有兩位人物形象始終在精神上支持著但丁。一位是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象征帝國理想與人的理性)他解救了但丁,引導他走出迷途。另一位便是但丁青年時代的戀人貝雅特里齊(象征神學以及上天的恩賜),將但丁引入天國,瞻仰上帝。這也就是文學作品中“Beatrice leading dante”譯為““貝雅特里齊引領但丁”的精神內涵。
同樣,在《但丁奏鳴曲》第三部分的音樂中關于上帝主題的表現中有兩個方面與文學中隱喻性相聯系:
1)浪漫主義愛情的典范——把人“神”化
瑪麗?德?阿古是被但丁譽為“精神導師”的貝雅特里齊,在李斯特現實生活中的化身。毋庸置疑,在旅行歲月的創作中,她是青年李斯特心目中的貝雅特里齊。作為一位在他生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女人,他們的愛情史是由1833-1844年間及其以后歲月發生的無數情節與插曲構成的。她不僅是李斯特第一位生活的伴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他青年時期的精神導師。
文學中宣揚的浪漫主義愛情典范是把人物形象“神”化。對于但丁而言,貝雅特里齊的隱喻形象不僅是象征神學與智慧的女神,更是拯救詩人靈魂,使其擺脫世間痛苦,來到上帝面前,享受喜樂的恩賜。在李斯特致伯爵夫人的書信中,作曲家這樣表達:
現在您可以更為清楚地了解到,在我的生命中僅存的一個念想便是“上帝”。
我們知道在這里李斯特所表達的“上帝”是具有隱喻性的,他像是“晨禱者”一般虔誠地向著他心目中的“上帝”表達著愛意。
瑪麗,瑪麗,請張開您的臂膀來擁抱我,用您的愛來溫暖我那赤裸、寒冷的靈魂……片刻間為我驅散所有的痛苦……拯救我的靈魂。
這里瑪麗像是一為高貴的女神。她具有高尚、仁慈的品格與光輝的形象。
啊!瑪麗,瑪麗,再愛我一次吧,讓我的生命再次鮮活……你的淚水如同天上的露珠一般,能滋潤我那枯萎疲憊的心……瑪麗,把你靈魂的語言教給我吧……因為沒有你,我就再沒有快樂,沒有陽光,沒有自然,沒有上帝,沒有廟宇,沒有生命。
雖然在李斯特的書信中,并沒有直接表達過瑪麗?德?阿古就是但丁筆下的貝雅特里齊,但他卻感受到瑪麗可以使他失落消散,拯救他靈魂的痛苦。這足以說明,這位伯爵夫人在他心目中具有的崇高地位,也符合浪漫主義所表達的愛情“把人神化”。
在樂譜第290-299小節,第300-305小節和第306-317小節中這個“神性”的主題在高聲部再現,D大調的調性色彩,象征著光明與美好,在輕聲地吟唱中音樂表現了李斯特對于上帝所賜予的這份浪漫主義愛情美好的向往與虔誠的感謝。在經過300-305小節,若干個遞進式上行之后,306-317小節再度出現的由大三和弦構成的這個“神性”主題,仿佛是李斯特對他心中的這個“上帝”的歌頌與贊美。
2)追求宗教信仰的高尚情懷
《但丁》詩歌中的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形象,也同樣出現于李斯特的音樂中。在作曲家心中始終存有著一種能獲得精神上平衡的理性希望,也許這種希望只有上帝能夠賜予。我們如果可以在《但丁奏鳴曲》中發現音樂家這一宗教情感的需要與愿望,就不會為他53歲那年接受修道院院長這樣的一個圣職,而感到驚訝了。
李斯特終其一生都處于一種復雜的矛盾中:
向往獨處的寧靜,但無法離開社交活動而生存;
夢想簡樸的生活,卻不能舍棄金錢世界的誘惑;
頌揚美好的自然,而無法忍受鄉村生活的無聊;
喜愛單純的樣子,但不能擺脫不安心靈的焦躁;
宣揚思想的民主,而依然屈從上層階級的貴族。
顯然,這樣復雜的矛盾性需要精神上的解脫,從而求得平衡。這里音樂表現的精神內涵,再一次與但丁文學思想相吻合。人的靈魂在獲得上帝的昭示后,享受著光明與幸福。
樂譜第327-373小節為全曲的高潮樂段,這個瞻仰上帝的光輝主題即是樂曲最后的總結,也是其音樂精神內涵的集中體現——從黑暗到光明;從苦難到幸福。所有之前出現過的音樂材料在D大調的光明調性色彩中得到重現,在這里沒有恐懼與掙扎,所有的大調和聲構建出一個輝煌、宏偉的音響空間,表現著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對上帝至上榮耀的贊美。
縱觀全曲,李斯特表現的音樂精神內涵與但丁《神曲》的文學主題緊密相聯。《神曲》以黑暗的《地獄》篇起始,歷經艱辛“洗禮”的《煉獄》篇,而最終以光明的《天國》篇完滿結束,構成了一部理想的“喜劇”。而李斯特把人生滲透于哲學,把“魔性”與“神性”,代表黑暗與光明的兩個矛盾對立面,通過“人性”的轉化,相為滲透、互為貫通,推動著音樂在矛盾中發展,在和諧中統一。其貫穿一生的音樂精神內涵表現為:在“魔性”中爭斗;在“神性”中統一。(責任編輯:陳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