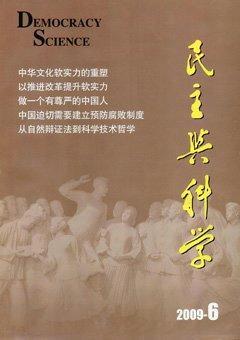為尊嚴(yán)討一個(gè)“說法”
30年的改革成就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令人震驚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廣袤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上,也體現(xiàn)在人們的思想解放和社會(huì)觀念的轉(zhuǎn)變之中。個(gè)人意識(shí)逐漸覺醒,每個(gè)人都開始思考,尋找各具個(gè)性的人生意義。
人和人不一樣: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小人;有活人,有死人……
有的人,當(dāng)了股長、科長、總經(jīng)理,成了“大人”,但其思維和行動(dòng)卻仍在“小人”的圈子里不可自拔。古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說,大概就是指的這些人。大人們也有想當(dāng)英雄流芳百世的,但正是他們卻恰恰忘記了伏契克所說的:“英雄——就是這樣一個(gè)人,他在決定性關(guān)頭做了為人類社會(huì)利益所需要做的事。”有的人自恃有高官厚祿,勒索特權(quán),卻忘了是誰供奉他們,抬他們高坐于殿堂之上。
有的人,庶民百姓一個(gè),清風(fēng)兩袖一雙,被“大人”們斥為“小人”。但正是他們,“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他們,“擺脫冷氣,積極向上,能做事的做事,能發(fā)聲的發(fā)聲,有一份熱,發(fā)一份光,即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fā)一點(diǎn)光”。歷史常常無情地告誡“大人”(他們老愛健忘),世界正是由這樣無數(shù)的“小人”們創(chuàng)造的。一旦小人們站起來了,他們還小么?
有的人,雖然活著,卻似死了一般。雖然當(dāng)面有人向他獻(xiàn)媚、奉承,但背地里卻被人指著脊梁,詛咒早點(diǎn)去見上帝(不是去見馬克思)!雖然他們衣錦食豐,但其精神早已極度空虛。他們與草木同腐,與醉夢同生,日夜操著坑人的勾當(dāng),陰暗角落里經(jīng)常可窺見他們的嘴臉。這些遭受人民唾棄的人,還配做一個(gè)真正的人么?
有的人,雖然死去,卻“留取丹心照汗青”,十里長街永駐送行人。雖然他們的心臟已經(jīng)停止跳動(dòng),但大眾的脈搏仍和他們在一起跳動(dòng),雖然他們的身軀已化作塵埃,但大地永記他們的情愫!
有的人活著似一具腐尸散發(fā)著臭氣,有的人死去,卻似春蠶吐著縷縷絨絲;有的人活著,似一條蛆蟲蛀食著共和國的大廈,有的人死去,卻似燭光一盞照亮人們攀登之途;有的人活著,儼如一條叭兒狗奴性十足,俯拜于沒落亡靈的腳下,有的人死去,卻似蒼松追求真理,挺拔向上,任爾東西南北風(fēng);有的人活著,好像一朵無果之花,有的人死去,卻似黃牛仍然辛勤地耕耘在廣袤的沃土上……
一撇一捺,便寫成個(gè)“人”字,著實(shí)簡單,但要做一個(gè)真正的人,卻不那么容易。我們不妨問一下自己:我活的有尊嚴(yán)嗎?
人活在世上都是有尊嚴(yán)的,曾看到葛劍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心中一亮。葛先生認(rèn)為:“人的生命、人的尊嚴(yán)是第一位的,當(dāng)人類與其他生物或非生物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shí),我們只能先考慮人類。”這意思是說,人類高于自然,為了保證人類的生命和尊嚴(yán)可以侵奪自然的利益。
對于尊嚴(yán),不同的時(shí)代會(huì)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數(shù)時(shí)候,人的尊嚴(yán)并不表現(xiàn)為占有,而是表現(xiàn)為放棄,表現(xiàn)為有原則地拒絕。比如在泰坦尼克號(hào)的沉沒中,一直堅(jiān)持演奏的樂手們是有尊嚴(yán)的,而那位憑借一把子力氣搶到了救生艙位置的男人,即使獲得了生命,也是沒有尊嚴(yán)的。在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上,放棄對自然的肆意掠奪,過簡樸簡單的生活,并不會(huì)使我們失去尊嚴(yán),反而會(huì)使我們獲得尊嚴(yán)。
尊嚴(yán)還需要權(quán)利來維護(hù)。我們都擁有做人的權(quán)力——做男人的權(quán)力,做女人的權(quán)力,做上司的權(quán)力,做下屬的權(quán)力,做朋友、路人的權(quán)利,做師長、晚輩的權(quán)利。只要我在社會(huì)中生活,我就有行使社會(huì)角色的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利給我以保護(hù),保護(hù)我能完全有效地行使社會(huì)的職能,保護(hù)我們的尊嚴(yán)不受他人的侵犯。
曾經(jīng)看過一部電影《秋菊打官司》,對電影本身倒是沒有什么想說的,關(guān)于它藝術(shù)上的創(chuàng)新和追求,也已有文學(xué)家們的不少評論。我這里要說的是影片自始至終的未解之謎——“說法”是個(gè)啥東西,影片為啥就是不給秋菊一個(gè)讓她滿意的“說法”?
影片的情節(jié)并不復(fù)雜,村長在與秋菊男人的爭吵中踢了一下他那“要命的地方”,使其“要命的地方”出現(xiàn)輕度的水腫。按照鄉(xiāng)政府李公安的調(diào)解,村長賠償秋菊男人醫(yī)療損失費(fèi)200元也就算可以的了——要是在其他鄉(xiāng),村長打的人是普通村民,不僅沒有什么賠的可能,村民還要向村長送禮賠情,讓村長消消氣——更何況秋菊男人也罵了村長“斷子絕孫的話”。按說這樣處理也就夠可以的了,秋菊也該識(shí)國情,況且村長還很大度——如果賠錢不依就張開腿也讓秋菊的男人朝他“要命的地方”回踢一腳。可是秋菊不干,她不愿意彎下腰去一張一張拾起村長甩下的20張10元人民幣。于是劇情一跌三宕,官司打到縣里打到市里,賠償金額增加到250元,最終把村長押上了警車。可是,秋菊苦苦索要的“說法”呢,始終沒有得到——從她那緊緊追趕的腳步聲中,從她那目送警車失望的眼神中可以得到印證。
一樁并不復(fù)雜的民事、刑事案件為何搞得如此復(fù)雜?其主要原因就是一個(gè)新時(shí)代的新女性為要一個(gè)“說法”而不肯罷休;李公安、吳律師、嚴(yán)局長都是一個(gè)個(gè)大好人,但始終都沒有給秋菊一個(gè)“說法”。這是粗心的編導(dǎo)們的疏忽,還是高明的編導(dǎo)們留給我們深深思考的一個(gè)嚴(yán)肅課題?
什么是秋菊死死追求的“說法”呢?這就是常常被人們特別是某些大人們包括像村長這樣的“大人物”忽略的人的尊嚴(yán),一個(gè)人生活在社會(huì)上最起碼的做人的公正權(quán)利。也許有人會(huì)說,村長不是同意賠償秋菊男人的經(jīng)濟(jì)損失了么,法院不是最終把村長抓去了么?不錯(cuò),這些都是事實(shí)。但是,影片中自始至終都沒有村長向秋菊認(rèn)錯(cuò)的一句話,特別是當(dāng)村長的不該隨便打村民這樣的內(nèi)容。非但沒有,還有輕視、侮辱和報(bào)復(fù)的行為或意思。秋菊所要的“說法”就是要屬于她和她的男人應(yīng)該享有的人的平等權(quán)利。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告訴我們,人的自尊需要是人的高層次追求。但是,長期以來這個(gè)最能體現(xiàn)人的人格的東西卻往往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忘記了。在經(jīng)濟(jì)落后的社會(huì),人們(主要是勞動(dòng)者)不可能要求社會(huì)承認(rèn)自己的存在,這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但社會(huì)發(fā)展到了今天——科學(xué)和民主的時(shí)代,如果有誰還想用金錢和刑役來取代人們對人格、尊嚴(yán)的享有,那就大錯(cuò)特錯(cuò)了。影片中有這樣的人,社會(huì)中也有這樣的人。前幾年云南省丘北縣不是發(fā)生過罰活的人為當(dāng)官者的死狗披麻戴孝的事情么!北京街頭不是也有過明星開車撞人而揚(yáng)言“要多少錢我賠”的傳聞么!在這些人的眼中,不知人的尊嚴(yán)值幾何!看來,我們這方面的宣傳還是太少。
感謝文藝界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部好影片,不僅僅是電影藝術(shù)方面的,也不僅僅是法制建設(shè)方面的,它涉及所有人的存在和發(fā)展——這大概就是秋菊所追求的那個(gè)“說法”吧?
人活在世上不容易,特別是當(dāng)人權(quán)寫進(jìn)了國家的憲法,關(guān)于如何做好人,如何保障人權(quán)的問題就越來越多——我們都來認(rèn)真對待它。
編后:本文選自趙振宇所著《我們說了些什么》一書。作者以一個(gè)新聞學(xué)教授的責(zé)任感,以紀(jì)實(shí)的方式將社會(huì)變革、新聞報(bào)道和理論思考融為一體,回眸了30年來我國民主進(jìn)程中發(fā)生的重大變革、典型事件、媒體對此的評論,以及一代知識(shí)分子的思考。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