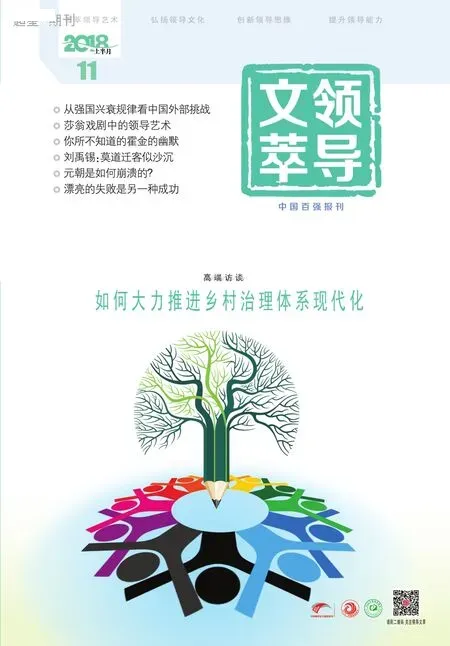黨內民主重在授權民主
舒泰峰
最關鍵的是授權階段的民主,這個階段的民主與其他方面相比顯得不配套
6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問題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
在建黨88周年前夕,這樣的集體學習耐人尋味。同一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其中指出,“要擴大考核民主,強化黨內外干部群眾的參與和監督。”
而此前的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專家解讀說,這意味著今后除了行政官員,黨的序列的干部也將面臨問責。
一系列信號都顯示,中央高層高度關注黨內民主問題。
就推動黨內民主的“路線圖”和關鍵點,本刊采訪了著名政治學者、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和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霞。
以“民主”破除“官主”
《瞭望東方周刊》:黨內民主建設應當從哪個環節進行突破?
王長江:中國的黨內民主已經進入了整體推進的階段。
這就是說,不應該把民主看作一種簡單的現象,一說民主好像就是選舉,就是老百姓說了算,就是領導聽聽老百姓的意見,這些都是不全面的。真正的民主是一整套系統。
民主體現在各個環節。最基本的一點,授權的過程必須民主。
權力是老百姓的,但老百姓不可能直接當決策者,行使權力,因而必須有授權過程,有多數人把權力交給少數人的過程。
在授權環節,通過一定的程序,大眾把權力交給掌權者,通常通過選舉的方式進行。我們或許也可以用別的方式,但授權的程序必須民主。
這個權是老百姓給的,因而使用的時候也必須有老百姓的參與——既包括決策,也包括執行。這是第二個環節。
第三個環節,有了權不光是為大家服務的,也可能為自己服務,因此,權力行使的整個過程就要讓大家看得到,接受老百姓的質疑,這是民主監督。
民主要在所有這些環節上去推進。應當說,我們的黨內民主確實也在不斷推進,比如干部推薦,比如權力運行透明化,比如輿論監督等。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沒有把黨內民主當作整體來看待。
現在看來,最關鍵的是授權階段的民主,這個階段的民主與其他方面相比顯得不配套。
目前,我們有的只是小范圍內的民主,甚至有人說這是“官主”,官選官。很多地方都有公推公選,這比過去肯定有進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參加,處級的推薦局級的,局級的推薦部級的,還有很大局限。這樣的推薦,往往容易出現老好人,拉票、賄選也可能因之出現。這方面的民主如果不向前推進,其他環節很難繼續前行。
我最想說的是,今后民主向前推進,最基本的一點是要整體推進;同時,整體里邊最弱的就是授權階段的民主,這相當于木桶效應里邊那塊最短的木板,需要趕緊提升起來。
29歲市長的事情為什么引起這么大爭議,大家質疑的不是他有多年輕,而是他怎么當的。如果還是變相任命,再年輕又有什么意義呢?因此,關鍵不是授權給誰,而是怎么授權。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老想解決授權給誰的問題。一說腐敗,就想把最有道德的人選上來。這個思路不對,關鍵還是要讓老百姓和普通黨員來判斷。
建議縣以下直選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老百姓會不會判斷錯呢?
王長江:當然,老百姓也不是萬能的,所以能選他上去還得有辦法能把他弄下來。有授權也有收權。
我們現在為什么上去容易,下來難?比如有的村官競選的時候什么都敢承諾,當選后什么都不兌現,但讓他下臺非常困難。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到操作,現階段如果我們放開授權環節的民主,到哪個層級是合適的?
王長江:授權民主從整體上來說必須是徹底的,但是授權的方式的確需要考慮。有人說,既然老百姓、黨員說了算,那么就各個層面都搞直選,在我國可能不能這么簡單處理。但在和民眾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那些層面,應該由民眾直接選。在村里、鄉鎮、縣一級都應該如此。
我把縣作為比較關鍵的一條線,真正把這個做扎實了,再往前就好走了。
僅有雙規收權還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對黨內民主進行一套制度設計,你有何建議?
蔡霞:黨內民主應當是一套制度鏈,其邏輯前提是以黨員的權利為主體,黨員是黨內的主人。實際的邏輯起點是黨內選舉,也即黨內的授權制度,把權力授予領導機關和干部。授權后,有黨內的權力的監督問題,其中實質性的問題,是黨代表大會、黨委會和紀檢委三者之間的關系。
這個框架設置后,下來就是權力的運轉機制。首先是黨代表大會制度,它不能簡單理解為開會,其中應當有黨委報告工作制、黨代表審議制、議案提出制度等。
這套制度設計應以黨代表大會為核心,因為它是黨內的權力機關。應由黨員選出黨代表,黨代表大會來進行監督制約,交由黨委會執行。
第二個是黨委會的集體領導制度,當中應當有黨委會的議事規則、表決規則,還有決策的責任追究制度等。接下來是黨務公開,應該包括情況的通報,黨員討論黨內事務以及黨內監督制度。
最后一個機制,就是權力如何收回,即收權制度的安排。我們現在是選舉制度不健全,收權制度幾乎沒有。現有的收權主要是退休和雙規收權,不出問題不收權。
科學收權應實行任期制,沒被選上去就應該下來,也不應該去別的位置去掌別的權。這是與選舉相配套的。
其實選舉解決了授權和收權兩個問題。而在權力運轉當中出現情況,如何終止他的權力?這就要有黨內彈劾制度、黨內罷免和撤換制度。
我們現在沒有彈劾機制,罷免和撤換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誰有權力罷免,前者寫的是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委員,而后者則規定黨員有此權利。
選舉就是授權,誰授權就應該由誰收權,這應該是黨員的權利。
《瞭望東方周刊》:這套制度鏈看上去很完整,但是如何才能保證其落到實處?
蔡霞:我們長期以來形成了權力主導的結構。當權力意志大到可以控制民主,這個民主就變味了。比如《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1995年就試行,2002年正式執行,但是目前帶病提拔、用人上的潛規則依然存在。我們也有考評、集體投票,表面上看有一整套嚴密的程序,但是這套程序是自上而下的,自己運作,自己評價,自己控制結果。體現的是自上而下的權力意志。這種用人權上的民主就變成了有限放開,不是把黨員的權利看作不可剝奪的,而是可聽可不聽。所以用人上的問題控制不了。
我想強調,制度的靈魂,關鍵在程序而不在于僅僅有選舉。制度沒有程序,就是個口號。而所有的程序設計都要保證黨員權利的行使。(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