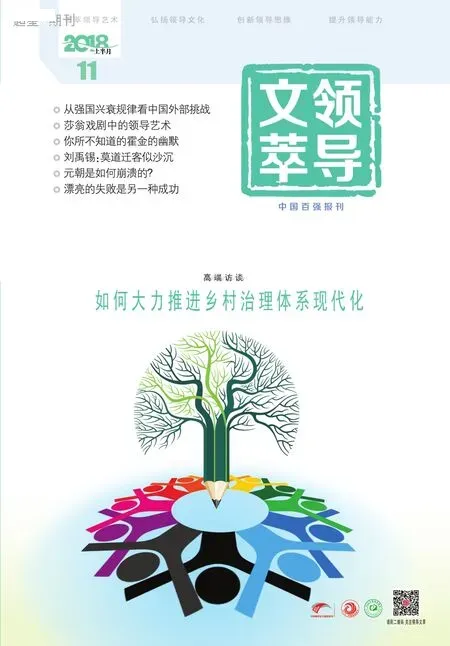不能對信任危機掉以輕心
鄭永年
現在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危機之一,就是各群體之間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機,而這種危機是有可能深化和轉變成為深刻的社會危機的。
例如,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國的就業問題變得嚴峻起來。于是,中央政府強調各級政府要做好就業工作,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作。但當有關部門關于大學生的就業數據發布之后,馬上就被大學生網民嘲諷為“被就業”。官方的其他一些“權威”數據,也屢屢遭到社會和公眾的懷疑。
民眾不信任成“思維定式”
盡管很多人知道有這種不信任的存在,但不是很多人對這種信任危機的惡果有深刻認識。可以肯定地說,只要這種不信任存在,建設和諧社會就困難重重,甚至會導致更加深刻的社會危機。
一些民眾對地方政府和部門的不信任,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客觀上,比如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地方政府和部門想方設法地想完成中央的“任務”或者“指標”,因此就千方百計地搞些花樣來欺騙中央,而實際上很多大學生并沒有真正“就業”,這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績觀、唯GDP論的思維,對民眾的利益造成了實質性傷害。比如因地方政府大拆大建形成的社會拆遷矛盾,犧牲環境利益發展地方經濟給民眾健康造成的危害。另外,地方政府官員屢見不鮮的腐敗現象,并不時發生的“官欺民”的事件,這些都在消耗民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對于民眾來說,正是因為這些經驗層面上的事情發生多了,時間一長,民眾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這種不信任的“主觀思維定式”,結果是民眾對政府總是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真正披露了事實真相,也同樣難以獲得民眾的相信,比如不久前河南杞縣“核謠言”導致大批民眾離城事件就是明例。應當說,民眾的這種“思維定式”對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
“欺上瞞下”是不信任根源
民眾為什么會對地方政府和部門產生不信任?如果把民眾和政府分成兩個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領域,那么民眾這個社會領域對政治領域的不信任是政治領域內部不信任的外部延伸。
有人說,中國的一些政策從一開始制定就缺乏深入研究,執行政策的官員心知肚明,根本就執行不起來。到了政策執行面,問題就更大。一些政策,中央政府的確經過深思熟慮,但就是執行不下去,關鍵卡在“中間層”,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體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點。表面上,“唯上”表示政策執行只需要對上負責,但是因為沒有“唯下”的機制,“唯上”很多時候會演變成為“欺上”。對于中央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變著法子打折扣執行。再者,因為政治和決策過程不對社會開放,社會與地方政府沒有實質性的溝通管道。也就是說,當不存在任何能夠促使中間層官員“唯下”的情況下,“瞞下”也具有必然性。進而,因為可以輕易“瞞下”,對這些官員來說,“欺上”遠比實實在在的政策執行要容易得多。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官員在“欺上瞞下”的同時,卻又不會欺騙自己的利益。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的政策就很可能演變成為中間層官員的“尋租”工具,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從不執行政策或者變相地執行政策中獲得巨大利益。在整個過程中,社會和民眾相對比較被動,其決策參與權和對政策執行的監督權十分有限,并且利益常常受到官員的侵犯,這是社會對地方政府和部門不信任的最主要根源。
把更多權力下放給社會
無論哪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任何理由對民眾的不信任掉以輕心。要跳出信任危機,避免演變為重大的社會危機,必須建立起中央政府同基層政府以及社會民眾的直接關系。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中間層過于龐大,所以中央政府應把部分權力從中間層收回,再下放給基層政府。當然,光把權力下放給基層政府還遠遠不夠,因為基層政府和官員同樣也會出現腐敗現象。因此,在向基層政府分權的同時,也必須把部分監督權力下放給社會。只有到了社會成為政治、決策和政策執行的內在因素的時候,中間層官員的“瞞下”和“不唯下”行為才會得到根本的糾正;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欺上”和假“唯上”也才能得到糾正。一句話,只有當社會成為權力產生和使用過程的內在部分的時候,政府才能建立起社會的真正相互信任,社會也才能找到信任政府的根本而牢靠的理由。
(摘自《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