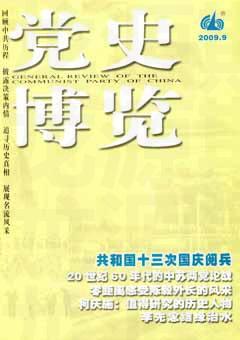零距離感受陳毅外長(zhǎng)的風(fēng)采
李景賢
毛澤東“布子”,陳毅躊躇
新中國(guó)成立伊始,外交部長(zhǎng)一職由周恩來總理兼任。但他的政務(wù)活動(dòng)過于繁忙,他這個(gè)人又舉輕若重,事必躬親,勞心、勞力、勞神。大約四年過后,毛澤東同志為減其負(fù),萌生出“外交換帥”的念頭,并暗中“布子”,將其鎖定在井岡山時(shí)期的老戰(zhàn)友陳毅身上。在這位中國(guó)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心口中,陳毅人才難得,政治上強(qiáng),既有戰(zhàn)略頭腦,又有外交才華。1954年秋天,陳毅從上海市長(zhǎng)的崗位上被調(diào)到北京任副總雕,他預(yù)感到將要接任外交部長(zhǎng)一職。
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huì)上,陳毅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其副總理的分量明顯加重,由他兼任外長(zhǎng),已是鐵板釘釘?shù)氖隆2贿^,陳毅并沒有立即挑起這副重?fù)?dān),這里面事出有因。當(dāng)年他在西藏考察時(shí),因高原反應(yīng)而頭疼不已,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駐華大使舉行的一次電影招待會(huì)上,陳毅突然暈倒。之后,他便向中央告假,療養(yǎng)了一年。1958年2月,陳毅副總理才開始兼任外長(zhǎng)一職。
面對(duì)毛澤東親自點(diǎn)將,一向心胸坦蕩的陳毅曾一度忐忑不安。他這個(gè)人有自知之明,對(duì)能否挑起、挑好外交這副重?fù)?dān)。心里沒底。一是因?yàn)椋鳛樾轮袊?guó)首任外長(zhǎng)的周恩來,在國(guó)際舞臺(tái)上叱咤風(fēng)云多年,被公認(rèn)為全世界罕見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項(xiàng)背;二是因?yàn)椋愐闵钪约河幸粋€(gè)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覺得這種不良習(xí)性對(duì)一個(gè)外長(zhǎng)來說是斂命的,擔(dān)心會(huì)因此“砸鍋”,誤了黨和國(guó)家的大事。
在接過外交重?fù)?dān)之前,陳毅曾坦蕩蕩地推辭說:“我這個(gè)陳毅,有時(shí)候說話很有破壞性,有時(shí)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來說話就沖口而出,不管輕的。在我們內(nèi)部,對(duì)同志有什么傷害,可以對(duì)同志解釋;在外交上這么一來可就砸鍋了。”對(duì)夫人張茜,他說得就更直:“我這次兼任外長(zhǎng),可能有四種結(jié)果:第一個(gè)是干出成績(jī),第二個(gè)是一般化,第三個(gè)是犯大錯(cuò),第四個(gè)是得大病。”
陳毅在中國(guó)外長(zhǎng)這一崗位上名義上工作了十三四年,直至1972年辭世。但是,在“文革”開始后,他就逐漸被非法剝奪了工作的權(quán)力。在只有七八年的“有效工作時(shí)間”內(nèi),這位元帥外長(zhǎng),在國(guó)際大舞臺(tái)上,與周總理一樣叱咤風(fēng)云,為新中國(guó)外交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贏得了他所預(yù)期的第一種結(jié)果。
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鑒于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際形勢(shì)和中國(guó)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人們更多看到陳毅外長(zhǎng)“立馬橫刀”那剛性的一面,但他的才氣、文采、風(fēng)趣、人情味,他的人格魅力,電常常為知情者所稱道。外交部的人都親切地管他叫“陳老總”。1963年8月,我進(jìn)入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幸為他當(dāng)過俄語翻譯,還有機(jī)會(huì)在許多場(chǎng)合零距離目睹了這位元帥外長(zhǎng)的風(fēng)采。如今,40多年過去了,敬愛的陳老總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
鐵骨錚錚的元帥外長(zhǎng)
1965年秋天,亞洲地區(qū)的局勢(shì)變得更加緊張,在中國(guó)的對(duì)外關(guān)系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毛澤東提出,清陳老總出來向中外記者講一講。當(dāng)時(shí),陳毅正在外地,得知主席這一指示后立即往同趕,在回京的火車上,就開始緊張地準(zhǔn)備起來。
陳毅同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會(huì)。外交部翻譯處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語種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進(jìn)行同聲翻澤,領(lǐng)導(dǎo)讓我也到“前方”去體驗(yàn)和學(xué)習(xí)。
那一天,偌大的一個(gè)會(huì)場(chǎng)被三四百人擠得水泄不通。答問時(shí),陳老總訓(xùn)到了十五六個(gè)國(guó)際問題和對(duì)外關(guān)系問題。他幾乎都是即興講,時(shí)而闊論世界大勢(shì),時(shí)而推擋刁鉆的問題。在沒有多少時(shí)間進(jìn)行準(zhǔn)備的情況下,面對(duì)記者們所捉各式各樣的問題,陳老總鎮(zhèn)定自若,對(duì)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見他刈囤際大勢(shì)、國(guó)別關(guān)系與中國(guó)對(duì)外政策之精通。
這次記者會(huì)持續(xù)了近兩個(gè)半小時(shí),面對(duì)美國(guó)人的戰(zhàn)爭(zhēng)威脅,陳毅橫眉怒目,發(fā)出陣陣吼聲:
——我們等候美帝國(guó)主義打進(jìn)來,已經(jīng)等了16年!我的頭發(fā)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yùn)”能看到美帝國(guó)主義打進(jìn)中國(guó),但我兒子會(huì)看到。他們會(huì)堅(jiān)決打下去的!
——請(qǐng)記者不要以為我陳某人是個(gè)好戰(zhàn)分子,是美帝國(guó)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
——我們中國(guó)有一句老話,叫做:善存善報(bào),惡有惡報(bào),不是不報(bào),時(shí)候未到。時(shí)候一到,一切都報(bào)銷!
陳老總的話音一落,在場(chǎng)的所有中國(guó)人立即報(bào)以雷鳴般的掌聲,經(jīng)久不息。人們盡情地表達(dá)自己的激動(dòng)和振奮之情。老元帥在“一切都報(bào)”這句老話后面特意加一個(gè)“銷”字,加得實(shí)在是妙:總有一天,會(huì)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蟲”統(tǒng)統(tǒng)都給“報(bào)銷”掉!
2008年春,中央電視臺(tái)播放了一部紀(jì)念周恩來總理誕辰110周年的大型專題片,其中有一組回顧周恩來同志與陳毅同志兄弟、戰(zhàn)友情深的鏡頭。我看著看著,沒想到熒屏上出現(xiàn)了上述記者會(huì)的畫面。而且,還對(duì)陳老總當(dāng)年“一切都報(bào)銷”那聲怒吼刻意進(jìn)行了渲染。這位老元帥是位詩人。“詩如其人”,詩人那首膾炙人口的《青松》,贊美的是中國(guó)人民“壓不垮”的英勇氣概,也是這位元帥詩人的自我寫照。
陳老總這個(gè)記者會(huì)時(shí)間之長(zhǎng),聲勢(shì)之大,涉及問題之多,答問之精彩,影響之深廣,在共和國(guó)60年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我在這個(gè)記者會(huì)上聽俄語高翻的同聲傳譯,感到陳老總的骨氣、陳式語言的那種“虎氣”,全都給譯出來了。
我們搞原子彈,最終是為了消滅原子彈
我從一些介紹中國(guó)核工業(yè)發(fā)展歷程的材料中了解到,還在中國(guó)革命勝利之前,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就已經(jīng)開始關(guān)注核問題。1949年夏天,劉少奇同志秘密訪問蘇聯(lián)時(shí),就表現(xiàn)出對(duì)核問題的興趣。有一次,毛澤東回憶起新中國(guó)成立之初出訪蘇聯(lián)的感受時(shí)說:原子彈,美蘇兩家都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diǎn)嘛”。
1954年10月,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國(guó)國(guó)慶五周年慶祝活動(dòng)時(shí),毛澤東就向他表示過對(duì)核感興趣。這位蘇聯(lián)最高領(lǐng)導(dǎo)人一開始只愿給中國(guó)提供核保護(hù)傘,但鑒于自己剛上臺(tái)不久,尚需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于是就答應(yīng)幫助中國(guó)建一個(gè)小型實(shí)驗(yàn)型核反應(yīng)堆。
過了不到一個(gè)月,毛澤東就與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興致勃勃地大談原子彈,并說,“正在開始研究”那個(gè)東西,1957年夏天,赫魯曉夫通過內(nèi)部斗爭(zhēng)把莫洛托夫“反黨集團(tuán)”搞了下去,有求于毛澤東就更顯迫切。在核武器研究方面,他主動(dòng)提供了圖紙、資料,甚至設(shè)備,還向中國(guó)派出了大批核專家。但是,到了20世紀(jì)50年代末,隨著中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逐漸顯現(xiàn),赫魯曉夫于1959年夏天決定暫緩向中國(guó)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核資料,一年后,又從中國(guó)撤走了全部核專家。
上面之所以扼要地同顧一下中辦之間的核關(guān)系,是因?yàn)?963年我到外交部工作之后,曾多次在不同場(chǎng)合聽到陳老總同外國(guó)記者談核問題,隱約感覺到他對(duì)某一核大國(guó)有些不滿情緒。
有一次,有位記者說,有的核專家聲稱,世界上目前已有的原子彈,就足以毀滅地球好幾遍,問陳老總對(duì)此有何看法。他答道:不只是核專家這樣說,有一個(gè)人(指赫魯曉夫)就拿這個(gè)東西來嚇唬人。原子彈是厲害,但毛主席有句名言:原子彈是只紙老虎,這是從戰(zhàn)略上
藐視它,原子彈沒有什么了不起,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斗爭(zhēng)才是最好的原子彈。
還有一次,有位記者問陳老總:中國(guó)核計(jì)劃的目標(biāo)是什么?他答稱:這個(gè)原子彈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些有啥子用嘛!中國(guó)只搞一點(diǎn)點(diǎn)。我們窮得很,不同人家搞競(jìng)賽。至于目標(biāo)嘛,我們搞原子彈,最終是為了消滅原子彈。
要“快刀斬亂麻”,不要“鈍刀子切肉”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陳老總突然來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譯處。司領(lǐng)導(dǎo)把他請(qǐng)到司里最大的一個(gè)辦公室——俄文組。碰巧,陳老總就在靠窗我平時(shí)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來。此前,我多次見過這位開國(guó)元?jiǎng)祝€給他當(dāng)過翻譯,但坐在他身旁零距離聽他作報(bào)告,這還是第一次。
陳老總滔滔不絕地講了三四十分鐘。他老人家對(duì)我們外事翻譯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躍然“嘴”上,深深地印在我這個(gè)剛剛踏進(jìn)新中國(guó)外交門檻的新兵腦海里。下面,就引述陳老總當(dāng)時(shí)在我們翻譯處所講的、我早已爛熟于心的幾段話:
——一年365天,你們的高翻們幾乎天天跟著我,是我另一張不可缺的嘴。如果沒有這張嘴,我在人家外國(guó)人面前就成了個(gè)啞巴。因此,再忙也得來看看大家,道一聲辛苦,說一句感謝。
——主席、總理把我擺在這個(gè)位子(指外交部長(zhǎng))上,一晃就是五六年。總理太忙,外事這一大攤,我替我這位兄長(zhǎng)分擔(dān)一點(diǎn)。功勞談不上,苦勞嘛。興許還有一小點(diǎn)。其實(shí)呢,我們中國(guó)的外長(zhǎng),一直還是我們的總理。還沒有解放,他早就已經(jīng)是我們黨的“外交部長(zhǎng)”了。
——你們這里人才濟(jì)濟(jì),臥虎藏龍。你們這些“虎”呀“龍”呀,如果給我翻得快刀斬亂麻,我就高興。鈍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來——這個(gè)最要不得!
近來,人們到處講“又紅又專”。人家“紅”講得多。我就多講點(diǎn)“專”。我常常引用“藝高人膽大”這句老話。對(duì)你們這些高翻來說,“藝高”就是你們“手里”那把“快刀”。
所謂“快刀”,其實(shí)是一把“利刃”。對(duì)諸位來說,“快刀”也好,“利刀”也罷,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領(lǐng)會(huì)領(lǐng)導(dǎo)意圖準(zhǔn)。對(duì)啦,再加上一條:還要古文基礎(chǔ)好。主席見外賓時(shí),常常引用占詩詞,有時(shí)還用典。《古文觀止》、唐詩宋詞,你不往腦子里裝一些,怎么給人家翻?!當(dāng)然,都懂——也不現(xiàn)實(shí),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總是可以的吧!
在“藝高人膽大”這句后面,還有一句,叫做“膽大人藝高”。我發(fā)現(xiàn),有些高翻膽子太小,一見到我就害怕。我陳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會(huì)吃人!沒有翻你就怕,還能發(fā)揮得好?!現(xiàn)在,我當(dāng)著大家的面表個(gè)態(tài):我支持你們的工作,你就大膽地給我翻!
——我在部里常常講,一年365天,我天天管著你們,不管你服還是不服。但是,我想,一年下來,總得給半天時(shí)間,讓大家也管管我這個(gè)外交部長(zhǎng)。現(xiàn)在,我就坐在諸位面前。讓我們來“換一下位子”,請(qǐng)諸位也來管管我,給我提提意見。
寫到這里,我想指出,上面所引“人家‘紅講得多,我就多講點(diǎn)‘專”那句話,陳老總是有感而發(fā),話中有話。我清楚地記得,1962年春天,他在廣州的一個(gè)座談會(huì)上,面對(duì)知識(shí)界人士當(dāng)時(shí)所受極左思潮的壓抑,發(fā)表了一篇三萬余言的“脫帽加冕”的講話。當(dāng)時(shí),陳毅向在座的知識(shí)界人士“掏心窩子”,擲地有聲地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xué)家,社會(huì)主義的科學(xué)家,無產(chǎn)階級(jí)的科學(xué)家,是革命的知識(shí)分子,應(yīng)該取消資產(chǎn)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說著,他向全場(chǎng)的知識(shí)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針對(duì)知識(shí)分子不敢寫文章、不敢說話這種反常狀況,陳老總動(dòng)情地說:“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gè)作風(fēng)不改,危險(xiǎn)得很!”這個(gè)后來被打成“大毒草”的“爆炸性”講話,激起了全場(chǎng)60多次雷鳴般的掌聲。
我是1956年秋進(jìn)入北京外國(guó)語學(xué)院俄語系學(xué)習(xí)的。在校學(xué)習(xí)七年(本科和翻譯班)期間,陳老總時(shí)不時(shí)地單獨(dú)到我們外院,或者到北京西、北郊十大院校(聯(lián)合)作報(bào)告。我到外交部工作后,聽陳老總作報(bào)告的機(jī)會(huì)就更多了。他每次話匣子一打開,少于一個(gè)上午或下午是關(guān)不上的,而且都是即席,桌面上連一張小紙片也沒有。大家最愛聽周總理和陳毅外長(zhǎng)作報(bào)告。那種場(chǎng)面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人人幾乎屏著呼吸在聽,簡(jiǎn)直是一種享受。陳老總那寬闊的視野、入木三分的見解、坦蕩的胸懷、獨(dú)特的幽默、不可復(fù)制的語言,都給我留下了一輩子揮之不去的印象。
“不憋不成才”
有一次,蒙古駐華大使館臨時(shí)代辦達(dá)賚為蒙中建交紀(jì)念日舉行招待會(huì),陳毅作為主賓應(yīng)邀出席。陳老總先與各國(guó)駐華使節(jié)交談,外交部四大語種——英、法、西、阿語的譯員和我跟在他后面,需要時(shí)上前當(dāng)當(dāng)翻譯。
事先,陳老總交代說,在招待會(huì)上,外交部準(zhǔn)備的講話稿他就不讀了,視情況只隨便講幾句。在蒙古臨時(shí)代辦致詞后,陳毅對(duì)在場(chǎng)的賓客們說,最近公開講話比較多,現(xiàn)在沒有多少新話可講了,只向蒙古朋友們講幾句祝賀的話。可是,陳老總的話匣子一打開,就關(guān)不住了。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在越南的戰(zhàn)爭(zhēng)正在升級(jí),他的話題是圍繞著越戰(zhàn)展開的。他越講越具體,什么越南叢林中瘴氣之大,猛蛇之毒,惡蚊之大,咬幾口就能咬死人……一連講了四五十分鐘,還絲毫沒有打住的意思。
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口譯工作的是外交部亞洲司一位蒙古族青年,他的蒙漢兩種語言都很好,一開始翻譯得挺順的。但隨著陳老總話題的具體化,可以看得出來,他越翻譯心里越發(fā)毛,頭上冷汗直冒,翻譯起來往往丟三落四,有時(shí)甚至站在那里發(fā)愣。
陳老總見狀提高嗓門說:“偌大的一個(gè)外交部,難道就沒有更好一些的蒙文翻譯!?”時(shí)任蘇歐司專員的戈更夫(蒙古族)連聲答道:“有!有!有!”并立即向擺著話筒的地方趕。陳老總沖他擺了擺手,搖著頭說:“不用有勞你的大駕了!還是讓他繼續(xù)給我翻。老話說:‘不憋不成才,年輕人嘛,就得讓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讓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輩子也成不了才!”
說到給陳老總當(dāng)翻譯,我不由得想起外交部翻譯處五大語種高翻們“集體卡殼”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記者會(huì)上,陳毅談到日本北方四島時(shí),把擇捉、國(guó)后、色丹、齒舞的名稱一一列了出來。當(dāng)時(shí),我與記者們坐在一起,戴著耳機(jī)聽俄語同聲傳譯。當(dāng)陳老總說完這四個(gè)島名后,俄語傳譯就一下子斷了。我立即把同聲傳譯器的選擇語道按鈕逐一快速撥到英、法、西、阿四條語道,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這四條語道一個(gè)個(gè)也啞了。原來,五大語種的高翻們?nèi)济闪耍磺暹@幾個(gè)島的外語究竟該怎么說,又不好根據(jù)漢語的發(fā)音瞎拼一通。
外交部翻譯處的領(lǐng)導(dǎo)對(duì)這次“事故”很重視,讓各語種把四個(gè)島的中外文名稱對(duì)照表打印出來,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隨身帶上,得便時(shí)就拿出來看看、背背。我還把一張北方四島的地圖粗線條地畫了下來,并附上四島的地理概況和歷史沿革,時(shí)不時(shí)地翻出來看看。盡管后來在口筆譯實(shí)踐中,在與外國(guó)人交談時(shí),再也沒有機(jī)會(huì)碰到這幾個(gè)島名,但其俄文名稱及概況,40多年過去了,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最后一次巨大貢獻(xiàn)
如上所述,陳毅在“文革”中被剝奪了工作的權(quán)力。但在1969年,這位元帥外長(zhǎng)為中國(guó)的外交事業(yè)、乃至為對(duì)內(nèi)方略的改變,作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貢獻(xiàn)。
這一年的3月,在中蘇邊境地區(qū)發(fā)生幾次大規(guī)模武裝沖突后,國(guó)際形勢(shì)變得更加錯(cuò)綜復(fù)雜。林彪提出要準(zhǔn)備“早打”、“大打”、“打核戰(zhàn)爭(zhēng)”。為慎重計(jì),毛澤東委托早已“靠邊站”的陳老總主持召開“四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國(guó)際形勢(shì)座談會(huì)”,讓他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從戰(zhàn)略角度來看待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所處的國(guó)際環(huán)境,并重新審視中國(guó)的對(duì)外政策。從3月1日至10月8日,在七個(gè)多月時(shí)間內(nèi),四位老帥開了24次會(huì)。
陳老總和另外三位老帥不為一片打聲所左右,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際形勢(shì),特別是中美蘇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客觀、實(shí)事求是的分析。他們認(rèn)為,在可以預(yù)見的未來,美國(guó)、蘇聯(lián)單獨(dú)或聯(lián)合發(fā)動(dòng)大規(guī)模侵華戰(zhàn)爭(zhēng)的可能性不大;在當(dāng)時(shí)的中美蘇“大三角”關(guān)系中,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又大于中蘇矛盾。據(jù)此,四位老帥提出利用這一有利的國(guó)際形勢(shì)開展外交工作的具體設(shè)想,寫出了《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的初步估計(jì)》和《對(duì)目前局勢(shì)的看法》。
在座談中,陳老總首先提出恢復(fù)中美大使級(jí)會(huì)談的建議,還主張“用非常規(guī)手段”打破中美關(guān)系的堅(jiān)冰。1971年春天,毛澤東真的采取了一種“非常規(guī)手段”——邀請(qǐng)美國(guó)乒乓球隊(duì)來華訪問。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開了中美之間緊閉的大門。當(dāng)時(shí)已重病纏身的陳老總,得知毛澤東接受他的建議后非常高興。
陳老總和另外三位老帥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所提出的觀點(diǎn)與設(shè)想,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消除了林彪等在“戰(zhàn)”“和”問題上的干擾,最終被毛澤東所采納。為毛澤東后來調(diào)整對(duì)內(nèi)大政方針以及在中美蘇“大三角”中縱橫捭闔,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