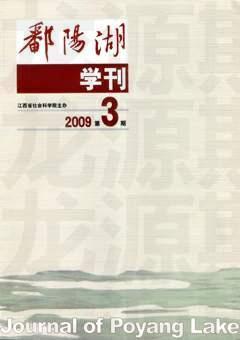《資本論》與生態學的交錯:馬克思思想的生態軌跡之三
黃瑞祺 黃之棟
[摘 要]本文從生態學的角度來剖析《資本論》中的生態思想。作者認為,《資本論》中的生態思維,可以從物質代謝、資本主義批判與代間正義三個面向切入。其中資本主義的型構批判貫穿三者,最為重要卻也最常為人所誤解。質言之,環境論者常認為《資本論》是一本專門討論勞動與資本的書籍,因此該書有著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并忽視了自然的重要性。本文作者以為,當代環境危機乃肇因于資本主義無止境積累的假設,致使吾人習于大量生產、大量消費以及伴隨而來的大量廢棄的生活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協動 (社會)層次的物質代謝進行分析與批判,是解決環境危機的唯一方法。基此,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對當代環境議題仍有相當的啟迪。
[關鍵詞]馬克思;《資本論》;生態學;物質代謝;代間正義
[中圖分類號]A811.2;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09)03-0075-11
[作者簡介]黃瑞祺(1954—),男,臺灣臺北市人,社會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歐美社會政治理論、生態社會學、全球化研究;(臺北 11529)黃之棟(1977—),男,臺灣人,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暨政治學院(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博士候選人,主要從事環境理論與左翼思想研究。
[收稿日期]2009-09-30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Ruey-Chyi Hwang Chih-Tung Hu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Marxs Das Kapital through an ecological lens. In doing so, three analytical angles are suggested in the article: metabolism,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mong them,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form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t is however the most misunderstood as well. Briefly, environmentalists often argue that Das Kapital downplays the importance of nature. As a result, this book is widely criticized as an anthropocentric text. The authors attempt to argue that mos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n find their roots in capitalists' over-production and over-consumption. If capitalism is the culprit, in order to solve environmental crisis, a critique of modern capitalism is necessary. In this light, Das Kapital provides fruitful new insights into curr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 words: Marx; Das Kapital; ecology; metabolism;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一、緒論
如眾所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處理的主題,在于揭露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型構中所潛藏的矛盾。經由他深刻且系統的批判,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特征有了基本的認識。直至今日,金融海嘯席卷世界,吾人仍能從中獲得一定的啟發(Foster and McChesney,2009)。然而,《資本論》一書的環境定位向來存在著重大爭議,并使環境主義者(environmentalists)對馬學抱持著相當的疑懼。造成此等欲迎還拒的原因眾多,其中一個重要的爭點集中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對勞動的評價之上。換言之,學界對勞動的意義究竟為何的問題,存在著見解的分歧。
簡言之,“勞動”一詞本身存在著“對象化活動”這層意義(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也就是說,人類會在有意識的狀況下對自然進行改造,并生產出自己賴以維生的生活資料。就這點來看,人與自然是割裂且對立的。不但如此,這種觀點下的自然之于人而言,是一種作為客體的存在。從而,人們可以依自身需要,對自然進行改造。環境主義者從這個角度出發,把討論勞動的《資本論》解讀成一本無視環境議題的“人類中心主義”文本(OConnor, 1997;Ses-sions,1995; Dickens,2002; Eckersley,1992)。畢竟,在這三卷的大部頭文本里,環境的議題淹沒在一連串對資本與勞動的討論里。乍看之下,馬克思對人的關注確實超越了他對自然的關懷。
《資本論》一書絕大多數的篇章集中在對資本與勞動等議題的討論,此點自不待言。問題是,資本與勞動的側面是否必然與環保思潮相違背?這個問題似乎就不是不證自明的了。對此,本文將從環境思潮的角度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新的詮釋。我們將依序從三個角度切入:物質代謝、資本主義批判、代間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經由系統地分析前述三項與環境思潮相關聯的概念,作者希望重構我們對《資本論》一書的新理解。

二、物質代謝的意義
循著歷史的經緯,我們一路從《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上溯到《德意志形態》等幾個重要的文本。在一連串的分析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在前述這些著作里,馬克思已經認識到了人的主體面向與客體面向,也闡釋了主客間關系態樣的重要性。不過,他對主客間的接合點的問題,在這些文本中還沒有進行細膩的分析。簡單來說,在前述著作里,馬克思精準地指出了人的兩面性,發現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且不能與自然分開的特質。換言之,人看似是一主體的存在,事實上人若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利用自身的勞動來和自然發生關系,就這點來看人的存在有其客體的面向。問題是,此處“勞動”一詞所指為何?在《資本論》之前并未有清楚的交代,彼時的著作只是提及人必定會進行此種活動而已。


這個問題一直要到《資本論》完成之后才獲得系統的解決。自此,馬克思徹底揭開了勞動的性質與功用,點破了勞動所代表的意義是:物質代謝(stoffwechesl;metabolism)的過程(Clausen,2007; Burkett and Foster,2006; Foster,2007; Martínez-Alier,2003; Grundmann,1991; Clark and York,2008)。他在書中論及勞動過程時,開宗明義地點出了勞動的意義: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媒介;vermitteln)、調整(regeln)和控制(kontrollieren)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物質代謝①;stoffwechsel)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馬克思,2004卷1:207-208;對照 ????,1977:234)
由上面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勞動指的其實是一種生物體與自然環境間的物質變換過程。這種轉變物質的活動,是以人的自然力為基礎來對自然進行改造且同時被自然所改變的過程。此類人與自然間物質代謝的活動,通常伴隨著素材(stoff)的變換(wechsel),這使得人的生存成為可能?(巖佐 茂,1994:131-132; Clark and York,2008)。

舉例來說,為了維系生命,每種生物體都會進行呼吸代謝,由大氣中吸入氧氣,并呼出二氧化碳等身體所不需要的物質。在這一呼一吸之間,我們也會與環境進行溫熱代謝,借由排汗(水分的蒸散)來進行體內的光熱平衡,將自身的能量與周遭的環境進行轉換。這種代謝的過程就是一種物質之間的轉換。更不用說食物的攝取與體內廢物的排泄,更屬新陳代謝的范疇,而成為一種典型的物質代謝表征。總之,馬克思所說的物質代謝與生態學中所說的“新陳代謝”有著高度的關聯,原因是他們基本上都是生物體與周遭環境進行物質轉換的過程。
……因此,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代謝)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馬克思,2004卷1:56)
在上述代謝的意義下,我們可以讀出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學意蘊。從生物體的角度來看,人類借由勞動從自然界中獲取具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物,經過人類內在自然的消耗后,生產物轉變為廢棄物并被生物體排出,之后回到自然環境里。這一來一往之間,物質進行了互換。當代生態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開展的。
不過,除了上述這個意義之外,馬克思比當代生態思潮又更進了一步,原因是他的思想中除了生態學的意涵之外,也囊括了生態社會學的意義。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人與自然間的物質代謝使得人的生存成為可能。此處我們所說的人,指的是個體層次上的人,但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關系不只存在于“個體-自然環境”間而已,真正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重大轉折的過程,其實出現在集體(社會)的層次(Clark and York,2008; Foster,2007)。也就是說,社會與自然間的物質移轉,改變了整個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的物質互換過程。
正如生物個體與自然之間會經由物質交換來攝取必需品并排出廢棄物一樣,整個社會也同樣會利用人與人之間的協動關系,創生出群體勞動所產生的自然獲取(社會的同化),在此同時也發生“被人類以衣服和食物形式消費后的土壤成分,再度回歸于土地之中”的社會的異化②(巖佐 茂,1994:133)。不管是古早時代抑或是現代生活,我們衣食住行等種種的必需品,大多不是由個人所產出,而是經由集合眾人之力所產生的勞動成果。基此,當我們在討論物質代謝或環境問題時,不應該只從個體的角度出發,而忽略了集體層次的討論。在這層意義上,如果我們要討論生態危機,就不能不探討協動層次的物質代謝問題。

上述個體同化、異化與社會之同化、異化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下交織出物質生產與消費間的同化、異化過程。這種大量向自然排放的異化思考,是今日環境困境形成的主因。對此,我們可以從個體自然的角度與人群協動兩方面觀察。
先從個體的層次來看,全球人口的急遽上升是造成19世紀以來環境污染的原因之一。人口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糧食問題(個體同化)與廢棄物問題(個體之異化),被認為是今日環境壓力的重要來源。這個問題在當前全球暖化的問題上亦常為人所討論。如上所言,只要有人存在就一定會有物質代謝的過程,因此生命的延續本身一定會與生存排放(survival emissions)產生牽連。基此,歐洲國家常常以此對人口大國施壓,希望他們減少人口的絕對值。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議題的接點(黃之棟、黃瑞祺,2007;Clark and York,2005; 2008)。
再從協動的角度來看。支撐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過程,基本上是沿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架構開展的。由于這整個生產的過程,牽涉到生產時與消費后的大量廢棄物,使整個資本主義的構造成為環境學者交相指責的對象(Foster and Clark,2003; Clark and York,2008; Foster,2007)。這類大量生產、大量廢棄的過程,原本只有地域性的影響。由于這個緣故,傳統的環境思想希望在區域的層次里討論污染與廢棄問題的解決。然而,當我們面對諸如全球暖化等議題時,前述的分析架構就顯得捉襟見肘,難以掌握全球層次的生態挑戰的全貌。原因是,工業先進國所排出的工業廢棄物總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影響了整個地球的物質代謝。從這個角度來看,協動(社會)層次的物質交換過程,取代了個體層次的分析架構,成為我們關注今日環境污染的主要視角(Burkett,2005; Clark and York,2008)。
總之,“生物體-自然”之間反復進行的物質交換,是每一種生物都無法逃避的自然過程。不過,人的勞動與動物的活動有幾點顯著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區別在于只有人對自然作用的基礎,是來自有意識的生產勞動,其他動植物的物質代謝過程基本上只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然過程而已。由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此處所指的“自然”一詞包含了三個層次:(1)外部的自然環境;(2)人類本身內在的自然;(3)通過勞動而形成的自然。三種不同平面上的自然觀,其中最為馬克思所重視的,不是客觀存在的自然,因為這種自然的物質代謝只是自然的過程而已;真正對人類會產生偌大影響的,是由人類主體活動所創造出的“勞動史中的自然”。這個層次上的自然觀,基本上是通過人的生產活動,對內、外在自然環境進行改造的主體與環境交錯而成的。通過這個層次的關懷,使得馬克思對自然的關懷擴張到了人所創設出的人工環境(built environment)層次。這使得他注目的對象,轉向那些對現有給定條件下對環境進行變革的勞動行為。換言之,從人類得以利用群體之力來加大自身活動范圍那一刻起,自然就已經不再是自然的了(Nature is no longer natural)。基此,生態學觀點下所著眼的“主體-環境”平面上的相互關聯研究,必須要延伸到主體間(協動)的層次才能完滿。
三、勞動的生態學詮釋
關于勞動進行的過程,馬克思曾經作過以下的分析: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
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只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一切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并非任何勞動對象都是原料。勞動對象只有在它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是原料。(馬克思,2004卷1:208-209)
許多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質疑,都集中在上面所引用的主體經由勞動過程把客體“原料化”的批評之上(Foster,1999)。由于這個緣故,馬克思遭到環境學者的嚴厲批判,并被認為他是完全以主體(人類)為起點的“啟蒙之子”(Barry,1999)。
綜觀馬克思所說的勞動概念,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他所說的自然并不是笛卡兒式切斷的、兩相分離的、臣屬型的自然,而是一種勞動史下的自然。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自然在馬克思眼中并不是(傳統)環境學家所想象的那樣,只把自然看成是一種可讓人予取予求的客體存在,他的自然觀是關系哲學式的。自然既是人的根源,也是人物質代謝成立的基礎,而不只是單純的客體而已。忽略了上述關系式的理解,我們很容易就會陷入理論的誤區。易言之,當我們歸結出人是自然界主人的“人的對象化活動”理論時,很容易就忽略了他思想中“自然的根源性”、“物質代謝”等面向,而誤把馬克思當成啟蒙繼承人的箭靶。
為了避免陷入理論解釋的誤區,我們在討論原典時必須調整我們閱讀的視角,從生態學的角度來對文本進行解釋。比如說,正如馬克思在定義物質變換時所說的那樣:“自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媒介、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傳統環境主義者的解釋,把重點放在第二段文字,強調人想要操控物質變換的過程,把自然給客體化。但生態學的詮釋,則認為此處馬克思的著重點在于人必須媒介、調整和控制物質變換過程。換言之,由物質變換的角度出發,人與自然關系的最佳狀態不是人單方面的征服與操控,而是借著漸漸理解自然規律的過程,進而對“自己”的物質代謝進行調控。
就事物的本質而言,自由之域系在真正的物質生產范圍之外,在此范圍(指生產過程)中所可能存在的自由,是指社會下的人群……在共同控制下,以理性的方式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而不是受制于新陳代謝,如同受盲目力量所支配。用最小的力氣,也可以符合人性的尊嚴與最適合的條件來完成新陳代謝作用。(Das Kapital III:873; Capital III:820)
所以,如果我們只注意到“控制”自然的面向,那么我們當然會認為馬克思只重視人對自然的操控。但他所真正關注的不只是對自然的控制而已,他的關懷也涵蓋了人對自身的控制以及人對人(人作為一種自然)的控制等面向。當然,當時的馬克思還沒有走到如法蘭克福學派這么遠的程度,因為此時的他對技術與對人類控制等等議題還沒有進行批判(威廉?萊斯,1993)。但他這里提到用理性來處理人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觀點,不但不是在強化啟蒙精神,反而是抑制了人類過度高漲的自我中心主義③。也就是說,馬克思對前述人與自然關系的期待,是希望人真的可以以理性來控制自身的行為,并調整人與自然間的新陳代謝,如此一來個人與社會的異化、同化問題(即關于生產/消費問題)才能徹底解決。屆時,人類將會達到資源使用減半、生產能力加倍的境界。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消耗最小的能源與資源,得到最大的物質滿足。此時的人與自然關系將會是人能獲取他所有生活所必需的資源,但只釋出最小的個人與社會異化物(廢棄物)。到了這個階段,人的廢棄物排放將完全達到控制。也就是說,此刻人們的生產行為會是在不損及地球這個萬物之母的前提下,與自然進行交流的過程。當新的生產方式實現之時,人類的自由也將無限擴張。由當前的全球暖化條約等等嘗試來看,我們已經漸漸在往自我控制的道路邁進了。
四、資本主義型構批判
順著本文的論述一路下來,我們說明了勞動的中介作用,也述及了人與自然間的物質代謝。事實上,這些論述隱含了一個前提要件,此前提要件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時期就已論及的“自然之先在性”、“自然之根源性”等問題。這樣的想法一路延伸至《資本論》中,都毫無任何變更:
……簡言之,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總還剩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人在生產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式。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本身)中還要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因此,勞動并不是他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2004卷1:56-57;對照 ????,1977:58)
由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人們如何強調自己的與眾不同,也不管人類多么自以為是地把自身的勞動看做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人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的產品,大自然是物料提供的先決條件,人們只能在這個自然所給定的條件上,對自然進行物質形態改變而已。所以,人類實踐活動的基礎還是在自然。這意味著,雖然我們反復說明馬克思的勞動史下的自然觀,是把未經人類勞動中介的自然看成是不存在的自然,但人類的勞動過程還是無法脫離自然的制約。因為我們不但需要自然作為材料,也需要自然力的幫助來進行勞動。從而,在整個(人類的)價值形成活動中,自然的素材被轉變為對人類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巖佐 茂,1994:135)。我們也是在這層意義上,發現了光是有財富之父(勞動),并不足以創生出新素材。必須要在勞動的同時,加進財富之母——土地(自然)才能使物質形態的轉變成為可能。
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們并未認清財富與自然間的重要聯系所在。因此,人們經常只重視經由協動過程所生產出的機械工具,并認為大量的物質生產完全只靠機器即可實現。這種看法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人與自然間物質循環的過程。所有產出的東西會耗損或被消耗,即便是消耗不完也是被丟棄。不管是消耗還是丟棄,物質資源與廢棄物最終都將再回到自然(本身)的循環里。自然借由其本身“力的作用”,對機械等廢棄物產生物質的破壞作用,讓鐵銹蝕,讓木材腐朽,讓一切原本屬于自然的東西再次解體為自然(馬克思,2004卷1:214)。
所以,當代環境危機的癥結不在于人與自然間是否存在著物質循環的關系,真正的問題在于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架構,讓這種原本緩慢進行的循環關系被單方面地加速了。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拋棄”的生活樣式,一下子傾倒了太多自然負荷不了的垃圾(如二氧化碳),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了原有的循環規律。由于人類本身也是這個循環中的一分子,因此當我們改變循環規律的時候,我們不僅是破壞了自然(本身)的循環而已,人與自然間的循環也將遭受波及。從而,希冀光是自然遭殃而不禍及人類的想法本身只是一種妄想而已。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攪亂)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通過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同時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并在一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馬克思,2004卷1:579-580;????,1977:656)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也作為一種社會形構,帶給人們的是兩路包抄式的破壞:一方面,大量生產、消費及拋棄的論理侵蝕了人們的生活基礎;另一方面,作為規制手段的資本主義,又強迫人們過度勞動。結果,(外在)自然消受不了工業廢棄物因而殘破不堪,工人(內在自然)也因承受不起超時勞動而身心受創④。到頭來,人們所要面對的不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進步,而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破壞。因為資本主義下的任何進步都只是一種掠奪式的進步,大量生產等的論理引導出的不僅是生產力而已,巨大生產力勢必帶來大量廢棄物,這就是說生產力的反面——即破壞力——也將亦步亦趨地成為人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我們利用龐大生產力提高物質生產之時,勞動過程產生的廢棄物物質交換,必將攪亂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當財富之母(自然)進了墳墓,我們就不可能再妄想還能以一己之力擁有富裕的未來,因為物質變換的基礎消逝了,下一個被否定的一定就是人類了。當自然中充滿了放射線與毒物,人們想要完全排除其影響根本就是毫無可能,最后的結果是這些自然沒辦法清理掉的垃圾將禍延子孫。
五、代間正義
《資本論》中另一個與環境思潮有關的概念,是在討論這個世代與下一個世代間的正義問題。具體來說,如果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那么我們這個世代大量消費資源的后果將會造成下個世代的資源耗損與環境耗竭。基此,(世)代間正義的問題是當代環境倫理學中的重要議題。
回首人類的歷史,自有人類以來不過幾萬年的光景,而人們開始使用石化原料的歷史也不過百余年。但就在最近50年內,大量的石化燃料消費幾乎耗盡了需要費時千百年時間才能形成的大多數能源。換句話說,我們這個世代在短短的150年內幾乎耗費了所有后代子孫賴以維生的寶貴資源。這種對未來子孫生活資源的巧取豪奪,剝奪了后世子孫的生存權,因此學者常以變相殺人和對未來世代的隱形犯罪⑤來比擬當中的不正義(加藤尙武,1991)。環境破壞與資源枯竭的現象之所以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嚴重,是因為資本主義無限積累的假設驅使人們毫無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換言之,為了維持無止境的資本積累或維持經濟高度成長,工業先進國常常以大量開發及大量消費天然資源為手段,企圖延緩資本主義危機的出現。當增長與資本積累成為目的的時候,環境危機就成為增長中的必要之惡了(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
現代環境倫理學從這里引申出一個新的問題,即當今世代是否必須對未來世代的生存負責?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掌握了后世子子孫孫的生存命脈。然而。這個問題其實不容易解決。此問題的難解之處在于,即便所有人⑥都認為世代間的正義確有必要,但因為造成資源枯竭的現存世代(加害者)與遭受苦難的未來被害世代間,存在著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的時間差。因此不論是兇手還是被害人,都難以確認因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世代間倫理的問題對當今民主論理會產生相當的沖擊。因為即使大家都肯認民主主義的功用,但以共時構造為基礎的民主機制,無力解決歷時構造的代間爭議(加藤尙武,1991:4-5)。
作為一種歷時性的歷史論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構想是站在當今資本主義體制之揚棄與催生未來新社會形構的基礎上建立的(Burkett,2003;2005)。由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的論理本身就是“未來志向”的。現今環境衰敗的問題,是一個跨越兩代之間的問題,因而放眼未來是一個必要的起點。當眼界放寬到未來,這意味著今日的種種必須被超越,明日種種必須預先被思索。
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超越了機械式的自然控制觀,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變革態樣,作了歷時性的探討。對他而言,隨著私有土地與私有財產的消失以及自由生產者聯合的出現,全球永續的自然觀也將隨之浮現。這種能使資源永續開發的構想,其實跟上述人規制自己與自然間的新陳代謝的看法有關。換言之,人們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以往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習慣,往耗能少一點、利用久一點、功率大一點的自我規制來建立未來新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新的生產方式必須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揚棄之上的。在這個前提之下,資本論理的框架要被打破,大量生產與消費的生產方式也必須被超越才行。此時,人類將從自身(生物)的需要中解放,而開始思索未來世代的關系(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
從社會較高層次的經濟形式立足點出發,整個地球被單獨的個人占有這樣的私有財產關系,與一個人被另一人占有的人與人之間的私有財產關系一樣荒唐。即使是整個社會、國家乃至于那些同時存在的社會整體,也都不是這個地球的擁有者。他們只是占有者—及用益權人罷了。和家里的好父親(patres familias;good fathers of families)一樣,必須把一個改進過的地球傳承給后繼的世代⑦。(Marx,1981:911)⑧
所以,站在更高階段的社會經濟型構鳥瞰資本主義,馬克思看見的是建構資本主義理論的重要假設,也就是私有財產制的荒謬。自然不是可以任人處分、拋棄的所有物,因為不論是哪一個世代的人,他們都只是這個地球的“看護者”,而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所有人”。從而,沒有哪一個世代有權利對這個唯一的地球進行沒有明天的巧取豪奪,人類必須從細心看管、仔細維護的角色出發,把這個地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其實,歷時性的探討也可以放在前述物質代謝的概念下來進行。即便是在自然的生態系統循環過程里,時間差也依然存在。就像人的排泄物不會(也不能)直接成為肥料一樣⑨,我們必須等待時間的累積與自然力的介入,才能使這些不為人體所需的廢料再度成為養料。所以,這種自始即存在的時間差,使得人們必須自發地介入廢棄物回收的歷程,使原本的自然循環不至因為無法消化龐大的生產與消費排泄物而停擺。
……消費排泄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泄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么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用來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貴,自然成為廢物利用的刺激。(馬克思,2004卷3:115)
問題是,身處資本主義社會的蕓蕓眾生,很少有機會去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惡果。在現行資本主義體制底下,眼前的獲利是資本家唯一的關懷。正如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金融危機一般,當短期利益與長期獲利有所沖突之時,資本家一定會選擇追逐眼前的套利。原因是,任何長遠的眼光還是都得接受市場的競爭,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合游戲不容許何人有一絲喘息的機會,無止境的競爭機制逼得資本家失去耐心與時間去關心未來可能爆發的問題。生存競爭戰勝一切。當吾人損及(攪亂)了土地的豐饒性之時,自然所帶來的苦果不會立即顯現,但除了人本身構造上的見識局限之外,真正主要的原因還是出在資本主義本來就是建立在沒有明天的短期論理之上的。因此,浪費成了資本主義的同義詞,許許多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資源,除了有利可圖的一小部分之外,大都被資本家當成垃圾丟棄。
由于資本家們所關心的本來就是現下一時的金錢進帳而已,人的身體與自然環境的受創與否,本來就不被資本家們列入考慮之列,除非保護環境和回收再利用可以得到現實的利益,或是原料昂貴到要讓資本家不得不回收資源,不然環境的損益與荷包的扁飽就完全無關了,未來子孫的福祉也與現下能夠賺錢與否無涉,這些議題當然也就為資本家所忽視了(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
盡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問題并未多所著墨,但很顯然是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必將被自由生產者聯合超越使然:
歷史的教訓是: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兼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馬克思,2004卷3:137)
對馬克思而言,在未來的新生產方式里,由于人們已超越了自身純生理的需求,也擺脫了自然力機械性的支配,而進步到能對自己的行為加以控制的階段。是故,未來的自由生產者聯合不會采取短線操作,每一項社會生產都將是為了使人的無限潛能釋放而做。自由王國中的每一份子都將與自然結合在一起(Foster,1995:112-114)。此時的自由王國已經可以用最理性的方式,來處理人與自然間的關系,也就是可以做到合理規制生產與消費中的剩余廢棄物。屆時,所有人都將小心翼翼地呵護這唯一的地球,而不致使整個生態系的新陳代謝受到擾亂。當然,此處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合理規制”等能否實現,容或有疑義。但從資本主義的演變來看,當前的環境危機似乎逼使我們向馬克思的目標邁進了一步。
六、結論
本文探討了馬克思最為人所熟知的大作《資本論》中的生態思想。馬克思的思想之路相當博雜,但是沿著他的思想軌跡一路尋來,我們可以從中理出部分頭緒。沿著歷史的經緯,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馬克思由討論自然、人,到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他所希冀解決的問題一步步逼近核心。在馬克思思想集大成的《資本論》里,我們看到經過《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峰回路轉,人利用勞動來和環境進行交換的過程,才是馬克思真正的注目之處。
對于勞動的意義,我們必須由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勞動”一詞除了有對象化與客體化的面向之外,亦有其物質代謝的面向,此種看法與當代生態學的精神吻合。其次,作者強調由于當今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協動(社會)層次的物質代謝失衡,因此我們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構進行批判,才能徹底解決環境問題。當然,在眾多學說之中,馬克思理論是最能有效解析資本主義生理及病理的分析工具。基此,要談環境危機的解決就不能不談馬克思。最后,馬克思的思想中也含有代間正義。必須說明的是,他的代間正義觀必須放在前述資本主義型構批判中來觀察。具體來說,由于資本主義強調競爭,因此所有的資本家與勞動者無時無刻不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改變現有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資本家就不可能顧及下個世代的存續問題。從而,我們必須在對資本的批判中,尋求代間正義的實現。總的來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是在今天,馬克思思想仍能給予我們生態學的啟示。
[參考文獻]
陳俊宏.1997.世代正義理論的困境:關于“非同一性”問題的吊詭[J].東吳政治學報,(7): 35-65.
黃瑞祺,黃之棟.2005a.綠色馬克思主義[M].臺北:松慧出版社.
黃瑞祺,黃之棟.2005b.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M].臺北:松慧出版社.
黃之棟,黃瑞祺.2007.身陷雷區的新人權理論:環境正義理論的問題點[J].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42: 38-51.
黃之棟,黃瑞祺.2009.環境正義的經濟向度:環境正義與經濟分析必不相容?[J].國家與社會學報,6 : 51-102.
(德)馬克思.2004.資本論(三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加)威廉?萊斯.1993.自然的控制[M].岳長齡、李建 華,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美)Ahmed M. Hussen.2002.環境經濟學原理[M].陳凱俐,譯.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藤尙武.1991.環境倫理學のすすめ.東京:丸善.
內田義彥.1992.資本論の世界.東京:巖波新書.
巖佐 茂.1994.環境の思想.東京:創風社.
????.1977.???????????全集(第23卷).
東京:大月書店.
Barry, J.,1999. Environment and social theory. Routledge, London.
Beckerman,W.,Pasek,J.,2001. Justice, poste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Burkett, P.,2003. Ecology and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7(2): 41-72.
Burkett, P.,2005. Marx's Vision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57(5): 34-62.
Burkett, P.,Foster,J. B.,2006. Metabolism, energy, and
entropy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thePodolinsky myth.Theory and Society 35(1): 109-156.
Clark, B.,York,R.,2005.Carbon metabolism: Global
capitalism, climate change,and the biospheric rift.Theory
and Society 34(4): 391-428.
Clark, B.,York,R.,2008. Rifts and Shifts: Getting to the
RootofEnvironmental Crises .Available at http ://
www.monthlyreview.org/081124 clark-york.php .
Clausen, R.,2007. Healing the Rift: Metabolic Restoration in Cuban Agriculture. Monthly Review 59(1): 40-52.
Dickens, P.,2002. A Green Marxism? Labor Processes,
Alien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Dunlap,R.,
Buttel,F., Dickens,P.,Gijswijt,A.,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 Classical Foundations,Contemporary Insights. Rowman & Littlefield,Oxford,pp.
51-72.
Eckersley, R.,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UCL Press,London.
Foster,J. B.,1995.Marx and the Environment.Monthly
Review(3):108-123.
Foster, J. B.,1999.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366-405.
Foster, J. B.,2007. Marx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ift.Available at http://www.monthlyreview.org/
mrzine/foster281107.html.
Foster, J. B.,Clark,B.,2003.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curse of capit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186-201.
Foster, J. B.,McChesney,R. W.,2009.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Accumulation.Available at
http://www.monthlyreview.org/091001foster-
mcchesney.php.
Grundmann, R.,1991.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87: 103-120.
Martínez-Alier, J.,2003. Marxism, social metabolism, and
ecologicallyunequalexchange .Availableathttp ://
www.recercat.net/bitstream/2072/1194/1/UHE21-
2004.pdf .
Marx , K .,1981.Capital ,Vol .3.InternationalPublishers,
New York .
O'Connor, J. R.,1997.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The Guilford Press,New York.
Sessions, G.,1995.Postmodernism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Demise of the Ecology Movement? The
Trumpeter 12(3): 150-154.
WCED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8.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責任編輯:胡穎峰
注:
①stoffwechsel一詞,中文譯本譯為“物質變換”,而日文譯本譯為“物質代謝”。在本文中不加以嚴格區分。
②在這里我們借用巖佐氏的同化、異化論理,雖然他區分馬克思的學說為生產、消費兩層次的說法,故有所據(巖佐 茂,1994:133;巖佐氏本人并未提及出處,其實馬克思關于此點論述是在《資本論》卷3第116頁以下),但我們還是認為這是一種便宜的解釋方法,且未擊中現代資本主義的要害。本文還是認為應該回到“主體-自然”也就是在社會與個人兩種不同的分析單位下來與現代環境論理作一結合,詳下述。
③用今天生態學者的話語來說,這種自我中心的觀點就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
④有很多人認為過度勞動的情形在今天已經解決,但從不時可聽見先進國家的日本出現“過勞死”的報導,就可以知道資本主義對人的身體(自然)的戕害并未終止(甚至沒有被轉化)。又,關于人的身體與自然環境遭受資本主義荼毒的情況,馬克思論述不多,這可能是因為他的摯友恩格斯已經作了他難以超越的實證調查所致。
⑤對于代間正義的問題,此處我們以加藤氏的犯罪比喻來凸顯其道德上的可責性。比較持平且通行的定義,是WCED在說明永續發展的概念時所下的關于代間正義的定義,其中他們把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WCED,1988:43)
⑥并不是所有人都贊成代間正義的觀點。例如,新自由主義者即反對此見解 (Beckerman and Pasek, 2001)。他們基本上認為,由于我們不知道后代子孫的選好,因此談論正不正義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此說的問題在于,我們這里提及的正義問題是基本的存續與滅亡的問題,而不只是選好之間的選擇而已。換言之,當我們說后代子孫有選擇滅亡的權利時,我們其實剝奪了他們的選擇權(黃之棟、黃瑞祺,2009;陳俊宏,1997)。
⑦請對照上述WCED定義與此處馬克思原典關于代間正義的說明。
⑧此處作者采用了英文版的譯文,從而譯文與中文版稍有出入。中文版的部分讀者可參考《資本論》第3卷第46章。此章節與環境問題有關,殊值參考。
⑨即使是像生物排泄物這么“自然”的東西,到再利用時還是有時間差。
⑩今日的泰晤士河明顯與馬克思所描述的情景不同,可見資本主義有其自我轉化的面向,此點值得吾人繼續研究。又,倫敦鐵橋中間彈頭型的建筑,是今日倫敦金融業的象征之一,也是此次金融風暴的發源地。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景氣循環似乎是資本主義的鐵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