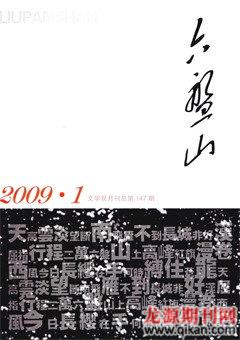王懷凌其人與《棉花》
紅 旗
真正認識王懷凌并熟悉他是讀了他的詩作《棉花》之后。
多年讀書,最為感悟的是:一個作者要寫詩,必須自己是詩,心中有詩,怎樣的品性決定怎樣的詩作,也就是“詩如其人”。對于王懷凌,以前似曾認識,也恍若相互寒暄過,但多半客套于泛常的應對,沒有深刻印象。一次翻閱《綠風》詩刊,看到一組《西部以西》詩歌,看到發表在其中的《棉花》,不由細細品讀,才算真正注意了詩的作者——王懷凌。
過去在老家農村接觸過棉花這種作物。摘棉花、曬棉花、揀棉籽,甚至幫著大叔大哥捆扎好棉花錠,交給公社收購站。棉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而我對棉花獨有一番情愫:它有白皙的顏色,卻不顯嬌柔的艷姿;它有飛揚的愿望,而從不輕浮;它有溫暖的懷抱,但毫不貪婪吝嗇;它緊緊貼著我們的身體,從不故意讓我們感覺到它的存在。在成熟的季節里,棉花在枝頭悄悄分娩,人們小心翼翼為其接生,在豐收的棉田里到處洋溢著采棉人的歌聲和棉花骨朵兒奉獻的爛漫。這正如詩中“在棉花盛開之前,所有的花朵都應該熄滅\九月,廣袤的新疆大地在棉花溫暖的懷抱中沉醉”。王懷凌用睿智的目光和善于思辯的抒寫,使我對他的詩作以及本人肅然起敬。這樣的筆調需要怎么樣的心情和見識才能培育?這樣的感知和自然而然的表達又得益于怎樣的基礎呢?我相信,這一切都出于一個人的秉性和對自然界的熱愛,對勞作的理解和對文字的嫻熟。于是,我以文取人,想象他是一個優雅的儒者,一定擁有廣博的學識、淡定的風范、深刻的啟悟和潛心的寫作。
當一次有人向我介紹王懷凌時,我十分驚訝,他是王懷凌?這樣年輕,年輕得近乎脫俗,一身迷彩服,似乎和氣中暗藏了許多傲骨。他自然地伸出手與我相握,并告訴旁邊人:“我們是老熟人了,他是老牛。”此時廬山蒼竣,在我眼中反而不近情理。
從此以后我便和王懷凌真正成了老熟人。我們(包括單永珍、楊建虎)經常聚會談詩歌。他們是老詩人,各自有不凡的成就,我年齡雖比他們大但起步最晚,于是他們三人對我都有一定影響,關心我、激勵我(常常叫我青年詩人)。我有時把自己的作品和他們的作品放在一起自我挑剔(尤其是王懷凌的作品,光《棉花》我就比較了無數次),得出的結論是:我年輕,他們成熟,王懷凌是個老家伙!
現在我可以直接說王懷凌這個老家伙了。他固原師范畢業,在鄉鎮當過教師,到文教系統當過于事,在政府機關辦公室干過,又去一個鄉鎮當領導(一個九品開外的芝麻糊糊官)。會開車(有時下鄉工作自己駕車)、會喝酒(劃拳老手、邊擲骰子邊猜對方眼神)、會調侃(這家伙笑容里有自信)、會寫書法(我好不容易討了一幅他自認為很糟的字,這家伙更好的字或許是想要點潤筆)、會吼秦腔(有一位姓陳的秦腔專家特別喜歡他的唱腔……)、很自負(自稱每年抽時間寫一些國家重點刊物能發的東西就行了,果真如此)、很忙活(公干忙得不可開交,還抽空和愛好文學的兄弟們打拼)、高興時唱一出周杰倫后現代的《菊花臺》……反正這家伙很絕!在詩作中他潛移默化地敘述著一種對勞動生活、對普通農民工的熱愛,“一望無際的棉田和天南海北的拾花人\在這個最忙碌的季節里秘密邂逅\從西海固出發的拾花人像蜜蜂一樣\涌出烏魯木齊火車站蜂箱\轉眼就被一片白色的花海淹沒\當他們在十月的花事中蘇醒過來\那個和我一樣累彎了腰的男人……”這種情感只有日積月累的沉淀,才能付諸筆墨生動地表現出來,這里我仿佛讀到了《詩經·采薇》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的感覺。他筆下的西海固不是荒涼無助的,是充滿鄉土氣息,具有昂揚拼搏活力、具有一種風起云涌的契機和一種溫和的堅持。記得在一次談笑中他說:“泰山只是雄偉,并不很高”,果然他在詩作《我站在泰山之顛》里寫到“我高出泰山一米七八”。這是一種蕩氣回腸的現代生活禪,這種意象在他平常生活、在他的作品里處處獨立存在。又如《棉花》中“……那個和我一樣累彎了腰的男人,由衷地感嘆著\新疆的大地之大,棉花。之白,少女之美”。
每次讀他的詩,我總會感嘆:這樣寬闊胸懷的詩人,這樣有才華的詩人,如果他能專心致力于筆耕多好啊。
當然,我知道的王懷凌并不是唯美的,也許只是一些單枝片葉,他的主干還需以后交往中多多觀摩和體會。我想“窺一斑便知全豹”、“覷一葉而知秋深”一定有它的道理。最后,我以他的詩順便做結尾:
我告訴你西海固:蒲公英的淚珠被風暴挾持
苜蓿夢見紫花的海洋工蜂暢想甜蜜的愛情
我送你一朵云你一定會熱淚盈眶,但我只送你一聲嘆息
西海固只是中國西部的一塊補丁在版圖上的位置
叫貧困地區或干旱地帶我在西海固的大地上
穿行為一滴水的復活同災難賽跑……
[責任編輯:單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