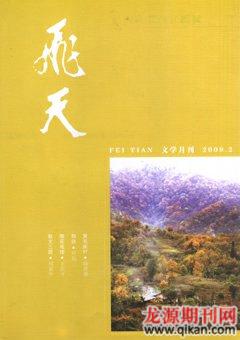黃毛柴籽
閻世德
黃毛柴籽,又名沙蒿,沙生植物,耐旱,生命力極強。其籽可藥用,更多則用于食品。
——題記
一
當臉色蒼白的太陽圓成孤獨飄浮在連連綿綿的大漠上時,二嘴子村的上空已經升起一縷縷的炊煙了,慢慢飄蕩的炊煙最后和夜幕扭結在一起,彌漫出村莊特有的靜謐。
大元推開飯碗的同時,摔出硬邦邦的一句話:“就這么定了,活人總不能讓尿憋死!”
“定了什么?”剛掀開門簾的二元抓住了話的尾巴,沒頭沒腦地問。
大元往炕里挪挪身子,給兄弟挪出一個位置。媳婦秀林已經盛好一碗飯湯給二元。她知道二元的習慣,不論吃多飽,不論到誰家,趕上吃飯,二元都要一碗飯湯喝喝,不然,他會很不高興。記得剛過門不久,她還不知道二元的習慣,把下了長面的面湯倒進豬食里,當時二元就拉下了臉。
二元總能把寡淡的面湯喝得香甜、饞人。在他吸溜面湯的時候,大元說了自己的計劃。二元被最后一口面湯嗆了,他用手背擦擦嘴:“好呀大哥,聽說黃毛柴籽每斤都和我差不多了。”
秀林笑了:“不會是每斤二元吧?那不成了金子?” 同時她小心地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好倒是好,就是進沙漠,危險得很……”
大元嘆口氣:“是要好好準備的,但值得一試,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做好了,不光能過一個好年,還能買些春種的化肥。”
二元似乎已經感到了實實在在的鈔票,雙眼亮亮的閃著喜悅:“大哥,說干就干,咱啥時走?”
簡單地商量過后,二元興沖沖走了。而歸于黑暗的屋里新的內容仍在繼續(xù)。秀林偎在大元懷里,溫情中傳遞自己的擔憂:“進沙漠是很危險的呀,窮就窮,咱不冒這個險……”
是很危險的。大元知道這種潛在的危險。村里的人都在山里生活慣了,山,就如自己的手指一樣熟悉,是不會有任何的危險存在,而沙漠,對他們這些移民來說還很陌生,許是人的本性使然,靠山吃山,靠沙漠,就要吃沙漠了。但媳婦的提醒,讓大元心里忽然涌上一種感動,結婚一年多了,這種感動還從未有過。他攬過秀林的身子,手臂緊了緊,他明顯感到秀林的身子哆嗦了一下,這種哆嗦讓他心里一陣隱痛。“是個好女人呢……”大元的感嘆讓自己的眼睛濕濕的,無法掩抑的委屈讓他情不自禁地喃喃:“這個倒霉的日子呀,怨不得人,由不得自個,總是讓你看不到的東西趕著跑,慢些都不行……”
顯然秀林對這些話有著自己的理解,大元感覺有熱熱的東西在胸脯上流淌,而秀林的話同樣顯得不著邊際:“由得人的日子不多,我不求過多好的日子,只求你對我好。我知道你心里的不如意,我并不比她……”
大元張開毛茸茸的大嘴,咽下了秀林要說的話。他閉上眼睛,拼命吮吸嘴中的柔軟,覺到一股熱流直入心底,這股熱流迅速向全身擴散,擴散為一團火焰,大元感覺自己燃燒起來了,同時燃燒的還有他一遍遍重復的話:“只要活著,總能找到活著的辦法……”
大元二元,加上村里的朱三和張五,四個勇敢的男人決定進入沙漠。大元讓他們找蒙古人的駱駝客,自己則準備更多的草繩用來捆綁東西。
大元盤腿而坐的右膝下,已經壓了一盤濕漉漉的草繩,左腳下的繩頭卻沒有盡頭般向前延伸。這是山里遍地都有的芨芨草,堅韌、粗糲。做成繩子的第一道工序就是認真剝了葉片一樣的皮,直到晾曬出芨芨草光滑明亮的身體,隨后拿一把木制的榔頭,細細地將芨芨草砸扁砸毛,要成繩的時候,口含了清水,一口口噴灑在上面。隨著“噗噗”的聲響,細碎的水霧在陽光下閃著七彩的光,如露珠般把芨芨草浸潤得濕漉漉的。
濕漉漉的芨芨草總能讓大元興奮。搓繩的時候,臉上有一種近乎喜悅的表情。雖然已經被砸扁砸毛,又被浸了水,但骨子里柔韌的芨芨草仍和大元一雙手做著最后的抵抗,但大元的雙手似乎比芨芨草更堅韌、粗糲。大元感覺到這種抵抗,抿著嘴,用勁做著最后的征服。隨著雙手的動作,柔韌的芨芨草變成了彎彎曲曲的草繩,最終服帖地盤踞在他的右腿之下。就在大元和芨芨草較勁的時候,蓮花來了。
“大元……”
一個澀澀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似乎遙遠但很熟悉的呼喚令大元怦然心跳,猛然抬頭的暈眩讓他的身子晃了起來,眼前的人影在晃動中終于穩(wěn)定了下來,大元的臉倏然漲得通紅:“蓮花……”
蓮花轉過身去,用腳尖在地上畫著雜亂的心跡:“我剛遇到你媳婦了,她給你壓面條,說你要進沙漠……”
隨著腳尖的扭動,蓮花的身子也在顫動,大元扭過頭去:“不去不行了,閑著也是閑著,這個日子逼死人呢……”
“就是。”蓮花抬起了頭,同樣紅著臉喃喃,“不要怨我……大元,我想和你們一起進沙漠。”
“你?”大元聲音大得令自己也吃驚。
蓮花反倒鎮(zhèn)定了,她木然講述著一個好像和自己沒有關系的故事,“他現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混著哩,婆婆病了,連個吃藥的錢都沒有,快要過年了,孩子沒個新衣,明年的水費、化肥……”亮亮的淚花在蓮花眼中閃爍,但她很快咽了下去,“我知道可能不方便,可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掙錢了。”
大元的心被刀子狠狠剜了一下,他的嘴唇哆嗦了起來,但他很快克制了自己:“可是我怎么對她說?”
“說什么呀?”秀林的回答讓大元和蓮花一驚,不知什么時候出現的秀林臉上有些不自然,但她仍鼓著勁替大元做出了決定:“誰家沒個難心事呀?蓮花你就快收拾收拾吧,沙窩里的東西又不是大元的,誰都可以去呀。”
蓮花看看大元,又看看秀林,嘴唇哆嗦了幾下,卻沒有說出一句話,她折轉身,腳步有些慌亂地走了。
黃土夯實的小院很干凈,干凈得有些空白和寧靜。回過神來的大元看著秀林,想要找一些東西出來,秀林不自然地扭著身子,和大元直勾勾的目光做著較量。最后大元的目光軟軟地收了回來,他指著秀林手中還沒有變成面條的面粉說:“你怎么……”
秀林笑了,笑得有點慌亂:“我知道蓮花會找你的,我不知道這么做對不對,可我知道她缺錢,她實在沒有辦法了,唉……我這就去壓面條。”
大元再也沒有搓繩的興頭。這時,他才發(fā)現手掌已經浸出血水。對著陽光,大元拔出鉆進手掌肚的一截芨芨草,木然看著更多的血水在手掌慢慢匯聚,最后凝成晶亮的一顆血珠落下。在血珠悄沒聲息地滲入地下的同時,大元的心顫了一下。
二
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大元他們已經走了大半個夜晚了。
晨陽下的大漠鮮潤而遼闊,豐滿的沙丘渾圓且富有肉感,到處閃爍著亮晶晶的霜花。翻過一道沙梁,他們走進相對平坦的地方。這是一條彎曲的白色土地,很像大漠中流淌的一條河流,又像大漠不忍舍棄的記憶,靜靜濡染在空曠中。河灘中全是一人多高、胳膊粗細的小樹木,蒼勁的枝干,鐵一般澆鑄在自己的空間。駱駝客說,這些柴禾叫霸王柴,你們可以用這些柴禾做飯。朱三一腳踹過去,一棵柴禾脆生生地倒下了。
二元喊:“原來都是枯死的?”
駱駝客笑了:“它們都是活的,一到春天,就會抽枝發(fā)芽。”
張五貪婪的目光打量著漫無邊際的柴禾感嘆:“老子要是有條路就好了,把狗日的們砍了當燒柴多好!省得掏錢買煤了。”
大元的眉頭卻緊緊擰在一起。他感覺到身后的蓮花有點力不從心了,而且蓮花往沙窩子里跑的次數越來越多,莫名的擔憂讓他心里煩躁不安。
蓮花臉色蒼白,一種快要流干了的焦渴讓她精疲力盡。早上吃了一點剩飯,鬧壞了她的肚子,剛一上路,就無法控制地一次又一次拉。毫無準備的尷尬讓她欲哭無淚,不時的疼痛,迫使她哀怨、害羞地看一眼大元,又折頭跑向沙窩子。
朱三惱了:“這個婆娘就是多事,磨磨蹭蹭的什么時候才能到?”
二元看看大元,說:“大哥,要不我們先走,你在后面等等蓮花?”
大元有些感激地看看二元,默默地站在霸王柴邊卷了旱煙,等著蓮花。
大漠的天空很藍,藍得沒有一點雜質,藍得沒有一點內容,藍得讓大元的心里空蕩蕩的沒有一點著落。怪了,山里的天也藍,但似乎沒有這么蒼白的藍呀……哦,山里山里……大元的目光投向山里的方向,山里已經虛無成一抹隱隱綽綽的遙遠。
但再遙遠的大山在大元的眼里都是清清楚楚的痛。透過裊裊升起的煙氣,揮之不去的記憶又異樣清晰地出現在眼前:起伏的大漠在大元眼中抖動,最后抖動成山里滿眼的綠地,在向陽的一面山坡上,白豌豆花開得正好,而緊鄰的青豌豆花也同樣開得血紅,一陣風吹過,白的波浪和紅的海洋像綢緞一樣起起伏伏,隨著這景致的還有大元的笛子。悅耳的笛聲好像和豆花吻合了一樣愜意,在山谷里飄飄蕩蕩。遙遠的聲音從山頂上爬了上來:“大元哥——”蓮花攥著拳頭跑向了豆地。淹沒在花海中的大元對著蓮花拼命招手,蓮花滿臉驚喜地撲到大元跟前,伸開攥著的拳頭:“大元哥,我奶奶給我的白沙糖。”可是白沙糖不見了,蓮花委屈地說,“我明明放在手心里的……”大元突然抓起蓮花的手舔了起來,一連聲說:“在這里呢,在這里呢。”手心癢癢的讓蓮花咯咯大笑,清脆的笑聲融進起伏的豆花,傳了很遠很遠……
“大元哥——”
大元被燃盡的煙卷燙痛了手,而一聲真真切切的呼喚從沙窩子里傳了過來,聲音充滿了羞澀、無奈和急切。大元似乎想也沒想,就匆匆地撲進沙窩子。
蓮花倚在沙丘上抽搐著身子哭泣。她不敢抬頭看大元,更不想讓大元看到自己的眼淚,她只是哭出幾個字來:“肚子痛,痛死了……”
蓮花恨不得讓沙子吞噬了自己。然而,來勢迅猛的痢疾,已經讓她的臉色蒼白,雙腿也如面條一樣綿軟無力。
木然之后,大元很快醒過神來。他長長呼出一口氣,從衣袋里摸出一個塑料袋袋,取出幾粒氟哌酸。想想還缺少什么,又緊著追上前面的駱駝。他知道,駱駝客有一個保溫的水杯,那里一定有熱水。
一個來回的折騰,大元已經氣喘。蓮花迫不及待接過水杯,有些貪婪地猛喝幾口,吞下大元給她的膠囊。
滾燙的開水以及大元粗重的喘息,給了蓮花容走出沙窩子的力氣,看著大元黝黑的臉龐和關注的眼睛,她想說些什么,但最終只是張了張嘴。大元的眼睛幽深而平靜,像一潭不起波瀾的水,卻透著溫馨和蓮花熟悉的東西。只一看,蓮花就已經沉入潭底,有些驚慌而愜意地暢游了一會,蓮花似乎在打撈起自己的同時,也打撈起很多的東西。但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淚水,在無法抑制的抽泣聲中流淌。淚水,總是女人心底的秘密或者是掩藏心事的最好遮蔽物。
大元的腳步慢了,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唇齒之間似乎還留著蓮花手上的甜,而蓮花嚶嚶的哭泣卻使他心里焦灼而煩躁。大元無措的手突然觸及到腰中的笛子。
蓮花聽到了久違的笛聲。她記得自己出嫁前的那個晚上,大元吹了整整一夜,她在笛聲中也坐到了天亮。那期期艾艾的笛聲硬是抓住她的心,在滿月朗朗的天空中飄飄蕩蕩。她感覺大元用笛子掏空了自己,又感覺那笛子實實在在為自己填充了很多,就是因為這笛聲,她把自己囫囫圇圇嫁了出去……從那以后,他們從山里來到這大漠,蓮花再也沒有聽過大元的笛子。現在聽到這笛子,蓮花止住了哭聲。她想不明白,大元不識譜,也沒有人教過他,他更不知道自己在吹什么曲子,但每每吹出的曲子卻總是那么可人心意。在笛聲中,你自個的心就由不得自個了,總是讓那笛聲牽扯著忽悲忽喜,忽傷忽憂。眼前這個像木匠隨意幾斧子劈出人樣的漢子,竟也有如此善解人意的心嗎?蓮花心里熱熱的,她情不自禁地喃喃道:“大元呀,這笛子,我恨這笛子……”
大元的笛聲停了,他似乎明白蓮花的意思:“蓮花,該恨,你從小聽這笛子長大,是這個笛子告訴你該怎么活,又是這笛子告訴你忘了很多應該忘記的東西……”
蓮花身子顫了一下,她咬著自己的嘴唇,咬出的仍然是那幾個字:“我恨呀,恨這笛子……”
“該恨的,”大元用笛子狠狠劈了一下天空,委屈的笛子發(fā)出幾個蒼白的音符,“這個笛子哄了我多年,現在還哄著我;這個笛子也哄了你很多年,這會又哄上你了……”大元的眼睛充血了。“這個倒霉的日子,在山里咱們靠天吃飯,吃得越來越窮。這會遷到灌區(qū)了,肚子不餓了,可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緊巴。心里憋得慌,不是這笛子能到現在嗎?”大元看了一眼蓮花,“我也恨,不就這笛子么,一個破竹管,哄得你高興,也哄得你嫁了人,又把我從山里哄到了灘里。總想著日子會好一些,總想著能活得順心些,可是……”
蓮花感覺大元的話說到了自己的心里,可話到嘴邊還是那個意思:“我只恨你的笛子把我嫁了出去……”
“要不是我的笛子你就不嫁了嗎?”大元像在自言自語,“那你的弟弟不娶媳婦了?我又能給你們家想要的財禮嗎?”
蓮花搖搖頭閉上眼睛,同時把心里流淌的很多東西緊緊關閉了起來。
大元甩開了腳步,大大的,很有力,腳下干得卷起皮的地面隨著撲哧撲哧的聲響,冒起青煙似的土塵。跟在身后的蓮花緊緊抿住了嘴唇。來自心底的嘆息卻固執(zhí)而強烈,唉,大元近在舉手之間,大元又距她有萬里之遙。哦,大元,大元……蓮花在心中呼喚,有著被攥緊的幸福和疼痛。以前她極力回避著不見面也沒什么,日子就在木然和忘記中悄然溜走,而現在單獨在一起,掩藏在心底的一切都一股腦兒涌了上來……唉,這日子,讓他們揮淚而別,又讓他們走到一起。
大元收住眼中的淚花,接過蓮花抱在懷里的羊皮襖,加快了步子。
三
二元和駱駝客已經走出了很遠,在平靜的沙漠上,留下的足印像一條繩索,緊緊牽扯著大元和蓮花。大漠在無風的陽光中溫暖起來,一只只兔子不時在柴禾中小心地來回穿梭。慢慢的,柴禾少了,不知在什么時候就消失不見了,出現在眼前的仍是連綿不斷的沙丘。這些沙丘已經很像山的樣子了,高高的沙山擁著一道道彎,很有山彎的味道。在這彎里,一人多高的黃毛柴泛著金浪,沉甸甸地垂頭而立,仿佛專門在等著他們的到來。
大元隨手捋上一把揉了揉,用嘴一吹,金黃的柴籽飽滿地躺在手中。喜悅讓大元的眉頭舒展開來,而蓮花也忘記了所有的不快和痛苦,靈巧地在黃毛柴中穿梭,臉上笑意盈盈,似乎又回到了從前。大元有點動情了,他摸著黃毛柴頭,像摸著已經到手的豐收:“蓮花呀蓮花,老天爺可憐咱們,看來這次是走對了,這么好的柴籽,打上十天半月的,弄個五六百塊不成問題……”
蓮花的臉上全是感激:“大元,我沒想著五六百,要能弄上個一兩百,我就高興死了。”
大元笑了,指著沙漠說:“一兩百塊還不夠咱們的辛苦錢。蓮花,幸虧老天讓沙漠長了這柴籽,只要人勤快,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喜悅已經醉倒了這些走進沙漠的人,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二元他們瘋狂的吼聲,張五放肆的“少年”也緊跟著傳了過來:“尕妹妹那個夾緊了你等著,哥哥掙上個錢錢了就回來……”
當大元和蓮花向前走的時候,已經卸完東西的駱駝客迎了過來。這個臉上像沙漠一樣荒涼的老人跳下駱駝,笑呵呵地說:“大元,很少見的黃毛柴籽呀,這回你們可算是來好了。”大元也笑,笑得很開心,老人繼續(xù)說,“你們以前沒到過沙漠,一定要小心,太陽偏西就往住的地方走,晚上有人沒回來就在高處的沙丘上點柴火,千萬不要去找人。另外,不論發(fā)生什么事,都不要自己走,一定要等著我,沙漠迷路就是要人的命。”老人看大元點著頭,又爬上了駱駝,“好好干吧年輕人,等你回家后,可要好好給我吹個笛子。你的笛子吹得好呀,吹得好。”
老人意味深長地看看蓮花,笑出幾聲意思來,吆喝著駱駝上路,沉悶的駝鈴在大漠孤寂地叮叮咚咚……
豐收的黃毛柴籽讓五個人實實在在的感到了希望,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發(fā)自心底的笑,這笑容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使每個人都主動想干些什么。張五選擇的駐地確實不錯,中間一塊沙地無疑是一張暄軟的床,而四周一人多高的密密實實的柴禾不但可以擋風,而且能很好地隱蔽他們的東西。當張五和朱三拾來一大堆柴禾的時候,二元架起了鍋灶,蓮花開始準備簡陋的晚飯。
大元坐在高高的沙丘上,讓慢慢寒冷的風吹瞇了雙眼,太陽飄浮在虛無成煙幕的大漠之上,流溢著令人心悸的蒼白和寂寥,最后被黑夜一點點吞噬,星星已經眨著賊亮的眼睛在天幕閃爍。這一切,盡情被他的笛子吸了進去,然后又用另一種形式娓娓婉婉地還給了大漠。
大元和蓮花最后放下碗筷,剩下的面湯自然被二元喝了,蓮花收好所有的碗筷,悄沒聲息地去洗。朱三高興了:“還是帶個女人好呀,就像在家里。”
二元立即罵:“狗日的,得了便宜就好,蓮花今天走得慢了些,你張嘴就罵。”
朱三卻也不惱,往火堆中扔進一些柴禾,隨著火焰的跳動憨憨地笑了。張五看看大元,又看看蓮花,隨意的“花兒”脫口而出:“蓮花花枯了者還會開,笛笛子啞了者還會響……”
大元順手一笛子敲在張五的頭上:“響個球……”不自制的眼神飄向蓮花,看到蓮花的手顫抖了一下,他的心也抖了,輕輕的,卻感到一種莫名的躁動。
等到燃著的篝火熄滅,蓮花打開手電,照著大家把灰燼均勻地攤在地上,又在上面蓋一層薄薄的沙子,然后鋪開被褥。行走了一天的疲勞很快侵襲而來,二元和朱三的呼嚕一起一伏地響起,張五的少年也慢慢被黑夜吮吸。蓮花睡在大元旁邊,兩人全無睡意。在野地過夜的陌生,使她老害怕旁邊的空虛,身子不由自主地攏向大元,大元的呼吸快了起來,兩人的心跳激動而有力,好像整個大漠都喧響著他們的心跳,滿天的星星都在對他們擠眉弄眼。蓮花閉上了眼睛,大元也把滿天的星星關進了自己的眼睛,而蓮花已經在悠悠的笛聲中浮了起來,輕輕地暖暖地漂浮,飄向那個讓自己成為女人的日子,那個日子,哦,那個日子……流翠的山谷里到處涌動著令人心醉的春潮,馬蓮花開得正旺,鮮嫩的花瓣如一張張小嘴,毫不回避地傾吐著自己的欲望,山雀子在這種欲望中興奮不已,盡情進行著自然的交配,而發(fā)情母羊的氣味越來越濃,越來越重,為數不多的公羊亢奮不止,山里的天空讓這種氣味熏染得含情脈脈。那同樣亢奮的笛聲在含情脈脈中突然歸于寂靜,一人多高的馬蓮叢起伏著令人心顫的慵懶,受精后的花瓣無聲地落下,落下……蓮花輕輕喊出了聲,輕輕的,就如花瓣落下的聲音,而大元就在這喊聲中睜開眼睛,又放出滿天的星星,賊亮賊亮的星星呀……大元感覺到一只欲望的手緊緊噬咬著自己,在這種噬咬中,他輕松地放開了自己,他感覺自己壓在枕下的笛子正在沉醉地吮吸這種感覺,他驚奇星星怎么跑到了蓮花的臉上,亮亮的,一顆、兩顆……荒蕪的大漠因為這種情景,似乎溫馨起來……
太陽溫暖大漠的時候,勤勞的人們已經有了沉甸甸的收獲。
蓮花的靈巧,使她如魚得水,她用小腹把懷里的簸箕抵緊在柴禾上,兩手輕松地揉著黃毛柴頭,她能感覺柴籽落進懷里的充實。等簸箕滿了,她就快步走向高高的沙梁,鋪好的單子上面,已經是小山一樣的黃毛柴籽了。蓮花開始就著大漠的微風揚去其間的皮皮草草,金黃的,如油菜籽一樣大小的黃毛柴籽干凈地堆成了一堆。蓮花輕輕收進袋子,如同裝進了孩子的新衣、春種的化肥、老人的藥片,臉上的笑容醉心而可人。蓮花掏出袋中的早飯,干硬的饅頭被凍得更加瓷實,蓮花卻香甜地啃著,每啃一下,上面就留下整齊的牙印。不遠處的大元仍在勞作,他打柴的方法粗獷而豪爽:用鐮刀割下柴頭,然后放在單子上一陣捶打。遠處,張五的少年隨著他的心情盡情在大漠張揚:“人世難得呀,得了者也難活;七十七道個坎,坎坎都得過……”
太陽落山的時候,大元背起沉甸甸的柴籽,快步走到等他的蓮花身邊。充實的收獲讓蓮花很開心,她看著大元的眼神神采飛揚。當和大元一起走向駐地的時候,竟然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
大元也是喜悅的。寂寥空曠的大漠是一種誘惑,讓許多壓抑的東西悄悄溜出了心房,有著無拘的自由和隨意。大元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蓮花,昨晚上想什么了?你的手伸進了我的被窩,我的胳膊都被你掐腫了。”
“你知道的,”蓮花的臉緋紅,她低下了頭,聲音小了些,“你知道的,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大元也笑了,笑得曖昧,他好像在自言自語:“就是,我怎么會不知道,我能不知道嗎?”
蓮花抬起頭來,有些勇敢地追問:“你知道個啥?”
大元顯得有些慌張,他別過頭去:“就是,我知道個啥呀,我能知道個啥呢。”
蓮花多少有些失望,語氣沖沖地:“就是,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記得了!”
大元好像補償似的,接過蓮花夾在胳膊下的簸箕,仍像在自言自語:“有些事情是需要記在心里的,不是掛在嘴上。過去的已經過去哩,只想過去,就沒有明個了。你知道,張五和你男人的關系不一般,有些事情過頭了,他會難為你的,就更不顧家了。”
蓮花委屈地撇了撇嘴,哀怨地瞪一眼大元:“不是為了弟弟的日子,我還不想和他過了。你知道,換門親,我走他妹也要走,我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只是他妹和我弟過得好,苦再大,我也受了……”
大元看看蓮花,眼里多了些溫情:“蓮花,這么想就對了。”
蓮花打斷大元的話,惱恨地說:“對什么?你也不看看我活的什么人?我也是個人,他一年四季不回家,又不給我一分錢。”
大元加快了步子,雖然有些慌,但很堅決:“認命吧,蓮花,我們認命吧。”
蓮花干脆停下來,她覺得雙腿軟得沒有一絲氣力,她不知大元錯在什么地方,但心里仍是在恨他。看著太陽從眼中消失,她抽泣了一下,終于挪開了腳步。
四
每個人的收獲都很不錯。朱三好像害怕自己少了,固執(zhí)地把別人的袋子看了又看,掂了又掂,總算舒展了自己的心:“蓮花和大元最多,咱們三個差不多,哈哈。”
張五有些陰陽怪氣了:“他們和咱不一樣嘛。”他細細的眼睛瞄了一下大元和蓮花,笑著把柴禾折成小截,又吼開了他的少年:
田地荒了者就荒了么,
犁頭銹了者就銹了;
今生的姻緣前世里修,
想斷個腸腸者也枉然……
蓮花忽地直起了身,冷冷地迎著張五搜尋的目光,毫不客氣地說:“張五,就你那破鑼嗓子也配唱少年?真真是狗嘴里吐不出個象牙來!”
張五的臉紅了,他有些惱羞成怒:“老子唱得不好,你唱得好你唱啊?”
朱三樂了:“蓮花,你唱,好長時間沒聽你唱了,唱他個狗日的!”
蓮花的歌聲就飄了起來:
閑吃個蘿卜淡操心,
牛娃子發(fā)情者你著啥急?
自家的田地我做主,
想讓誰耕也輪不上個你!
大元惱了,他大喊一聲:“蓮花!”
蓮花摔了手中的碗:“你又不是我男人,你吼個啥?對你婆娘吼去!”看著大元的嘴唇在顫抖,蓮花低下了頭,可嘴卻不饒人,“張五,麻煩你狗日的給那個壞捎個信,再不回家把老娘逼急了,讓他試試看!”
二元把火弄得劈劈啪啪響,聲音也跟牛似的:“都不要扯雞巴蛋!狼不吃野狐子,都是個跑山的!日后要是聽到哪個狗日的到村里嚼舌根子,我二元把狗日的腿卸折!”
眼看一場好戲就要散場,朱三有點急:“張五,你狗日的好歹也算個男人,就這么不中用?”
張五看看火光下大元鐵青的臉,撇了撇嘴,一屁股坐在沙上不吭聲了。晚飯草草吃完,大家都圍在篝火邊靜坐不語,唯有二元喝湯的聲音呼嚕呼嚕。大元往火堆里丟些柴禾,從腰里摸出了笛子。
大元僵硬的手指開始在笛子上輕靈地起起落落。二元也喝完了最后一口湯,長長地呼出一口氣,他總覺得大哥在吹笛子的時候很苦很苦,苦得讓他想哭。蓮花突然驚奇地發(fā)現,大元在吹笛子的時候眼睛竟然是閉著的,在它閉著的眼睛里,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張五的心慢慢平靜了,說實話,他非常喜歡大元的笛聲,他總覺得大元在用另外一種聲音唱著少年,唱著人心里面的東西。而朱三則躺倒身子,嚼著一根柴棒子,計算著每人口袋里的黃毛柴籽。
火光在每個人的臉上跳躍,不時隨著噼啪的聲音爆出一個個火星……大漠靜了,兔子睡了,星星眨著寂寞的眼睛,風輕輕吹過,挾帶著來自大漠深處的蒼涼與無奈,還有陌生的近乎原始的氣息……大元的眼睛微微眨了一下,蓮花發(fā)現了他閃著的淚光,低下頭去,心里涌出一種揪心的痛楚,而二元看看蓮花,則是徹底閉上了眼睛。火光又跳躍了一下,熄了,濃濃的夜色緊緊包圍了這些人,但笛子卻似乎更為響亮地劃破夜空,久久不息……
大元放下笛子,輕輕嘆口氣,他往灰燼中扔些柴禾,重又燃起了篝火。他的聲音沉沉的,好像極不愿意地張開了嘴:“我們都是放羊娃,為了個日子,從山里搬到這灌區(qū),日子是好了,可日子也更難腸了。”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么,無奈地搖著頭,“我和蓮花的事情你們都知道,我們走不到一塊,就是因為我窮,蓮花窮。窮是個殺人的刀子,能把什么都給殺了,想想都難心。可如今這個世道我們又能怎么樣?你掙上三個,人家想方設法弄去你四個。花錢澆水,還要請人家吃飯,化肥漲價,農藥漲價,你要買的東東西西都在漲價,勤快,值不了幾個錢。”大元嘆口氣,“這就是我們的命。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提了,對誰都不好。”
每個人都嘆出一口氣來。張五干癟地笑出幾聲來:“窮歡樂,富憂愁,都不要唉聲嘆氣了,老天有眼哩,要你過的艱難少不了,要你享的福也少不了。” 他有些歉意地看看蓮花,“蓮花,我其實什么都沒說過,你男人是和我關系好,他知道你和大元的事情,但他在外面混也是不想受這里的苦、不想遭這份罪,并不是你和大元的原因。可是讓你受苦受罪了。”張五剜了一眼大元,“大元,我是佩服你的,做人做事都服你,可人世上的驢事情多了,有啥呢?不要苦自己,也不要苦別人。”
二元打斷了他的話:“你狗日的一會兒人,一會兒狗,到底要卵(說的意思)個啥呢?”
朱三已經讓自己周密的計劃得意了,他打了個噴嚏:“睡吧睡吧,明個還要干活呢。”
躺進被窩的時候,大元聽到了蓮花的呢喃:“張五說的在理呢。”他閉上眼睛,心里亂亂的,無法自制地翻轉過身,心里卻在想:那只手還會伸進夢中嗎?
五
大漠像一個美麗的蕩婦,剛才還溫柔地和你親熱,一轉眼的工夫,如同一個披頭散發(fā)的瘋子瘋狂地發(fā)泄著自己的不滿。大風卷起沙塵,遮天閉日地呼嘯而至,睜不開眼睛,嘴一張,馬上就填上沙子。黃毛柴籽怎么都無法打了,大元嘶啞著嗓子招呼大家趕回駐地,可是到住的地方大家都傻眼了:大風竟然吹燃了晚上余下的灰燼,點燃了他們睡覺的地方,呼呼響著的火苗再也沒有可愛和溫暖,毫不留情地吞噬能夠吞噬的一切。大元看看他們的鋪蓋以及柴籽都在上風頭,心里稍稍松了口氣。但他很快發(fā)現火苗不對勁,好像有人在向火苗澆著水,火苗拼命扭動著身子掙扎,同時騰起股股熱氣,就在他納悶的時候,蓮花叫出了聲:“水,我們的水啊!”
大元瘋了般撲了過去,但已經晚了:裝水的塑料桶子被火融化,里面的水全都化為霧氣騰空而去。所有的人腿一軟,跌坐在沙丘上,眼睜睜看著大火搖擺著身子,鉆進另一個柴彎……
六
沙子像長了手,扯著人的腳往深處陷,每抬一下腿都需要很大的力氣,而缺少水分的身體軟得像棉花,時時想和大漠融為一體。看似遙遠的太陽,似乎發(fā)現了難得的機會,拼盡全力散發(fā)更多的熱量,榨取越來越少的水分。大元奮力爬上山梁之后,一頭栽了下去。
天依然藍得空洞,藍得無動于衷,連連綿綿的沙丘默默地挽緊了手臂,大漠陷入死一樣的寂靜。偶爾一只兔子翻越沙丘。微微一陣風吹過后,大元睜開了眼睛,在翻身坐起的一瞬間,虛脫的暈眩使他眼冒金星。大元舔舔干裂的嘴唇,感覺到了鉆心的疼痛。他再也無法堅持,從懷里掏出一個凍硬的生土豆來。
這是唯一能給他提供水分的東西了。昨晚風停之后,大元已經想好了應急的辦法,他把生土豆以及醋、醬油等能夠解渴的東西平均做了分配,他一再重復駱駝客說過的話,要大家堅持到底。同時他給大家講了一個也許并不存在的秘密,蒙古人為了駱駝的飲水,每相距十五公里就開鑿一眼水井,只要能找到其中的一眼大家就有救了。找到水井也就成了大家共有的希望。天剛一放亮,他便催促大家分別朝不同的方向出發(fā)。在沙漠里走了一個早晨之后,他已辨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了,粗略算算,至少走了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但連水井的毛也沒有看見。不知其他的人怎么樣,說好了誰找著水井就在沙丘上燃放煙火,可是除了大漠的空曠,就是空洞的藍天,哪有什么煙火?
大元吃進最后一口土豆。被凍硬的土豆確實含有不少水分,大元貪婪地吮吸其間的水分,榨干之后,唾出鋸末一樣的土豆渣。但是一時的清涼過后,嘴里更加焦渴,似乎有永遠也吐不完的沙子,糙糙的讓人有一種莫名的煩躁。大元使勁站起身來,不論怎樣,也得趕緊回到住的地方了,斷水才一天的時間就這樣艱難,還有八天的日子可怎么過?當踏上返回的路程時,他才突然想起蓮花,早上,他是和蓮花一起走的,沒想到只顧著找水井,竟然不知道蓮花在哪里了!
無風的大漠就像豐滿的女人一樣攤開四肢躺著,慵懶而風情萬種,柔情地接受一切可以接受的東西。大元跟著自己來時的足跡緊著返回,他想呼喚蓮花的名字,但干燥的嗓子使他很快放棄了這一念頭。當他急匆匆爬上一道沙梁后,終于看到了蓮花的影子。
這是一灣長勢瘋狂的黃毛柴,要不是站在高處,大元怎么也看不到蓮花的影子。而此時的蓮花,似乎瘋了,她瘋狂穿梭在黃毛柴禾中間,拼命收獲著眼前的豐收。大元看著蓮花忙碌的身影,心里突然一陣震顫,眼睛竟變得濕潤了。他不知自己怎么走下沙丘,怎么來到蓮花身邊的。蓮花的嘴唇也裂開了干皮,但臉上全是忘我的喜悅。她貪婪地揉搓著柴頭,醉心地聽著柴籽灑落的聲音,全然不知身處的險境。大元覺得蓮花機械的重復好像舞蹈一樣,有著不一樣的美麗。大元看著,一種不忍使他頹然跌坐下來。他卷上一支旱煙,拼命吸進一口,以前能給人安慰的煙味,如一股火焰一樣涌入嗓子,大元拼命咳嗽起來。
蓮花從咳嗽中醒過神來。看著痛苦的大元,她想起了該干的事情:“大元,怎么樣?找著水井了嗎?”
大元搖搖頭,但看著蓮花的失望又勸慰著她:“也許找錯地方了。”
蓮花無力地坐在了地上,臉上的喜悅瞬間消失,此時,她才感覺到嘴中的焦渴。蓮花掏出一個土豆,大口嚼起來,她連同碎渣一起咽下肚子,但更為強烈的渴望燒紅了她的臉:“大元,我們會被渴死嗎?”沒等大元回答,她又說,“不會的,你一定會找到水的,一定會!”她看著眼前的柴籽,恨不得全收了帶走,“多好的柴籽呀,你說得對,我們能掙上五六百元的。天呀,五六百元,我就能過一個舒心的年了!“
大元怔怔地看著蓮花,搖搖頭,嘴唇顫抖了幾下。他站起身來,背上蓮花沉甸甸的袋子,很難看地笑了:“蓮花,不要想太多,一切都會過去的,娃的新衣都在這里,他還等著你呢。”
蓮花沒有懷疑地笑了,和大元在一起的踏實,容不得她想更多的東西。但大元嘴唇裂起的干皮,讓她感到心疼。蓮花似乎沒有太多的猶豫,攔在大元前面,小心撕扯著他的干皮。大元沒有拒絕,看著蓮花的眼睛濕潤起來。蓮花不小心用過了勁,大元的嘴唇流血了,蓮花歉意地連聲說:“看看我笨的。”
大元吐出舌頭舔舔血,但新的血又很快流出來。大元的舉動似乎提醒了蓮花什么,蓮花毫不猶豫地抱著大元的脖子,含住了他的嘴唇:“看我笨的……”
蓮花的感嘆變成了一種瘋狂,大元的身子抖了一下,背著的袋子無聲地滑落下來,隨著蓮花的力量,大元終于伸手箍住了蓮花的身子。
埋在心底的焦渴瞬間找到了可以滋潤的清泉。陽光把他們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大漠上,拉長,再拉長……大漠沒有連續(xù)不斷的風,偶爾有旋起的風柱突然而至,很像未知的神鬼突然點燃的炊煙,帶著嘯聲急急遠去。風柱撞上纏綿在一起的人影,如一個甜美的夢,瞬間被撞得支離破碎。
兩人的嘴唇濕潤了,但臉上仍然是無法滿足的遺憾。可是,時間已經不會等待他們了。大元急急背上柴籽,近乎逃跑地向前走去。蓮花多少有些失意地匆匆追趕。
蓮花緊隨身后,聲音顫顫的,她說:“我知道你的心了……”最后的話,嘶啞著帶有可憐的哭聲了。
七
當夕陽的最后一抹亮光消失后,大元和蓮花疲憊不堪地回到了駐地。另外三個早到的男人眼巴巴看著大元,看到大元無奈的表情,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二元似乎比誰都失望,他叫了一聲大哥,竟然咧開大嘴哭了。
大元惱了,他扯開了嘴巴吼:“哭個球,省下些眼淚當水喝!”
大元的聲音嘶啞而憤怒,二元的哭聲就這樣被吼了回去。眼尖的朱三,卻一直盯著蓮花的袋子不放,鼓鼓囊囊的袋子漸漸讓他失去冷靜,他止不住沖過去,解開袋子,抓了一把柴籽,像被燙傷了一樣大喊:“我日他先人,老子們腳不沾地地找水井,狗日的們卻偷偷摸摸打柴籽!看看,你們看看!”
朱三手中的柴籽扎眼地在幾個人的面前晃動,到了大元跟前,幾乎頂住了他的鼻尖:“大元,你不會不知道吧?這里面,也有你的份吧?”
大元張張嘴,終沒能說出什么來,只好無奈地別過頭去。而蓮花卻一步沖上前去,一把打落朱三手中的柴籽:“這是我一個人打的,不關大元的事情!”
朱三嘴幾乎貼在了蓮花的臉上說:“是他讓我們找水井的,憑什么你就可以打柴籽?要不是你和他有一腿,能有這樣的待遇?”
蓮花的憤怒還未發(fā)泄,二元已經從旁邊竄上來,一拳就把朱三打在地上:“我還和你媽有一腿,你知道不?”
大元隨著二元的話音,同樣一拳捅到二元的臉上:“你怎么就改不了你的這個臭脾氣?”
跌倒在地上的二元不敢面對生氣的大哥。蓮花尖著嗓子喊:“這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你說啊?你打我啊?!大不了你們找到水井我不喝水還不行嗎?”看到二元的嘴角溢出血水,又急急地為他擦拭。
張五扶起倒在地上的朱三,鐵青著臉丟出冰冷冷的話來:“大元,不管怎么說,都是你的不對,在這個要人命的時候,都要齊心尋找水井,只有找到了水井,才有活著的念頭,人都活不了,要這些柴籽做什么?”
張五的話恰如給蓮花一個巴掌,蓮花一怔,如噩夢醒來般捂臉大哭:“是我的錯,都是我財迷了心竅。開始我操心著找水井,可是就遇到了那么好的柴籽,我走不動了,實在是走不動,那些黃毛柴籽引著我啊,我舍不得……大元,原本這些話是你來罵我的,可是你沒有說……”
蓮花的哭聲真切而凄惻,在寂寞的大漠里寒冷而悲愴。哭聲中,所有的男人都長嘆一聲,無力地癱坐在沙地上。
夜色就這樣密密實實地擠了過來,像無形的冰塊,不動聲色地向沙漠中的這些人逼近,最終把他們擠成冰冷的一團。越來越深的寒冷,正一件件剝去他們的衣服,使他們更加想念已經燒成灰燼的被褥。燃燒的柴火,忽明忽暗地在他們臉上跳出各種各樣的神色。前面烤熱了,只好轉過身去,再把脊背交給火焰,轉來轉去地往復,讓每個人都變得煩躁不安。
沒有人能吃下東西,也沒有人說些什么。人人都渴望能打破這個僵局,卻又不愿意第一個說什么。就在這個時候,似乎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大元的聲音:“張五,知道你的先人怎么死里逃生,又撿了一塊狗頭金的嗎?”
新添的柴禾燃起來了,火光明亮了很多。背對著火堆的張五哼了一聲,但另外的幾個人臉上明顯露出了興趣。
“張老實背煤的時候,煤窯子塌了。”大元拼命讓自己的聲音興奮起來,“他在里面圈了五天。”
蓮花問:“早些年前的事情了,是真的嗎?”
二元聽出了哥哥的意思,他鼓足精神讓這個故事真實起來:“這還有假?要不是張老實的狗頭金,他張家能那么闊氣地蓋房子?”
朱三直了直身子,轉過去烤著脊背:“大元你說說,老聽老人們說這個事情,還沒囫圇聽過一回。”
大元對著弟弟笑笑,他知道,這個外表粗魯的弟弟一點兒都不笨。他的聲音明顯興奮了起來:“張老實厲害呢,他給自己鼓著勁,他當時想,外頭的人肯定知道自己給困了,肯定會著急救自己的,在這個時候,關鍵要看自己能不能挺住。張老實熟悉煤窯子的情況,大致算算,就開始從窯頂上挖逃命的路。他知道,煤窯子不深,直直地向上挖,最多也就一天的工夫就能出去了。想想看,那是個真真實實的漢子,在嚴嚴實實的山里,黑漆漆的地下,張老實就像蛆蟲一樣為自己找了一條活路。”
柴火接連炸響,爆出一個又一個的火星子,心似乎被揪在了一起,即便是烤著脊背的人,也拼力扭轉頭來,看著大元明明滅滅的臉。
“不知道挖了多少時間,張老實只是不停地挖。他系著一條羊毛擰的褲帶,感覺肚子餓了,他就把褲帶緊緊,最后把自己系成了個葫蘆。老人們說,張老實能夠死里逃生,關鍵是心勁大。什么是心勁呢?心勁就是想自己的父母等著他,老婆孩子在等著他,以后的日子需要他。”
蓮花往火堆里扔了幾根霸王柴,一股白白的煙柱滲入粘稠的黑夜。火舌像一條條貪婪的野獸,舔食著粗壯的柴禾,直到燒成火紅的一團。
“可是張老實遇到了難處。他只顧著往上挖,卻忘了及時清理挖下的石渣,等他感覺呼吸困難的時候,才發(fā)現自己把自己關進了一個前后去不了的石匣子里。”
火星驟然爆響了一下,蓮花身子一顫,微弱的爆響,很快被喜歡寂靜的夜色吞噬。但大元的故事,顯然吸引了大家。張五接過了大元的敘述:“就在這當兒,我的先人哭了,哭得傷心,也哭得很生氣,他把頭狠狠釘進石壁,石壁塌了。”
蓮花倒吸了一口氣:“把人砸了?”
幾乎所有的人都笑了。大元說:“一镢頭砸出個棺材來,原來他已經挖到一座古墓下面了,棺材里,就有一塊很大的狗頭金。張老實就抱著這塊狗頭金死里逃生了。”
蓮花長長地嘆出一口氣,突然感到了一股熱浪:“要是我們能找到水,柴籽就是我們的狗頭金呀。”
張五突然就把幾根粗壯的柴禾砸進火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該死的娃娃球朝天,我就不信我們過不了這個坎!”
“就是,明天好好找一天,我就不信找不出個井來!”二元顯得信心十足,但皴裂的嘴唇,讓人感覺到他心底的焦渴。
蓮花的臉上明亮了起來:“只要找到水井,我們就算找到狗頭金了。”
朱三躺在了火堆旁,一臉的癡迷:“我要是有塊狗頭金,就是死了也值呀。”
二元笑:“死了你要狗頭金干什么去?到陰曹地府娶鬼老婆嗎?”
蓮花堅決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我保證明天專心找水井,再不打一粒柴籽!今天打的柴籽,大家都有份,我是糊涂了……”
朱三一骨碌坐起身子,眼睛亮亮的,但話在嘴邊卻拐了個彎:“看你說的啥話?誰不知道你的難腸呢……”
大家都笑,雖然干澀,但笑出一種溫暖來。
八
一個白天,似乎很快地過去,但絕望卻越來越多地降臨。在約定的時間,大元、張五、二元,幾乎同時從三個方向走到宿營的地方,不用問,看看彼此的表情,三個人都失望地躺在沙丘上。
夕陽蒼白無力地掛在天幕。大漠的落日更給人蒼涼悲壯的感覺,一股凄涼從心底如同夜色慢慢溢了出來。
“我今天遇到了一個駱駝客。”大元要給所有的人希望,“他說雖然不知道具體的位置,但肯定方圓三十里地會有一眼井的,只是沙漠里的井很不好找。”
他的最新情況并沒引起大家的興趣。二元在無意中發(fā)現一些異樣的情況,他看見自己有意在柴籽袋上做的記號有了變動,他幾乎是彈了起來,一把提起袋子,顯然,袋子的分量明顯少了很多。張五也警覺地提提自己的袋子,大元也看看,顯然,他們的柴籽都被勻去了一半。只有蓮花的袋子,仍顯得鼓鼓囊囊的。而朱三的袋子已經不知去向。大元瘋了,急忙跑到一處沙丘上,看到自己藏的兩瓶救命醋已不知去向。
“是朱三?”
三個人迅速朝著朱三要去的方向走去,很快,他們明白發(fā)生了什么:朱三看來早有計劃,早上他并沒有真的去找水井,而是藏在了營地不遠處,等他們走遠后,又悄悄回到了營地,偷了他們的柴籽,跑了!
“狗日的,要是活著出去,老子要他知道賊是怎么當的!”二元狠狠跺著腳,對著大漠喊。
“狗日的還算有點良心,沒偷蓮花的。”大元也失去了耐性,眼里都快流血了。
不語的張五突然仰頭大笑,笑出許多的意思來。不顧大元兩兄弟的驚訝,他掏出一塊干餅子狼吞虎咽。張五幾乎是強迫自己下咽,缺少水分的痛苦,是他嘴唇溢出很多的血,眨眼間,一個餅子就落到了肚中。張五說:“要想活命,現在馬上就走。”
大元搖搖頭:“蓮花還沒來。”
張五揮揮手:“那好吧。等她還是走,你自己決定,再不動彈,就沒有機會了。”他提起蓮花的袋子,招呼著大元二元:“你們看著,蓮花的柴籽我背上,一顆不少地還給她。她來了你們就趕緊往出走!”
不等他們說什么,張五毅然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夜色,如心底的絕望,慢慢籠罩了大漠。大元和二元心不在焉地強迫自己就著凍硬的土豆咽下一個饅頭,但是,蓮花還沒有回來。
大元牢記駱駝客的叮囑,走向一個很高的沙丘。他和二元砍來很多柴禾,燃起了熊熊大火。二元撕扯著嗓子大喊:“蓮花——”
微弱的喊聲很快被大漠吮吸得干干凈凈,而二元喊得精疲力盡的時候,無助地癱坐在沙丘上,呼喚蓮花的聲音,化成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號。
大元臉陰得深沉,他指使二元到背風的地方去睡,自己仍苦守在沙丘上。
夜深了,還是不見蓮花的影子。一道又一道的流星,拖著長長的尾巴,消失在遙遠的天際。天很幽靜,幽靜得近乎無動于衷。
大元臉上的肌肉一陣陣顫抖,他不時地抬頭巡視著周圍的大漠,希望看到同樣燃起的火堆,但是周圍全是黑漆漆的沙丘。
一滴淚水,終于從大元的眼際滑落。他知道,蓮花是心底憋了一口氣走的,為了抵制黃毛柴籽的誘惑,蓮花走得干干凈凈,沒有帶簸箕,也沒拿袋子,只是想著一門心思地找井。這個女人啊,井沒找到,卻把自己給丟了。
大元拼命壓制自己的抽泣,從身后取出了笛子。悠悠的笛聲響起來了。似乎從很遠的地方走來,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倏然的高亢之后,一路奔騰著,向著寂寞的天幕爬去,就在人心緊提的時候,又從很高的地方跌落,碎成了點點滴滴,撕成了絲絲縷縷,嗚咽著融入毫無感覺的大漠。而笛聲沒有停止,幽幽咽咽成無盡的纏綿,飄飄灑灑在寂靜的夜里。燃燒的柴火不時爆出一串串閃亮的火星,很像燃放在大漠里孤寂的煙花。半個殘月爬了上來,風停了,覓食的兔子停止了咀嚼,星星似乎破碎成渣子,撒滿了遼闊的大漠……
柴禾燃盡的時候,東方出現了明亮的白色。天亮了,而蓮花,仍然沒有來。大元的雙眼空洞成兩眼幽深的井,寒森森地看著連綿的大漠。
天還沒有完全放亮,二元就爬起了身,他活動著僵硬的身子,期期艾艾地看著大元所在的沙丘。二元在大元的笛聲中沉浮了一個晚上。他甚至想,要是蓮花真的走了,有這笛子相送,也不枉人世一場。
二元的嘴唇已經干裂成溝壑,他向著大元走去,一路想著安慰的話。路過一個低洼的地方,二元的眼睛一下直了,他近乎飛身撲了過去,趴在地上看,當他借著明亮的晨光看到自己的影子時,撕破了嗓子喊:“大哥——狗日的井,狗日的井我找到了——狗日的井就在我們跟前吶!”
大元聽到了二元的喊聲,他身子顫了一下,毫無顧忌的哭聲立即傳了過來。
補充水分的喜悅,很快被蓮花走失的痛苦取代。大元找來所有能盛水的瓶子裝上水。他叮囑二元守著井不要離開,晚上一定要在沙丘上燃起柴禾,等著他回來。
二元抓著大元的手,哭了:“哥,你一定要回來,嫂子還等著你啊。”
大元別過頭去:“我知道,可是蓮花也許在等著我呢。”
大漠的路很長,細細碎碎的沙丘上印著蓮花的腳印,如一根繩,扯著大元的心……
責任編輯 閻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