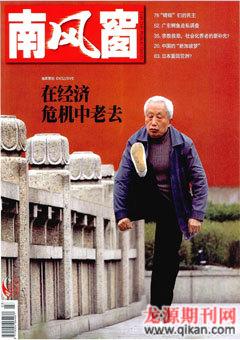危機挑戰養老難題
楊 軍
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財政收入受到經濟危機的深刻影響。在老齡化速度高于其它國家數倍的條件下,在中國整體改革進入深水區困難重重的情形下,中國能否在人口機會之窗關閉之前完成必需的改革,是中國老齡化危機中的核難題。
當東南亞和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走過巔峰漸向下行,“奇跡”已經被用老,一些海外媒體轉而使用“老去的亞洲”、“老去的中國”這樣的字眼。中國真的老了嗎?
根據國際一般標準,衡量是否進入老齡社會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60歲以上人群占到總人口的10%以上,二是65歲以上人群占到總人口的7%以上。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平告訴記者,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群比例已達11.21%,2001年,65歲以上人群比例也達到7%。至此,中國正式進入老齡社會。
老去的中國?
2007年底,中國60歲以上人群占總人口的11.6%,65歲以上老人1.06億,占總人口的8.05%。2008年的統計數字還沒有公布,據推算,60歲以上人口接近1.6億,65歲以上人群可能會達到1.09億。人口老齡化速度在加快,且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加快。2009年,解放后出生的人群將陸續達到60歲,上世紀5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批人將進入老年序列,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國“老去”的速度。
“其實現在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壓力并不大,在未來10~15年可能才會感到壓力。到2030年,中國老齡人口可能會達到20%甚至30%。”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告訴記者,“從預測看,2048年中國老年人口可能會占到總人口的1/3。到老齡化高峰的時候,中國社會各方面壓力都會比較大。”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一些研究機構陸續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做過一些比較著名的報告。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銀發中國》報告指出,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3.97億人,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人口的總和。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之后的人口增長基本上靠慣性和延長壽命來取得。根據CSIS測算,中國的勞動人口大約在2015年達到高峰,而總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現。
世界銀行曾公布的兩份發展報告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于1968年前后,于2010年前后終結。按照世行的分析,2015年中國老齡人口將升至2億,2044年更高達4億,在養老和醫療等方面將可能造成較大的財政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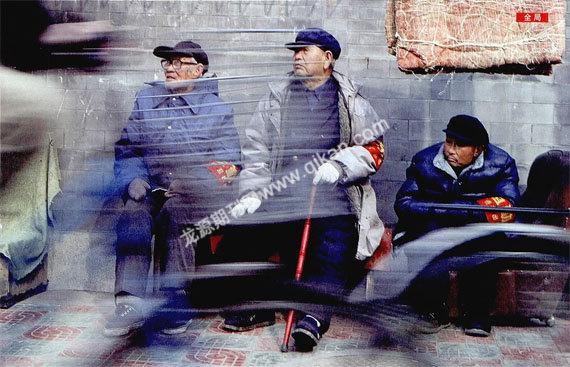
在預測中國老齡化高峰的時間上,不同的機構和學者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中國社會老齡化壓力將日益增加。
全球許多國家,尤其是日本、歐洲國家和拉美國家,也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變化的難題。相比之下,中國面臨的難題更大一些。日本等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長期過程,經過100多年才開始面臨勞動力短缺,而中國只用了幾十年。為了控制人口數量,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應該說,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計劃生育的實行是合理的,而且效果顯著,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
可以說,中國的生育率轉變是與社會變革和經濟轉型同步發生的,但客觀上,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單邊突進”,相關的其它社會政策并沒有及時跟進,甚至長期缺位,使中國社會老齡化過程比其它國家快了很多倍,從而埋下了中國未來潛在的老齡危機。雖然日本、歐洲和美國等國家的人口增速未來都將進一步放緩,但任何一個經濟體放緩的步伐都不會像中國這樣急劇。中國社會將承受的老齡化壓力自然也會隨之放大。
在1980年代,富有遠見的人口學家已經提出中國可能會“未富先老”的預警。“政府部門已經意識到了老齡化問題,并且一直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只是中國以前關于老齡化的研究大多只是從人口結構來認識,沒有從整個社會來看,現在已經開始從戰略角度進行研究。”郭平告訴記者。
最好的養老方式
因為老齡人口比例日益增大是世界性問題,尤其在發達國家更加明顯,很多國家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解決經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國家一度想大力發展養老機構,但很多老人感覺并不好,甚至有老人覺得住在養老院像住在集中營。現在西方國家已經讓老人回歸家庭,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大力發展社區服務,從制度上保證老人生活在社區和生活在機構能獲得同樣的服務,并通過對有老人的家庭進行福利政策傾斜等確保老年人可以在家庭中獲得舒適生活。
美國在社區開辟了各種老人服務項目,包括送飯上門、送醫上門、送車上門、定期探望、緊急救助等。出遠門時,只要給市政府相關部門打個電話,專車會按時開到家門口,辦完事還會把人送回。許多服務是免費的。目前,發達國家機構養老最多只能達到老人總數的8%,美國、英國等則有高達95%的老人在家庭養老。
中國目前主要有三種養老方式:由政府承辦的社會基本養老;傳統的家庭養老;以個人儲蓄為主的自身養老,也就是獨自生活。目前中國養老機構床位基本占到老人總數的1.5%左右,雖然數量很少,但在養老機構生活的老人還不到1%,養老機構依然存在空床位。因為中國有大家庭的傳統,家庭養老更適合中國。
“現在中國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區服務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補充。”郭平這樣描述中國的養老模式,“實際上,即使在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未來機構養老能發展到5%~7%已經很不錯了,主要還是依托家庭社區。”調查顯示,中國有90%的老年人養老方式首選家庭。
隨著老年人口高齡化、高齡老人喪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數增加,家庭養老的經濟負擔和生活照料負擔日益加重,而生活節奏越來越緊張的中青年夫婦常常難以兼顧對老人的贍養與對子女的撫養,夫妻雙職工也使得白天上班時間沒有能力照顧老人。中國家庭養老對社區服務需求非常迫切。
郭平告訴記者,中國的社區服務最近這幾年剛剛開始推行,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社區服務的建設還沒有明顯的時間表,上海、北京和長三角一些發達城市相對較好,已經開始啟動一些項目,比如上門醫療服務、送餐服務、建立護理中心、星光之家等。中等發達地區、中西部一些城市,欠缺較多,不只是理念上,資金、設施等都不足。
一些城市社區全面推廣“政府購買養老服務”,轄區內高齡、獨居的困難老人,部可以享受由政府出資購買的上門服務,由社區落實家政服務員,所需資金列入政府年度財政預算。
“真正的壓力還不是養老金支付或養老的經濟支持的能力,而是對老人提供的綜合社會服務是不是充分。”郭平表示,有關政府部門吸收經驗非常快,引用的都是西方國家的經驗,社區服務問題想得很周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員素質,目前愿意并且有能力從事社區服務的人員很少,絕大部分人員沒有經過系統的專業培訓,不具備養老服務護理員的專業資質和執業資格。
楊女士還沒到退休年齡,她父親已經去世,老母親有輕微的老年癡呆,時不時犯糊涂,平時必須有人守在身邊她才能放心上班。為此,楊女士為母親先后找了不下10個保姆,但沒有一個滿意的,有的保姆做飯難吃,有的保姆完全不會使用廚房設施,有的偷偷克扣菜錢自肥,更有甚者,只要楊女士不在,便根本不理會老太太的任何要求——這是中國家政服務市場的常見狀況。
除去人員素質問題,社區服務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目前各地開展的居家養老服務,雖然承諾的服務內容和項目較多,但實際上真正提供給老年人的往往比較單一。居家養老組織體系中各有關部門之間也缺乏有效配合。
老年產業剛起步
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增加,和社區服務一起崛起的必然還有老年產業,老年產業目前在中國同樣處于起步階段。說起老年產業,一般人們首先想起來的就是養老機構,中國老年公寓、敬老院以及社會福利院的建設,不僅嚴重滯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缺少護工,在養老院不能定點醫保,缺少子女精神上的關懷,等等,目前中國的養老機構普遍存在諸多問題。調查表明,老年人愿意在福利機構度過晚年的比例為10%~20%,這個比例并不高,但空床率卻達到了24.4%。
上世紀90年代,有一部分商家曾經瞄準過老年產業,老年保健品一度熱銷,而且屬于暴利。但這暴利其實并不正常,只是特殊時期的偶然現象。“進入老年產業的服務也好,機構也好,想謀取暴利不可能,這個行業屬于微利長期發展的行業。”郭平告訴記者。
“養老院的利潤像刀片一樣薄”,業內人士這樣形容。“除非是昧著良心做,不然在中國投資養老事業不一定能掙大錢,至少在目前掙不了。”在首屆中國養老事業發展論壇上,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曾經如是說。這也是中國養老產業的現狀。
“目前中國的養老產業利潤確實很薄,但這個市場潛力巨大。現在的老年用品博覽會上,大都是歐洲、日本等的產品。”杜鵬認為,中國的養老產業還有待進一步開發,比如老年淡季旅游、候鳥式養老、老年用品、老年保健品、老年活動場所等等,很多新產品都很有價值。現在的中國養老產業還只處于提倡階段,并沒有完全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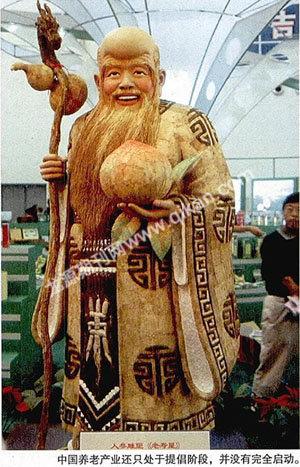
中國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比較高,并不是因為中國的老年人身體功能缺陷更嚴重,而是因為家庭設施缺陷造成的,很多家庭設施不適合老年人用。比如大部分浴缸,老年人即使腿腳靈便,也會因害怕摔倒而不敢使用。目前中國市場國內設計的適用于老年人的家庭設施和生活用品很少,即使有一些,也多是瞄準高端市場,這個階層的老年人消費水平較高,產品利潤空間也比較大。適用于一般老年人的家庭設施和生活用品發展空間非常大。
中國的老年產業雖然處于起步階段,但勢頭不錯。有些城市已經建成了老年公寓,雖然只是房地產業在低潮期為促銷造的一個概念而已,但畢竟已經有人把目光轉向了老年人。
人口的機會之窗
“老齡化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老年人問題,主要指老年人自身生存狀況,包括老年人的吃穿住用等。二是帶來的發展問題,對社會的影響。”杜鵬告訴記者。
養老模式、社區服務的建設、老年產業的發展等主要都是為了解決老年人問題,除此之外,老年人問題比較重要的還有代際關系。過去幾十年,中國是以少兒為主的社會,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東部發達城市,老年人已經多于兒童,上海兒童只占10%,老年人則占到了20%。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時候,中國14歲以下少兒占43%,現在則占不到20%。所以原來發展幼兒園、小學,現在則應該發展老年機構、老年大學。在解決老年人問題方面,很多城市已經做了不少工作,北京2008年10月出臺了十幾項優惠政策,給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老人每月發放200元補助。
和老年人問題相比,老齡化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帶來的危機會更嚴重,解決起來也要難很多,因為這方面問題的解決有待于中國整體改革的推進。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社會收入分配政策和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是使老年人難以及時和充分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原因。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體制改革是解決老齡問題的前提。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期滯后等才是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所在,老齡化只是一根“導火索”,或者說,人口老齡化只不過是使社會問題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暴露出來。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布隆教授應對“人口紅利”終結的總思路是政策制定者必須以前瞻性的眼光來思考人口問題,考慮到改革成效的顯現需要時間,政府應大力投資于教育、醫療和創造就業之上,而且越快越好。
杜鵬告訴記者,未來中國的勞動力還在增多。預計20年左右的時間才會停止增長,勞動力負增長大概要到30、40年之后。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雖然已經接近尾聲,但人口紅利期還沒過去,中國還處于人口機會之窗中。對中國的人口機會之窗到底何時關閉,業內看法并不一致,有意見認為,2020年人口機會窗口就會關閉。另一方面,從財政收入看,中國也已經完全具備建立國民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實力。
2009年是1929年那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80周年,新年伊始,全球經濟似乎依然看不到曙光,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財政收入都受到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老齡化速度高于其它國家數倍的條件下,在中國整體改革進入深水區困難重重的情形下中國能否在人口機會之窗關閉之前完成所有必需的改革,是中國老齡化危機中的真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