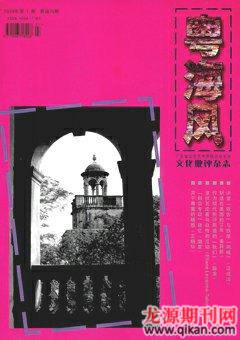“群眾專政”瑣憶
樊 星
“文革”中“砸爛公、檢、法”的口號一度十分流行。取代“公、檢、法”是“群眾專政”。
所謂“群眾專政”,就是依靠人民群眾對階級敵人(從“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到“叛徒”、“特務”、“走資派”)進行監督、管制。這一方面很能體現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因為當時的“政治犯”急劇增加,監獄里人滿為患,只好發動群眾進行監管。而那些被管制的對象就叫“群專對象”。
最能體現“群眾專政”強大威力的,是這樣一些口號:“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動員起來,打一場‘清理階級隊伍(或‘清查“五一六”)的人民戰爭!”“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記得剛上小學不久,“文革”爆發了。一股抄家的洪流迅速蔓延開來。“紅衛兵”組織可以不經過任何審批,打著紅旗,喊著口號,闖入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們的家中,去亂抄一氣,看能否發現秘藏的“變天賬”。結果當然常常是沒有。但多多少少會翻出一些舊時代的金銀首飾、“奇裝異服”、照片和收藏品,那都會成為“妄圖復辟失去的天堂”的“鐵證”,被展覽、沒收。一度,武漢曾經舉辦過“紅衛兵”“破四舊”的成果展覽。許多人看后的體會是:“第一次看見了,原來金條是那個樣子的!這算是開了眼界!”也有人佩服“紅衛兵”:“了不起!要是有哪怕一丁點私心,抄家的時候順手牽羊,哪個會發現?!”記得我家樓下,住著一家人。夫妻都是母親的同事,兒子是我的同班同學。這兒子的奶奶平時對人熱情,大家都叫她“王太(婆)”。沒想到有一天,母親單位的一批人打著紅旗來抄家,我們才知道她原來是地主婆,本名叫楊發喜!在她家被抄的過程中,鄰居們都在旁邊圍觀。在將她家抄了個一塌糊涂以后,人們好像沒什么重要收獲,只好貼了幾張“大字報”,勒令她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然后收兵了事。人們走后,那一對夫妻才默默地開始重新整理被翻亂了的家。有幾個年紀比我大的男孩子,革命的熱情意猶未盡,又聯名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地主婆楊發喜平時如何假惺惺地感慨今天的“伢們造孽,早晨起那么早去上學”,而她當年總是睡到早上九點才喝了牛奶去上學,認為這些話包藏了險惡的用心,妄圖動搖“革命小將”的革命意志,“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字報”貼在了楊發喜的門口,大家仍憤憤不平,去公用廚房將正在忙著給孫子洗澡的楊發喜揪了出來,給她帶上一頂寫有“地主婆楊發喜”字樣的高帽子,讓她跪在門廊中間,接受“革命小將”的批判。我站在一邊看了好一會,也跟著喊了幾句“革命”口號,但腦海里浮現出的,卻是每次上學和放學路上,與她相遇時,她總是笑瞇瞇的樣子……那一晚上,好像折騰到很晚,沒有一個人去制止那一切。不久以后,“抄家熱”隨風而逝,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政治觀點的兩派群眾的大辯論和大武斗。
那時“學習班”十分興盛,就是對有“問題”的人辦“學習班”,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批評教育,幫助那些人提高政治覺悟。毛澤東得知后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人民日報》1968年2月5日)但隨著革命的升溫,“學習班”常常成了“不說清楚就別想出去”的變相“監獄”。有“問題”的人被關在里面,反復交代“問題”。又因為那些“問題”常常是嚴肅的“政治問題”,所以必須對那些人實行“隔離”。這樣,許多單位都有了關押“走資派”和“反革命”的“學習班”,由“革命群眾”輪流值班看管,到了吃飯時間可以由家人送飯(這當然比蹲監獄強)。我記得一位“走資派”的小兒子在給父親送飯時,被“革命覺悟”非常高的值班群眾發現了問題。當那“走資派”的小兒子離開時,被攔住搜身,結果搜出了一個小紙頭。打開一看,雖然只是對家人的問候,但也顯示了“走資派”的“極不老實”,結果罪加一等,受到更加猛烈的批斗。
這樣的“學習班”,后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存在。一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我下鄉時農村干部在訓話時還開口閉口“哪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就辦他的‘學習班,讓蚊子咬死他!”那些干活“吊兒郎當”的人,那些敢于頂撞干部的人,都會被關進“學習班”。在那里接受“勞動改造”。不僅每天在民兵的監督下干苦活,而且在“學習班”期間的勞動是沒有任何報酬的。到了晚上,住在沒有蚊帳的“學習班”里,任憑蚊叮蟲咬,苦不堪言。有時遇到民工大規模集中勞動的時候,這些人常常在民兵的押管下,一邊敲著鑼,一邊按照指定的路線到處示眾,無可奈何地喊著這樣一些話:“我是×××!因為不服從管理,受到游堤的處分!大家都不要向我學習!”社員們都這么說:“進一次‘學習班,等于刮(讀“夸”)了一層皮!”邊說邊搖頭。住“學習班”的常常是那些家庭出身比較“好”的青年,他們常常因為家庭出身“好”而無所顧忌。而地、富子弟則因為非常聽話、干活賣力,不會身陷囹圄。我當時就想,這樣復雜的社會現象,也許只好以“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來解釋。毛主席不是也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嗎?
“學習”是需要“調節”的,那“調節”就是“勞動改造”。對于“走資派”、“五類分子”,罰打掃廁所,罰掃大街,是非常普通的“功課”。而那些“走資派”、“五類分子”在飽經精神折磨以后,干體力活,反倒成了暫時的解脫。《芙蓉鎮》中描寫的“五類分子”秦書田和胡玉音在“文革”中每天清早罰掃青石板街是那個年代常見的場景。
“群眾專政”的另一“創舉”也堪稱奇觀:把給犯罪分子量刑的權力交給群眾。上初中時的一次晚自習時間,老師給我一份鉛印的材料,上面印有準備公判的一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罪行。我的任務是讀給全班同學聽,然后征集同學們的意見,反饋上去。我至今記得在讀“強奸犯”和“奸淫幼女犯”時感覺的不自在,記得當時有同學發出的竊笑聲。而那次大家議論的結果是“一律槍斃”!當然,這樣的“群眾意見”是不可能作數的。
“群眾專政”在那個年代深入人心。許多普通人都自覺“繃緊了階級斗爭的弦”,百倍警惕地監督“階級敵人”。我所在的中學也揪出了幾個反革命分子,都是出身有問題的老師。我記得在幾次批判大會上,她們被點名站在主席臺一側,低頭接受同事的批判。只記得在批判鄧元貞老師時,有老師揭發她的一大“罪狀”是:在批評教育學生時也說英語,很成問題。但這樣的揭發反而使我們對她刮目相看。認識了這幾個“階級敵人”以后,不諳世事的同學們也常常以特別的方式去發泄對她們的仇恨:有時是在她們鋤草時奪過她們的鋤頭,不顧她們的乞求,故意將那鋤頭和鋤把弄散,然后命令她們重新將鋤頭和鋤把安到一起,繼續“勞動改造”;有時又是在她們喂豬時命令她們不得偷懶,或者是命令她們交代自己最近有什么“反革命”活動沒有。有一次,聽說母豬下崽時死掉了,大家自然就懷疑是在一邊看護的江翠娥搞了什么“鬼”,并幾次去突襲豬圈,想發現有什么“罪證”。最后當然是沒有結果。于是就“勒令”江翠娥認真“反省”。有時我在現場,覺得同學的做法有點“過”,但也不好多說什么,只是在心里想:她們是怎么成為“反革命”的呢?“文革”結束以后,她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好像沒過幾年,我就從《武漢晚報》上讀到了介紹江翠娥老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倒在了批改學生作業的深夜里的事跡報道。而我眼前浮現出的是江老師在豬圈里垂手而立,挨著幾個女同學的嚴厲訓斥,欲辯無語的可憐神情。
有時去農村勞動,老師也會提醒我們注意,不要和“階級敵人”說話。從電影和連環畫中看到的“階級敵人”形象多是獐眉鼠目、歪瓜裂棗,所以只要看到形象丑陋者,都會懷疑是“階級敵人”,而感到緊張(怕他進行“階級報復”)或警惕(防止他從事破壞活動)。
“階級斗爭天天講”。“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記得我下放農村時,每當麥收或者“雙搶”的農忙時節,在干活之前,生產隊長總要提起一件事:“地主分子王祖英為了破壞我們‘抓革命,促生產,別有用心地散布什么‘蓄精神,養精神的反動謬論。我們一定要擦亮眼睛,識破她的陰謀詭計!”我專門向社員打聽那“反革命言論”的由來,才知道那是好多年以前,王祖英好心提醒鄉親,干活不可不注意休息。但要抓階級斗爭,又沒有更合適的例子,于是,那句善意的提醒就成了“反革命言論”了。從那以后,我開始注意觀察王祖英——一個體態較為發福的中年婦女,總是笑瞇瞇的。在聽批斗她的那些話時,也并不低頭,好像批判的是別人一樣。她的兒子在勞動中也漸漸與我們混熟了,他是一把勞動好手,休息喜歡和大家一起瘋瘋打打。只是有時打得認真起來,吃不起虧的貧下中農子弟會大罵他是“地主的狗崽子!”這時,他才會尷尬地住手,說一聲:“這就沒意思啦!”而大家也都會向著他說話的。
在“五類分子”的門上,是統一釘了一塊小木牌的。那木牌上寫著督促他們自覺接受貧下中農監督、老老實實遵紀守法、不許亂說亂動的警告。每當從他們門前經過,我們都會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好像躲避瘟疫一樣。多年以后讀《芙蓉鎮》,才知道在湖南,還有過這樣的一幕:“不知從哪里刮來一股風,五類分子的家門口,都必須用泥巴塑一尊狗像,以示跟一般革命群眾之家相區別,便于群眾專政。”如此看來,各地的政治歧視還不盡一樣。釘小木牌的歧視顯然不如用泥巴塑狗像那么更有羞辱色彩吧。
但貧下中農與地主之間,平時其實是沒有什么隔閡的。早在母親下放的“五七干校”,我就聽母親她們悄悄議論: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怎么不那么分明?有好幾個貧下中農竟然把自己的小孩交給一個地主婆照看!而且她們在一起聊天,也親親熱熱的!這些“五七戰士”接受的階級斗爭理論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了困惑。到了我下鄉時,我也注意到貧下中農子弟與地、富子弟之間的和諧相處:在一起出工,在一起“日白”(荊州農村方言:聊天),在一起打賭。快過年時,各家都會“打糍粑”,那時,他們也是互相幫忙的:一起賣力地在石臼中用木杵將蒸熟的糯米飯搗爛,做成大鍋蓋那么大的糍粑,然后吃一頓主人家的糯米飯……而當生產隊長走過他們身邊時,也顯得視若無睹。
為什么“群眾”喜歡“窩里斗”?如果說“窩里斗”常常與蠅頭小利的爭奪有關,那么,那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層出不窮的、純粹是出于“革命警惕性”而產生的、制造出了無數冤案的告密行為呢?那些不謀取任何私利的告密行為,只能以“階級斗爭”的教育才說得通吧?!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時勢的誤導、復雜的社會矛盾、居心叵測的人心都使許多悲劇與群眾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現在“群眾專政”已經壽終正寢了。但當我幾年前有一次聽到一位大學教授竟然談到應該恢復給“壞人”戴帽子的辦法,才能打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時,我仍然感到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