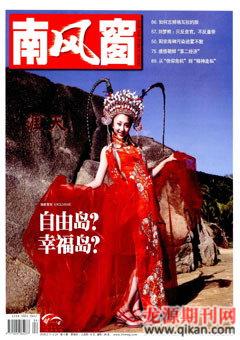喝“雞湯”人的生命焦灼
吳冠軍
于丹,不少學院知識分子給了她一個綽號——“學術超女”,因為據說她的學術功力不深,書卻賣得奇好。
人們今天為什么要讀《論語》?在談到自己的寫作時,于丹表示:“我把我的這種解讀,解釋為一種體驗式的、感悟式的闡發。什么是體驗?我的大學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所謂體驗就是‘以身體之,以血驗之,那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浸潤。”于丹之所以獲得如此廣大的閱讀群體,正是因為她把對古典文本的解讀,同當下現實中的日常生命“關聯”了起來。即使于丹對儒家思想的闡釋在學理上是那么粗鄙、錯漏,但對于儒學的一個核心思想——“道不遠人”,從寫作實踐上便可看出,于丹的理解比很多專業的學者實在要“浸潤”得多。
于丹的《論語》《莊子》解讀,是以把古典文本改編成“心靈雞湯”的方式,來使得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人們能夠“生活”得更“淡定”、更“平和”、更“安貧樂道”。那些從《論語》《莊子》中感悟出的“心得”,據說能夠使人們更為適應當下競爭激烈的日常現實,從而“就會抓住我們眼前的每一個機遇”。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有很多的壓力,面對各種社會不公、機會不均、幕后交易等等,于丹告訴讀者,“幸福快樂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孔子說,‘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內心的強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遺憾。”有了“內心的淡定與坦然”,人們就能對現代社會的各種不公坦然一笑,我自“逍遙”。這,便是于丹式寫作同當下日常現實所作出的“關聯”。
然而,盡管于丹的書以千萬冊暢銷,但是否讀者們都把這一口“心靈雞湯”喝得津津有味呢?按照于丹,“說白了,《論語》就是教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這三項是日常生活“幸福”的關鍵,那么是否如一位評論者所寫,“農民工被欠薪本應該‘淡定,下崗工人失去工作也應該‘淡定,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更應該‘淡定?”
于丹自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并聲稱讓“經典能夠活在當下”,是為了“能讓今天的中國人獲得一種可以幸福的依據”。確實,于丹的寫作字里行間處處一派“樂觀”、“幸福”,即使是那些深深陷入外在社會因素造成的各種厄境中的人們,也只須抱持據說是“孔子”的人生態度——“每個人的一生中都難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許我們無力改變這個事實,而我們可以改變的是看待這些事情的態度。《論語》的精華之一,就是告訴我們,如何用平和的心態來對待生活中的缺憾與苦難。”“汶川大地震”后,于丹站出來號召人們“替死者把好日子過下去”,而根本不去考量,在當下現實中,有多少人是在確實過著她那樣的“好日子”。
因此我們看到,于丹通過她的寫作,確實將《論語》等典籍,同當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做出了一個特殊的“關聯”。而這個特殊“關聯”的邏輯是:只要感悟出《論語》《莊子》中的道理(一碗古典中國版的“心靈雞湯”),人們每天就能夠真正地過上“好日子”。于是,透過“于丹現象”,我們真正可以看到的是:盡管于丹的著述,很大程度上是在極其惡心地“糟蹋”、“猥褻”、“意淫”國學(“十博士”語),但她那紅得發紫的“學術寫作”,確實是觸到了當下社會人們的某種普遍的生命性焦灼——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是如此地渴望過上“好日子”,是如此無奈地在尋找一種可藉此去認為當下生活是“幸福”的“依據”。
“于丹為什么這樣紅”?正因為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命是充滿著如此深重的焦灼!這就是“于丹現象”所清楚昭示的存在性的狀況。剛過去的2008年,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過下去”的話音未落,多少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上、剛剛睜開他們那一雙雙烏黑明亮眼睛的新生命,又在毒奶粉中無言地告別了他們沒有“福氣”去過的“好日子”。于丹自言“以身體之,以血驗之”,請摸著自己良心說一句,這是“好日子”么!要“淡定”,要“平和”,要“調整心態”,要“安貧樂道”,要“該放下時且放下”,請走到那一雙雙無聲痛哭的父母跟前去說!“這次大震,發生在5月12日。早一天5月11日是母親節。讓我們想想生命中還有多少個節日能夠與我們的父母在一起?”而幾個月后奶制品毒殺嬰孩事件被曝光后,于丹為何不再繼續出來,疾呼一句“保護住孩子!以命換命!”
于丹所端到人們嘴邊的這碗“雞湯”,盡管里面不含有三聚氰胺這類化學成分,但它卻通過進入日常意識形態,“無形”地毒遍——麻遍——讀者的心靈。馬克思曾告誡人們,那無形的意識形態話語,可以是最毒人的“鴉片”。2008之后,包括于丹及其批評者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都應該重新默聽一下馬克思的墓志銘:用各種理論去解釋世界是根本不夠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世界。用于丹式語言來說,就是讓人們扎扎實實地過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