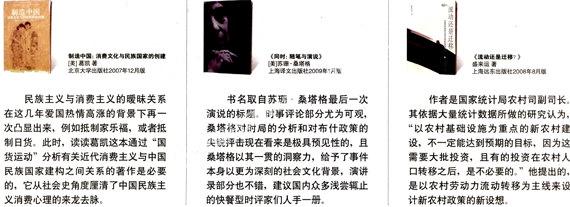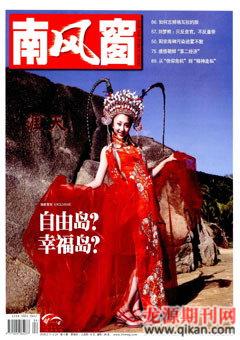理解改革,理解改革者
趙 義
有哲學家曾說,人們問我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問未來我們將往哪里走。中國30年改革開放史充滿了無數引人入勝的謎團。一組織、一企業、甚至一人的興衰起伏,足可為后來者之銅鑒。
而對于人的把握是最難的,尤其難者是那些被公認為弄潮兒的體制內的改革者。特別是在今天“還權于民,還利于民”的社會輿論高漲,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兩種改革嚴重不配套已經讓社會公眾強烈不滿的情況下,每一個體制內的改革者,即使已經退隱,或過世,也恐怕斷難“蓋棺論定”。有時對于體制內的改革者而言,能夠全身而退,已經是一種奢望。所有這一切的產生,有一個最關鍵的根源:改革開放也是政治,或者說經濟建設也是政治。
呂雷和趙洪的《國運:南方記事》在筆者看來是理解這一點比較理想的著作。在這里,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歷史與邏輯是高度統一的。最簡單的例子,廣東的開放和一段時間內的民眾外逃香港是有關系的。同樣,今天當人們比較珠三角經濟模式和長三角經濟特別是浙江經濟模式的時候,經常說珠三角經濟是候鳥經濟,內生性不如浙江模式。但當初廣東承擔的正是為國家推動開放這個最大的政治重任,這構成了體制內改革者最大的外部約束。今天廣東誓要在推動科學發展上當排頭兵,這也是如今最大的政治。
在這個最大的外部約束下,并非說改革者失去了主觀能動性,否則歷史當不是今日的模樣。是否敢于擔當,其間有天壤之別。書中一個情節很耐人尋味。鄧小平1992年南巡去的唯一一個縣級城市是順德,還特意到順德珠江冰箱廠(科龍公司的前身)去看了看。但南巡后不久,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就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順德黨政班子老老實實地承認,他們一致認為順德前景不妙,包括小平剛看過的珠江冰箱廠!原來,順德鄉鎮企業的確發展很快,但負債極重,鄉鎮企業正在患上“國企病”,企業頭頭都是鄉鎮領導兼任或任命的,短期行為突出。當地申請進行產權改革。但順德的鄉鎮企業是名震全國的典型,小平兩次來都給予充分肯定。小平一走,板凳子還沒涼呢,他老人家肯定過的東西說改就要改?改壞了誰負責?
更要命的是,順德在產權改革之前,想先把政府職能轉變了——通過機構改革把計劃經濟產生的企業的“婆婆”取消。上級主管部門勢必很不“高興”,后果自然也“很嚴重”。當年的改革者的魄力在于,認清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就給予順德一個“尚方寶劍”——省委綜合改革試點。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自然是層出不窮,告狀的不計其數。有一次謝非到中南海開會,午餐時江澤民總書記端著一碗面條向謝非走來,問道:“你的順德人又被人告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謝非解釋完后,總書記覺得有道理,表態說可以大膽一試。
歷史和人,需要多層抽絲剝繭才能逐漸理清楚。改革的復雜性就在于,比如像產權改革,至今仍有對于將國企轉讓給私人老板的投訴,在某一個特殊時期,就會成為引人關注的政治問題。但無論如何,今天人們也不得不佩服當時對上層建筑的改革魄力。如今,順德再次成為科學發展觀試點,并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直接聯系的點。人們反復提到這樣一個事實:作為綜合改革試點時,順德享有地級市待遇,許多工作同樣直接與省對接。佛山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后,順德的地級市管理權限自動取消。“繼續改革創新的各項自主權限不復存在,改革空間壓縮。”
改革之初站在浪頭上的改革者,很多都曾經歷過新中國建立前革命戰爭年代的洗禮:袁庚作為東江縱隊聯絡處處長,組織了“美軍在東南中國最重要的情報站”;謝非17歲就被任命為陸豐河田政府指導員……雖然不能過分估計年輕時成長經歷對人生的影響,但對于政治人物而言,云譎波詭中形成的意志力往往比掌握多少知識更重要。
30年改革開放,南國改革風流人物何其多!如果非要總結一下這些人物的可貴之處,那就是大政治下的勇于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