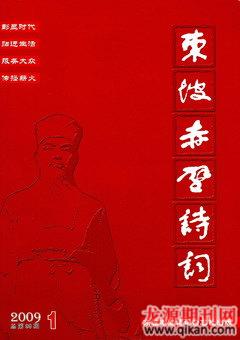從格律詩(shī)詞談到新詩(shī)
吳洪激:本刊是以傳統(tǒng)格律詩(shī)詞為主兼發(fā)新詩(shī)的詩(shī)詞文化期刊,故所發(fā)作品堅(jiān)持平水韻的詩(shī)詞格律(新詩(shī)除外)。然而,我們?cè)谝恍┛锖蛨?bào)紙上看到,一些完全不符合格律要求的所謂詩(shī)同卻層出不窮,還堂而皇之冠以“七律”或“七絕”之名,有的甚至是名人名家,攪亂了詩(shī)詞的體例,模糊了詩(shī)詞的界線。我在楚天都市報(bào)上看到您發(fā)表過很精辟的意見,您能就這一問題和本刊的定位,淡談您的看法嗎?
謝克強(qiáng):詩(shī)詞近些年確實(shí)比較熱,其中一個(gè)根本的原因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受到了應(yīng)有的尊重。中國(guó)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由詩(shī)傳承下來(lái)的;是由詩(shī)經(jīng)、楚辭、漢魏樂府、唐詩(shī)、宋詞、元令、清詩(shī)和“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奮勇當(dāng)先的新詩(shī)一路傳承下來(lái)的。中國(guó)之所以號(hào)稱詩(shī)國(guó),我想大概就是這個(gè)意思。中國(guó)孩子的啟蒙教育也是從詩(shī)開始的。這也是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大概由于這些些原因,不要說趙忠祥這樣的人,還有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huì)的某副主席等以詩(shī)言志抒情也就不足為奇了。據(jù)我所知,在中國(guó)大陸,沒有那一個(gè)縣沒有詩(shī)詞學(xué)會(huì),有的鄉(xiāng)鎮(zhèn)都有詩(shī)詞學(xué)會(huì)。趙忠祥的《神七贊》經(jīng)網(wǎng)絡(luò)傳播引起熱議,也引起更多的人對(duì)古典詩(shī)詞的關(guān)注,我以為是件好事,至少可以使人們對(duì)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的生存發(fā)展現(xiàn)狀有一點(diǎn)了解。《楚天都市報(bào)》的記者采訪我時(shí),我是說過“格律詩(shī)自有其規(guī)律,且要求嚴(yán)格,如果不合規(guī)律,比如平仄不對(duì),那就不是格律詩(shī)了。”當(dāng)然還不止這么多,但核心是這個(gè)意思。我也在《楚天都市報(bào)》上看到有的同志談到:“詩(shī)詞寫作重在意境,個(gè)別失律的地方可以接受,規(guī)范不是不可以打破的。”這個(gè)意見我不敢茍同。我以為一切藝術(shù)都重在意境,但每門藝術(shù)都有自己的規(guī)范,詩(shī)之所以是詩(shī),詞之所以是詞就是由它們的規(guī)范決定的。規(guī)范當(dāng)然可以打破,但打破還得遵循它的藝術(shù)規(guī)律,如果失律那肯定就不是律詩(shī)而只能是偽律詩(shī)了。詩(shī)人毛澤東在給陳毅談詩(shī)的一封信中就說到“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這字面上(形式上)感覺于律詩(shī)稍有未合。因律詩(shī)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shī)。”他在這里只講平仄不符,如果失律那就更不是律詩(shī)了。所以他在1957年《詩(shī)刊》創(chuàng)刊時(shí)給《詩(shī)刊》主編臧克家寫了《關(guān)于詩(shī)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詩(shī)刊》發(fā)表他多年創(chuàng)作的舊體詩(shī)詞18首外,還寫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話:“詩(shī)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zhǎng)發(fā)展。詩(shī)當(dāng)然應(yīng)以新詩(shī)為主體,舊詩(shī)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xué)。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我還注意到臧克家在《毛澤東和詩(shī)》中還轉(zhuǎn)引了毛澤東的另一段話:“舊體詩(shī)詞要發(fā)展要改革,一萬(wàn)年也打不倒。因?yàn)檫@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guó)人民的特性和風(fēng)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這是不是可以看作他對(duì)新中國(guó)詩(shī)歌發(fā)展的戰(zhàn)略設(shè)想呢,即新體詩(shī)和舊體詩(shī)都要發(fā)展,但應(yīng)以新詩(shī)為主。
貴刊是當(dāng)代中國(guó)詩(shī)詞的重地,我贊成貴刊的定位,也欽佩貴刊為發(fā)展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詞所作出的貢獻(xiàn)。
吳洪激:有人說,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格律詩(shī)詞也要進(jìn)行改革。此話不錯(cuò)。尤其是普通話的推廣,過去平水韻的許多仄聲字變成了平聲字。如拼搏的“搏”,國(guó)家的“國(guó)”等。但我認(rèn)為格律詩(shī)詞自南北朝的齊梁時(shí)期發(fā)端,直到唐初成熟定位,已經(jīng)歷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今天的詩(shī)韻改革,也須加以探索,也要一個(gè)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不能一蹴而就,故本刊專設(shè)了“詩(shī)改試驗(yàn)”欄目,就是希望接納各方面有探索性的新格律(如舊詞新韻、自度曲等)、新聲韻作品,為詩(shī)詞改革推波助瀾,積累經(jīng)驗(yàn)。不知您對(duì)此有何看法?
謝克強(qiáng):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格律詩(shī)詞要進(jìn)行改革,這個(gè)話題已說得很久了,我就看過不少人在這個(gè)問題上發(fā)表了很好的見解。要改革是一回事,怎么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這個(gè)問題不僅是古典詩(shī)詞界,在新詩(shī)界,這個(gè)問題也討論得比較熱烈。在我執(zhí)行主編的《詩(shī)歌月刊》下半月刊2008年7月號(hào)中就發(fā)表了詩(shī)評(píng)家呂進(jìn)先生的《論新詩(shī)的詩(shī)體重建》和詩(shī)評(píng)家鄒建軍的《中國(guó)新詩(shī)詩(shī)體重建的基礎(chǔ)與路徑》。不久前,我還讀到丁芒先生的《對(duì)當(dāng)代詩(shī)詞體式改革的幾點(diǎn)思考》。丁芒先生不僅在思考,并進(jìn)行了改革實(shí)踐,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新體詩(shī)。他將他創(chuàng)作的新體詩(shī)集寄給我品賞。我在品賞時(shí),不禁想起詩(shī)人毛澤東給陳毅談詩(shī)的信中的另一段話:“要作新詩(shī),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jí)斗爭(zhēng)與生產(chǎn)斗爭(zhēng),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shī),幾十年來(lái),迄無(wú)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lái)的趨勢(shì),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yǎng)料和形式,發(fā)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shī)歌。”我感覺丁芒先生似乎是在作這種嘗試。
形式當(dāng)然是重要的,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內(nèi)容。就我目及的范圍,我看當(dāng)前格律詩(shī)詞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內(nèi)容。前幾年,省直某系統(tǒng)組織了一次詩(shī)詞大賽,來(lái)稿有幾百篇(首),我應(yīng)邀作為評(píng)委,我在讀過幾百首格律詩(shī)詞之后,不僅感覺內(nèi)容大多雷同,甚至語(yǔ)言也大多相似,似曾相識(shí)。最近網(wǎng)上傳播趙忠祥的《神七贊》就是這方面的一個(gè)典型的例子。且不說它是否合律,單就詩(shī)的語(yǔ)言就缺乏詩(shī)意。這類重大題材,選擇切入的角度非常重要,不僅要有獨(dú)特的角度,更要有富于個(gè)性和張力的抒情語(yǔ)言。中國(guó)的詩(shī)歌是特別強(qiáng)調(diào)意象的,雖然詩(shī)歌和其他文學(xué)作品一樣,都是試圖再現(xiàn)什么?表現(xiàn)什么?說明什么?但詩(shī)人總是力圖避免赤裸裸的表白。創(chuàng)作實(shí)踐使我體會(huì)到,意象實(shí)質(zhì)上一種經(jīng)驗(yàn)的表達(dá)而且是自己所有的經(jīng)驗(yàn),詩(shī)人寫出它來(lái),實(shí)際上是在咀嚼自己的獨(dú)特性,或者說是形象意蘊(yùn)的再造。
吳洪激:新詩(shī)是本刊的一翼,我們開辟了一個(gè)專欄,專門發(fā)表新詩(shī)。但我在審讀新詩(shī)的來(lái)稿時(shí),總感到有些迷茫。一是讀之如嚼臘,二是甚至讀不懂。記得我們這一代人走上文壇。也是從寫新詩(shī)開始的,當(dāng)年熊召政同志那首《請(qǐng)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是那樣清新明白。令人震撼。我認(rèn)為新詩(shī)寫作也有個(gè)大眾化的問題。您是當(dāng)代著名詩(shī)人,您能同我們的新詩(shī)作者談?wù)勥@個(gè)問題嗎?
謝克強(qiáng):可以這么說,這幾十年來(lái),我沒有脫離中國(guó)新詩(shī)現(xiàn)場(chǎng),對(duì)新詩(shī)生存發(fā)展現(xiàn)狀還是看得比較清楚的。先說說詩(shī)的大眾化問題。我個(gè)人認(rèn)為,詩(shī)不是一種大眾化的藝術(shù),而是一種小眾化的藝術(shù)。有人曾說:詩(shī)屬于天才,而歌屬于大眾。這話雖然有點(diǎn)偏頗,但自從詩(shī)歌分為詩(shī)與歌之后,我們可以看到,詩(shī)是和者寡,而歌卻流行眾。因?yàn)閷懺?shī)、讀詩(shī)或者欣賞詩(shī)還是要有一點(diǎn)閑情逸致。這就致使她不可能在大眾中流行,而只能為少數(shù)人所鐘情。在我的印象里,新中國(guó)誕生后似有過三次詩(shī)歌大眾運(yùn)動(dòng)。一次是1958年的新民歌運(yùn)動(dòng),成果結(jié)集為《紅旗歌謠》;一次1976年為紀(jì)念周恩來(lái)總理而發(fā)生的“4.5”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結(jié)集《天安門詩(shī)抄》;再一次就是今年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而迅速展開的一次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就我目力所及,大概結(jié)集有幾十部之多,為中國(guó)新詩(shī)發(fā)展史所罕見。《紅旗歌謠》、《天安門詩(shī)抄》和汶川地震詩(shī)集都列在我的書架上。這幾次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的發(fā)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因?yàn)槿藗冇性捯f,有情要抒,不吐不快;而詩(shī)歌就是“詩(shī)言志、歌詠言”的藝術(shù),所以有“國(guó)家不幸詩(shī)家幸”之說。就這三次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之后結(jié)集的詩(shī)歌作品來(lái)看,客觀地說,符合詩(shī)歌藝術(shù)規(guī)律、體現(xiàn)詩(shī)歌藝術(shù)特質(zhì)的詩(shī)歌作品并不多。在這里就有一個(gè)思想與藝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了。你說到詩(shī)人熊召政的抒情長(zhǎng)詩(shī)《請(qǐng)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這使我想起我當(dāng)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chǎng)參加的一次詩(shī)歌朗誦會(huì),當(dāng)朗誦白樺的《陽(yáng)光,誰(shuí)也不能壟斷》時(shí),僅僅開始朗誦這首詩(shī)的標(biāo)題“陽(yáng)光,誰(shuí)也不能壟斷”,全場(chǎng)幾萬(wàn)人歡聲雷動(dòng)。那時(shí),詩(shī)是作為思想解放的先導(dǎo)出現(xiàn)在中國(guó)的社會(huì)舞臺(tái)上。時(shí)過境遷之后,這些詩(shī)可能只是作為一種歷史文本了。所以詩(shī)人徐遲在一次詩(shī)歌對(duì)話會(huì)上就說:詩(shī)有三個(gè)層次,一個(gè)層次是詩(shī)能夠發(fā)表,這對(duì)于一個(gè)詩(shī)人來(lái)說,不難;第二個(gè)層次就是詩(shī)發(fā)表后,當(dāng)時(shí)能引起一定的社會(huì)反響,這對(duì)于一個(gè)詩(shī)人來(lái)說,有一點(diǎn)難,但也不太難;難的是第三個(gè)層次,詩(shī)發(fā)表了,也在當(dāng)時(shí)引起了一定的社會(huì)反響,還要留得下來(lái),傳得下去。而當(dāng)今詩(shī)壇,發(fā)表詩(shī)是太容易了,有一點(diǎn)反響也不太難,難的是可以留得下來(lái)傳得下去的詩(shī)作太少。你說你在審讀新詩(shī)的來(lái)稿時(shí),總感到有些迷茫。一是讀之如嚼臘,二是甚至看不懂。這種感覺不僅是你,我在讀一些詩(shī)刊上發(fā)表的詩(shī)都有這種感覺。因?yàn)楝F(xiàn)在很多詩(shī)歌作品已經(jīng)喪失了詩(shī)歌抒情的特質(zhì)、詩(shī)美的特質(zhì)。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過,詩(shī)是一種語(yǔ)言的藝術(shù),要有富于個(gè)性的張力的抒情語(yǔ)言。詩(shī)也是一種形象思維的藝術(shù),而這種形象思維就是詩(shī)的意象,而且特別強(qiáng)調(diào)象外之象。這樣的詩(shī)才可讀、可品、可賞。反之,怎不味同嚼臘呢?
吳洪激:感謝您談了關(guān)于詩(shī)的這些精辟之見,我想這對(duì)于本刊的讀者、作者一定會(huì)有所教益,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