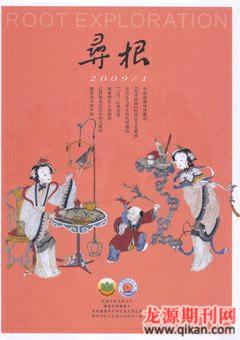寢丘與固始
戴吉強
寢丘與固始,本是兩個不同時期卻有某些關聯的歷史地名,因涉及固始是否從淮北僑置,也涉及楚相孫叔敖故里問題,從晉代爭議到現在,尚無一個相對權威的定論。筆者綜合近年資料整理情況,草作分析,并希望與方家商榷。
固始是否從淮北僑置,寢丘是否只是一地專名,在三代及秦漢時期尚無爭議。汝南之寢丘與淮南之寢丘,史籍各自表述。到晉代,杜預注《左傳·宣公十二年》楚伐鄭“沈尹將中軍”時首提:“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把“沈”與“寢”釋作同地之名,并注明曰“今汝陰固始縣”,于是“沈”即“寢”,即“今汝陰固始縣”,與古寢丘、淮南固始縣是否關聯,是否僑置,兩種不同觀點針鋒相對,各有所憑。
寢丘地名,見于古籍者有兩地,系同名而異地:一為同“沈”之“寢”,地在今河南沈丘縣東南,秦置寢縣;一為潘鄉寢丘邑之“寢”,地在今河南固始城關,古潘國地,楚相孫叔敖家鄉,秦置寢縣。兩地雖然同名,發生于兩地的歷史事件卻各不相同,可見寢丘并非專名。沈丘之寢,楚時屬于沈縣地;潘鄉之寢,楚時屬于期思縣地,而且歸楚時間有先后,期思設縣在前,沈置縣在后。古人因信息不靈、資料不多,故多將二者混同為一地,然后亂作史證。實際上,孫叔敖子僑受封之地,應為潘地之寢丘,而非淮北汝南之寢丘,下文將有詳證。
固始地亦然。歷史上淮南淮北都有過固始縣:一為淮北淮陽國固始縣,《漢書·地理志匯釋》淮陽國固始:“[顏注]師古曰:本名浸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之地。[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晉灼曰:固陵即固始,此班志之固始也,其世祖更名之固始,自屬汝南浸。周壽昌云:浸下注引應劭云,孫敖子所邑之浸丘是也。”《漢書·地理志匯釋》“寢”縣下所注亦略同。即固始亦有二:一是由固陵縣改名固始,西漢屬淮陽國,地在今河南太康縣南,東漢廢入陽夏縣,與所有寢丘無關,顏注錯誤;二是由浸縣改稱的固始侯國,東漢大司空李通封邑。
現在爭議的焦點即侯國固始,因它的分封還有一樁歷史佳話。《漢書·地理志匯釋》“淮陽國固始”條下:“[補注](汝南固始)縣,故浸也,浸丘在南,故以藉丘以名縣矣。城北又有孫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有關孫叔敖子受邑,見宋洪適《隸釋》收錄的東漢延熹三年(160年)五月立于期思縣城孫叔敖廟前的楚相孫叔敖廟碑(碑陽):“……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該碑陰亦云“相君三子,長子即封食邑固始”。明嘉靖《固始縣志》卷二:“固始縣,古潘國。”清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二“建置”:“固始,周蔣國……楚滅之,改為期思,封其大夫復遂為期思公,又分其地封孫叔敖之子,是為寢丘。”同志卷八“城池”:“固始在西漢為期思,為寢。寢即今縣城。”
由此可見,李通因慕孫叔敖以土寢薄取而為封,光武嘉之,更名固始。而讓李通所仰慕的孫叔敖受封之寢是古潘國之地,即今固始縣城,位于今固始縣城中北部的潘國故城遺址,是國務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此推論,孫氏所邑之寢應是淮南固始之寢,李通慕孫氏而受封,也當是固始之寢,故言孫氏子受邑,李通慕而受封之寢丘、之固始地在淮北是講不通的,難道淮北古寢丘之上也有個潘國故城遺址、蔣國故地?
孫叔敖活動的時間與受封時間亦可說明淮南之寢與淮北之寢各自存在,淮北之寢與孫氏封邑無關。孫叔敖死于公元前593年,楚莊王死于公元前591年,莊王封孫叔敖子于寢丘之事當發生在公元前593~前591年之間,但此時沈、項等淮北之地尚不屬于楚的勢力范圍內,《左傳》對此有明確記載,可以查證;而此時固始歷史域地的蔣、蓼、潘等古國已被楚滅,并建有期思等縣,楚莊王不可能把屬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給功臣,故孫氏所封之寢只能在淮南固始。同時,孫叔敖的家鄉和活動范圍,在他做令尹前也多在今固始歷史域地內。《呂氏春秋·不茍論·贊能》記載沈尹莖向楚莊王推薦孫叔敖時就說:“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孫叔敖為楚期思縣潘鄉人,即今固始縣城關人。《荀子·非相》說:“楚之孫叔敖,期思鄙人也。”楊注:杜元凱云“鄙人,郊野之人也”。《光州志·期思景賢義學記》引《史記·正義》:“寢丘,土浸薄也。潘即寢,義取諸此。”“潘為孫叔敖桑梓湯沐之鄉。”孫氏在做令尹前,在家鄉帶領鄉親修建了中國水利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從而使他名重朝野,故《淮南子·人間訓》說:“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這個工程遺跡至今還分布于固始中、東部平原地區。對此,武漢大學石泉教授有比較詳細的考證。
固始縣城特殊的地形,見高誘所注的《淮南子·人間訓》記載孫叔敖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丑。”高誘注“寢丘”云:“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后有莊丘,名丑。”《列子·說符》、《呂氏春秋·異寶》所載,亦與此相似。清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八“城池”、順治《固始縣志》卷三“城池”都說:(固始)城創于漢高帝,垣圍六里,門辟三關。其縣城一般至少有四門四關,而固始城只有三門三關,南門外因“前有垢谷”無法立關設市,至今亦然,故固始俗言“固始縣無南關”。固始縣城建于古寢丘之上,舊城東門上方嵌一石匾,上書“古寢丘”三字,1958年《固始縣志》(稿本)對此有過記載,因當時東城門還未拆除,人所共見。
至于《水經注·潁水》所記淮北之寢丘、固始,臨泉、沈丘等縣地方志所列之寢丘、固始,或許是一種地名巧合,或因縣名重復而誤記,都很正常,可以繼續研討。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在研究漢代政區地理時,列舉了很多名同而地異的縣,最多時一名而六地,現在這種現象應不多見。
這里還要糾正一下固始縣舊志中關于東漢時固始縣屬淮陽國的說法。西漢時,淮陽國治下有固始縣,由秦固陵縣所改,東漢省入陽夏縣。東漢時,因朝廷不斷弱化諸王實力,諸王封地也比西漢時為小。東漢淮陽國,是劉昞封地,是從汝南郡中析出新安、西華二縣而置。固始也是汝南郡37縣之一,但不屬淮陽國,只屬汝南郡,可能是前人整理舊志時把兩漢之淮陽國固始弄混了,才有此說。估計固始僑置說也與這種地名混同有關。
我對此的幾點認識:
一、僑置之說未見于正史明載。《元和郡縣圖志》曰:“光州固始縣,東漢封蓼侯之地,春秋時蓼國,楚并之,今縣是也。宋明帝失淮北地,于此僑立新蔡郡,領固始一縣。”這說得很明確,于固始原址上“僑立”的是新蔡郡,而不是固始縣,是新僑立的新蔡郡領固始原址的固始縣。固始舊志歷史沿革連貫而明確,只是在南朝時短時期向南、西僑置過,而未見從淮北南遷的記載。
二、古寢丘,古潘國,孫叔敖子受邑,李通慕而受封,在固始歷史域地上有序展示,古今史載明確無誤。有些古人在注釋過程中,強行把孫氏封邑與李通封地拉到淮北之寢,顯然與史實不符,更與大歷史背景下的楚國域地不合。古人注書,因資料、見解等原因產生這樣那樣的曲解、誤注,都很正常,我們不能責備先人,只能盡力還歷史于相對真實。如《水經注》關于“蓼國”(即固始東蓼)地域記述就與六安南部的“舒蓼”混同,現在應當糾正。
三、東漢延熹三年,期思、固始兩縣長官為孫叔敖建廟立碑,以后此碑由期思鎮移立于固始縣城文廟前,1960年前后,縣文廟改建會場后不知下落,《隸釋》與《金石錄》都收錄有碑文,清末固始舉人萬自逸在《固始縣地理沿革考》中記載:“孫叔敖碑為延熹三年固始令段光立,在期思出土。”現在有人認為孫氏碑文是后來假造,此說只能是假設。
四、沈丘之寢與潘鄉之寢都應存在。從前文所列史料,位于潁水流域的寢丘與位于決水(今史河)流域的寢丘應同時存在,存在原因應與西周中期淮夷部落受到周日益強大的軍事壓力,遷居于淮河以南的歷史事件有關,地名隨人是歷史常見現象,顧頡剛、錢穆等對此都有論述,此處不再列舉。但由于“人為”巧合又把固始與古寢丘聯系了起來,當今固始與淮陽國之固始,還有“潁水流域之固始”有無歷史淵源,成為一樁歷史公案。這個中間的結合點應是孫叔敖子封邑與李通封地,還應與古潘國、古蔣國有歷史的地緣關系。只有把這些歷史的聯結點有機聯系起來,才能勾畫出一幅合于史實的寢丘·固始歷史圖畫。
—————————————————————————
作者單位:固始縣史志研究室